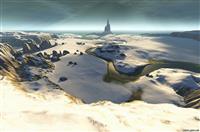《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政策和学术研究的层面展开讨论,相关主管部门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5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领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将于2015年推出方案,2016年征求意见,2017年正式公布。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2016年3月两会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第六十五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进一步将其明确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议题虽然多次被提及,甚至“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曾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在“十三五”期间,中央审时度势,统筹两个大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将延迟退休年龄的实施安排在“十四五”期间,这是非常正确的。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1953年《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的:“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六十岁,一般工龄已满二十五年,本企业工龄满五年者,可退职养老”,“女工人与女职员年满五十岁,一般工龄满二十年,本企业工龄满五年者,得享受本条甲款规定的养老补助费待遇”。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6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规定的退休年龄是“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和“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2021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2020年0~14岁人口为2.53亿人,占19.95%,与2010年相比,上升1.35个百分点。但15~59岁劳动就业年龄人口为8.94亿人,占63.5%,与2010年相比下降6.79个百分点。引人注目的是,60岁及以上人口是2.64亿人,占18.70%,比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1.91亿,占13.50%,比2010年上升了4.63个百分点。
展望未来,我国人口结构和预期寿命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在2035和2050年这两个时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变化非常快。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的数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我国中位数年龄仅为23.9岁,而2020年提高到38.4岁,预计到2035年和2050年将分别高达45岁和47.6岁,就是说,到2050年中位数年龄将是1950年的两倍;1950年我国零岁组的男女平均寿命预期仅为49.3岁,2020年已提高到76.4岁,到2035和2050年将分别高达78.6岁和80.9岁;其中,65岁组的平均余命1950年仅为8.7岁,而2020年提高到16.2岁,到2035和2050年将分别提高到17.8岁和19.5岁。其中,女性的寿命预期更长,1950年零岁组女性的寿命仅为50.8岁,2020年提高到78.6岁,到2035和2050年分别高达80.6岁和82.5岁。从老年抚养比来看,在过去70年来的变化也较为明显,例如,以65岁/15~64岁的比例为例,1959年仅为8.4%,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提高到10%,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到2020年就快速提高到14.3%,预计到“十四五”期末将提高到16%,此后发展的速度更快,到2035年将提高到20%,2050年提高到25%。
人的寿命预期不断提高,说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卫生条件和医疗技术水平进步了,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了,自然环境越来越宜居了,是一件大好事。但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一些挑战,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积极采取措施,其中,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各国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首个改革选项。
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定是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889年德国宰相俾斯麦建立世界上首个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前,各国无须以立法的名义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为了生计,工人一般都工作到很晚甚至直到丧失劳动能力时才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即使在个别企业里建立了私人养老金即企业主举办的待遇确定型(DB)退休金制度,工人退休的时点也是与雇主协商的结果,退休年龄属于家庭决策和私人部门的事务。但是,当国家建立起强制性养老金制度时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需要国家出面设定一个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于是,1889年俾斯麦根据当时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将70岁作为其法定退休年龄,那一年,俾斯麦是74岁。一旦公共养老金制度作为一项福利制度普照天下,就必然需要绑定一个法定退休年龄,而此时,降低退休年龄与提高替代率也必定被绑定在一起,成为工人斗争和争取福利权益的一个焦点。从此,法定退休年龄的曲线就一路下滑,直到20世纪80-90年代的谷底,此后,提高退休年龄成为各国的改革热点。于是,退休年龄曲线就成为一个“汤勺形状”:漫长的上百年的下滑加上近三四十年来的“翘尾”。
退休年龄的降低主要集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建立起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后的几十年里,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法,他们的退休年龄一般也都设定在70岁左右。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年,德国首先将法定退休年龄降至65岁,一战结束后,其他国家也纷纷随之降至65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纷纷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黄金发展期,除芬兰、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停留在65岁法定退休年龄以外,很多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纷纷降至60岁左右,法国和新西兰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才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降至60岁。当人们跨入20世纪90年代的门槛之后,二战后婴儿潮即将退休的预期和养老金收支压力迫使各国开始提高退休年龄,由此形成一个提高退休年龄的小高潮,但下调退休年龄容易,提高退休年龄却阻力重重,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实现了延迟退休,像法国和希腊等发达国家由于发生多次激烈反对的社会骚乱,延迟退休的改革不得不搁置起来。2010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流产的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掀起第二次提高退休年龄的小高潮,尤其希腊这个“老大难”竟然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压力下顺利通过了延迟退休的改革。在希腊的“激励”下,2010年,十几个国家一夜之间完成了十几年都受阻没有完成的提高退休年龄的立法进程,其中,西班牙从65岁提高到67岁,意大利女性公务员从61岁提高到65岁,英国从65岁提高到66岁,法国提高退休年龄的最后堡垒也成功通过了延迟退休的立法,实现了从60.5岁提高到62岁的改革,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至67岁。但另一方面,反对这项改革的社会运动从这些国家向东欧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罗马尼亚、波兰和中欧的德国蔓延,抗议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浪潮在欧洲风起云涌。
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诞生于大萧条后的1935年,比其他欧洲发达国家晚了几十年,起步实施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65岁,因为此前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退休年龄设定的是65岁。更重要的是,此前美国联邦铁路退休金制度的退休年龄是65岁,很多州早已建立起州立公务人员退休计划,大约一半计划的退休年龄使用的是65岁,另一半是70岁,并且企业雇员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以上。基于这些环境和条件,美国1935年通过《社会保障法》时罗斯福总统将65岁设定为法定退休年龄。此后,美国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始终没有变化,一直到1983年里根总统决定提高退休年龄。
在1983年里根政府决定提高退休年龄之前,由于老龄化的原因,美国联邦政府举办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老年、遗属和残障信托基金”(OASDI)的“基金率”逐年下降(“基金率”指年初的基金资产余额储备可以支付养老金下一年度的百分比,例如,如果基金余额储备是50%,就意味着还可用于支付半年的养老金):1970年基金率是103%,还可用于支付一年的养老金,但到1975年下降到66%,仅够用于支付七八个月的了,到1980年继续下降到25%,仅够支付三个月的了,预计1981和1982年将连续下降到18%和15%,到1983年8月基金将告罄。
为了应对基金收支失衡的局面,1983年4月20日,里根总统顺利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其中,“完全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这是战后以来美国社会保障的最大改革之一。所谓“完全退休年龄”是指符合条件的个人可根据其工作记录领取100%退休福利的年龄。里根改革采取的是典型的渐进式提高退休年龄,其主要特征有三个:一是与《社会保障改革全国委员会报告》提高三岁的建议相比减少了1岁,只提高两岁;二是将延迟的两岁分散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改革的预告期从1983年签署立法到2003年实施长达20年,改革的执行期从2003年正式启动到2027年完成,把延迟的两岁分散在长达24年里,预告期和执行期合计长达44年;三是每年仅提高两个月,且在延迟的两岁之间“插入”了一个“喘息期”,即在前6年延迟1岁之后,在66岁这个档次上留出12年的“喘息”时间,然后利用6年时间再提高一岁,每年仍只提高2个月。由于美国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策过程公开透明,经多次反复论证,态度十分谨慎,渐进式特征十分明显,所以,美国提高退休年龄从未像欧洲那样遇到社会阻力或成为诱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从前述中国目前退休制度的现状来看,延退主要涉及三个群体:50岁退休的女工人、55岁退休的女干部、60岁退休的男职工。这三个群体的退休年龄均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其中,难度最大、提高年龄最长的是女工人这个群体。延迟退休年龄是社保制度改革的百年大计和社会稳定的百年大计,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延迟退休改革涉及人数最多、一次性延退年龄最长,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世瞩目。因此,延迟退休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应确保万无一失,否则,其负面影响将十分大。为此,结合发达国家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经验教训和具体做法,从策略上讲,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国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时至少应关注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不同群体应坚持同龄退休的“一视同仁原则”。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为65岁,少数国家为67岁。鉴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趋势,确立65岁为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为此,在不同性别之间、灵活就业人员与正规部门之间、机关事业单位与私人部门之间、脑力劳动者与非脑力劳动者之间,其政策制定要尽量避免碎片化现象,以防止相互之间的攀比。欧美退休制度之间的一个明显差异性在于,由于历史遗产的缘故,欧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性别、行业、职业的退休年龄差别,这些差别正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改革的重点,也是这些国家社会不稳定性的根源之一,而美国则不存在这些差别,退休制度从未导致社会不稳定。
第二,坚持小步慢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渐进式延迟退休节奏。小步慢走的渐进式延迟退休节奏涉及几个问题:一是“预告期”的问题。有的国家设立的预告期较长,有的较短。我国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来,全社会已有了十多年的心理准备了,所以,即使设立“预告期”,也无须留出那么长的时间。二是设立“等待期”的问题。目前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比男职工低10年,在设计男职工延迟节奏时可设置等待期,“拉长”男职工的延退节奏,也可考虑不设置等待期,有些发达国家就没有设置等待期。三是延退的节奏。美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之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就已达65岁,再延迟两岁的压力不大。中国目前的实际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年龄都很低,如果完全按照美国的做法,估计要持续上百年,这是不太现实的。但是,美国的做法告诉我们“渐进”很重要,应适当把握延退的节奏,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第三,特殊工种的退休政策不包含在国家制定的基本退休政策之中。多年来,“特殊工种”的滥用导致提前退休情况十分严重。科技进步使得特殊工种的分类和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家制定延退政策时不应包括特殊工种的特殊退休年龄,这个规则应由相关部门专门制定,单独处理,以减少改革阻力,防止制度“碎片化”。
第四,同步提高最低缴费年限。在过去的10年来,遵缴率逐渐下降,已从90%降至80%,越来越多的登记参保人在达到最低15年缴费年限之后停止缴费,这既不利于提高个人未来养老金替代率,也不利于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提高最低缴费年限越来越显得急迫。因此,适当提高最低缴费年限应是此次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引入弹性退休机制。弹性退休机制是指在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之前设定一个较低的“提前退休年龄”,比如63岁,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设定一个较高的“延后退休年龄”,比如67岁,前者领取的养老金标准略低于法定退休年龄领取的全额养老金,后者领取的养老金标准略高于法定退休年龄领取的全额养老金。引入弹性退休机制好处多多。一是可更好地推动延退改革进程,减少改革阻力;二是可为参保人多提供两个选项,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三是可为需要隔代抚养的参保人提供一个选择,有利于弥补托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等;四是可重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的主人翁精神,在闲暇和收入之间充分体现家庭决策的权衡作用,提高参保和缴费积极性;五是可为提高制度可持续性做出一定贡献,因为广大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工作人员选择“延迟退休年龄”的概率高于其他群体,而他们的收入稳定,对提高基金收入具有积极意义。对弹性退休年龄机制可实行“申请制”,如个人不提出申请,退休年龄将自动顺延到下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