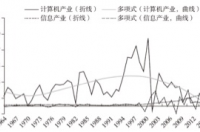皮克迪他的在《新资本论》里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其主要的建言,是以“全球”的公权力来对市场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平衡——对顶级富人家庭课以重税。方案之一,是对美国年收入超过五十万美金的人启徵边际税率高达80%的所得税。历史上施行过的累进所得税率,在欧美发达国家(直到1970年代)曾经超过90%,而美国针对富人的最高税率甚至达到过96%。然而扼杀性的高税率效果并不如预期,遏制了有效投资、风险承担、创新发明,最终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而经济增长受阻,结果穷人的生计并不能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个严酷的历史教训,可以说是里根、撒切尔代表的保守经济政政策之能勃兴、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市场无误思潮所以崛起的最大动力。
上述解决方案,要求各国联手稽征高昂的财富累进税,政治上可操作性尤其低。在信息技术时代资本国际间的流动畅行无阻,任何经济体想实施不利于资本的税率、利率、汇率、及管制政策,无异为渊驱鱼。过往三十年供应链的全球化整合,无不以资本为引擎,引领着产能、技术、就业、市场的综合能力平衡和再平衡。我国肇始于经济特区的开放,成果非凡,关键也在于给资本税率和监管松了绑。跨国公司让巨额赢利趴在分支机构的账面上而不挪回总部,原因也在钻税率差异的孔子。因此,要“全世界的资产者联合起来”可以说连门都没有。
皮克迪的母国法兰西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这里举两个微观层面的例子。社会党人二十余年后重新执政,奥兰特总统把富人的累积税率提高到75%,影视明星大鼻子迪帕蒂立即迁册比利时,随后入籍俄罗斯。这和他自己声称的“俄罗斯是他精神上的祖国,因为他父亲是个老社会主义活动家,”其实没什么关系,只因为俄罗斯的最高税率是13%,远低于任何欧美发达国家。葡萄牙的地产商人拜奥兰特为里斯本最大的财神,他把法国的钱赶到了那里投资置产。目前法国人成了葡萄牙海滨高级住宅的最大买家,紧随其后的有巴西人(同样说葡语)、中国人和英国人。中国人何苦远到葡萄牙买房子?你不妨留心一下。
皮克迪的政策建议既然无法落实,看来也就无从被证伪,但是这种吊诡的安全性被一项长程历史的实证研究给颠覆了。有数的经济史学家G.克拉克的新著“The Sons Also Rise”(似可译作《子孙照样发达》)对“皮克迪疗法”来了个釜底抽薪。书名很有趣,是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翻版,在英语里太阳和儿子的发音完全相同。克拉克教授辩解说这书名是编辑给取的,他的前一部名著“A Farewell to Alms”(《永别了,施舍》)也套用了海明威的名作《永别了,武器》,alms(施舍品)和arms(武器)的发音很相近。看了这样的书名,不用猜测你就不难想见书的意图:社会上成功人士的后代也将成功,(而不成功人士的后代同样不太可能成功)。
克拉克的分析调用了大量历史旧档和征集了长程历史的实证数据,揭示出跨(多)代的社会粘滞性(social persistence)是异乎寻常的高,上层人士以及下层的人要“回归到”社会的平均水准相当艰难,常是绵恒数代、十数代而不可得,不论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文化条件、和体制安排下,都是如此。他试图证明或业已证明的结论,可说是“惊世骇俗”,岂止是“政治上不正确”,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些信条也将有颠覆性的影响。
你也许对各种“学”没有兴趣,但你对于自家的儿孙能否“发达”是很难不感兴趣的。在个体层面,克拉克的建议是,若想自己的子女继续发达,或者变得发达,你最重要的事是同好的伴侣结合,给孩子一个好的生父(或生母),其余则顺其自然可也。出生后的额外补课、小灶家教均无关宏旨,甚或徒劳。
相信许多人(曾包括笔者)听了会很不自在,甚至深感侮辱,拍案而起怒斥他是“种族歧视、帝国主义、唯精英论者、优生论者、天良丧尽……”不一而足。克拉克教授深知他的探索有离经叛道的味道,为避免各种罪名起见,他做了许多细致详尽的实证数据分析;提出结论时也很委婉,往往以提问的方式,比如问,“要不是基因遗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历史上可观察到如此高度一致的现象呢?”
克拉克教授用的方法相当简单,追踪数百年来姓氏在社会的综合地位的起落,特别是那些显赫而稀少的姓氏,所占据的地位高于社会平均水准有多大程度,能持久多少代。书中集中考察了多个社会,包括英国、日本、印度、韩国、中国,和美国、瑞典、智利、丹麦等国家,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群体的长期演化,实证数据的跨度几世纪,英国的数据更长达九百余年。克拉克发现非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下的英国,社会流动率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是同样的迟缓;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也不比推崇社会主义平权的瑞典、丹麦的高,甚至和印度、日本等差不离。
教授把这种人类社会的高粘滞现象称之为“社会执着度”(social persistence),计算出代际传承率为0.75左右,并认为是一个“普世常数”(universal constant),与文化、制度安排等等无关。如此,孙辈和祖父辈的相关性是它的平方,即56.25%,第四代受祖辈的影响则为42.19% (0.75的立方)…… 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续的影响仍有可观的7.5%。这对人们素所“乐意”相信的高流动性的信念——社会越开放流动性越高,而在理想的社会每代人都应当“重新洗牌”,每个新生儿都将“生而平等”地面对着平等机会,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克拉克考察和分析的结论,是风水即便轮流转,速率是很低缓的,远不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两代人之间;而得要十代人——“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据他的计算,一个家庭要在一代里从社会综合地位的中间水平翻到社会顶层的0.5%,机会只有五亿分之一。在英国这几乎没有发生过,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现代英格兰;至于要通过一代的时间从社会的底层(0.5%)翻到社会顶层(99.5%)的概率等于零,克拉克相信,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我不是太有把握,朱元璋算不算是个例外?)
究竟哪个更有道理?
克拉克指出,人们高估社会流动性的印象,部分来自误算。他们以物质收入的代际影响替代了社会流动性。其实,竞争社会地位、获取资源的能力是综合性的,除了财富,还有教育(掌控信息和知识的)、职业(拥有高尚岗位)、社会联系(抱团的紧密网络)、健康状况及长寿,等等,都是构成“社会成功”的元素。譬如说,盖茨和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准会比父辈差得远,他们不惟不再孜孜为钱打拼,其主要的职业甚至是在散财(公益基金会之类),然而他们的综合社会地位,大半由祖上遗传得来的综合社会能力(underlying social competence),并不会很快衰减。若是根据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大不如其父,就以为他们迅速回归到社会平均,从而得出美国比其他社会流动性更高,更 “公平”,是很不可靠的表面现象。
至于为什么人们对社会流动性速率的印象与此大不相同,克拉克的解释,是人们意识的重心是短期的,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代际变化,只是两代人之间发生的变动,这时随机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噪音”——各种运气(好的或坏的)掩盖了真实的讯号。噪音的影响在长程中会抵消、在群体里会折冲掉,需要大致跨四代人的时间,大约为75年。他提出的实据,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社会和之后的现代社会的比较。测算的结果表明,传统英国的代际粘滞系数在0.80-0.85,现代英国的代际粘滞系数则在0.73-0.84左右。以此来计算,第四代英国人受其曾祖父影响的仍分别为 28.4%-40.96%(传统)和40.96%-52.20% (现代),相关度在五分之二左右,虽说有改进,都依然很显著。而素有“机会平等大熔炉”的美国,社会粘滞度比起英国也实在不遑多让。
在提出“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个好配偶”的建议时,克拉克请大家注意,1、配偶的“好”,不仅他(她)是否有钱或生于有钱的家庭,也不在其面貌是否姣好,而是其生父母的财富、教育、职岗、社会网络、健康长寿等因素的综合考量; 2、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从长计议,才能确实把握他们的成功乃有坚实的根基,而非“噪音”所致的假象。
那么,克拉克的发现和皮克迪的研究又有什么关联呢?《新资本论》揭露出财富的社会分配严重不均,且在扩大之中,这也许是个事实。皮克迪着力剖析的困境不止是发达经济体特有的,与我们的国情也有着相当的关联。例如,国际间常被引用的一个数据,称美国参众两院最富的前50位议员的财富加总起来不到11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大委员会里最富有的前50位代表的财富总值达到了980亿美元。要是把没露白的财富也计算在内的话,两者的差别可能还要令人瞠目结舌。可是,如前文所述,皮克迪提出的在全球合作对财富征收高的累积税率的解决思路,很少具有可操作性。克拉克的发现则(间接地)对皮克迪的核心理念发难:非但以公权力为杠杆的社会再分配成效短暂甚至是徒劳的,其初衷都是疑问。克拉克认为以发挥人类本身的规律来运作,市场带来的结果其实更“公正”(fairness),更深刻也更为持久。
我们主要关心的,自然是中国人的社会流动现状。《子孙照样发达》里辟有专章,就中国近代的案例展开讨论,这个案例是以克拉克教授和他的博士弟子郝煜的合作研究——“中国三个政体下的社会流动性——姓氏研究(1645-2012)”为基础的。他们汇集和分析了清朝、民国、以及1949年后大陆和台湾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三种体制下中国社会的流动性都和世界各国的相仿,比一直以来认为的要低得多,尽管这十几代期间,尤其是十九世纪末页直到现今,我们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剧烈变革。作者沿用了姓氏的变迁的分析方法——通过比较该姓氏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它在上层成功人士的占比,来说明该姓氏是处于社会的顶层及上层、中层、还是下层及底层。这里所谓“成功的社会综合地位”,衡量的要素除了“富”,主要是“贵”,包括科举里考中“举人”、“进士”数量。成功获取功名在清朝是地位晋升最主要的社会阶梯,民国以后,“贵”的评测改换了内涵,科举的功名被替换成现代的上层职岗:名校的教授、学者院士,名医生名律师,高级行政官员,以及企业的董事长,等等。
作者追踪前清的“精英十三姓氏”(主要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三百多年来的变迁,证实前朝的精英在现代社会上层的占比仍然超过社会平均(overrepresentation)。如果把社会平均水平设为1——姓氏占总人口的比例和该姓氏在上层成功人士所占比例是同等的话,那么“精英十三姓氏”同“全国三大姓”(张、王、李,占全国人口约22%)以及“地区三大姓”(顾、沈、钱,总数在两千万人以上)相比,其影响远远超过1,也就是说,他们的“代表比率”远超过社会的平均值 (overrepresented)。
具体的计算,根据1820年至1905年(之后科举被废除)的科考数据,在乡试(“中举”)和会试(“中进士”)里成功的比率,“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国三大姓”的8.6倍(张王李三姓人口众多,足以代表全国平均水平,故比率为1),是“地区三大姓”的4.7倍。
废除帝制进入近代共和以来,差别依然巨大。从民国政府的高官名录(1912-1949)来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国三大姓”的4.85倍、“地区三大姓”的2.28倍;从著名大学的教授名录(1912)来看,“精英十三姓氏”为“全国三大姓”的3.82倍、“地区三大姓”的1.88倍;从企业的董事长名录(2006)来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国三大姓”的4.51倍、“地区三大姓”的1.62倍;从中央政府的负责官员的名录(大陆,2010)来看,“精英十三姓氏”则为“全国三大姓”的2.75倍、“地区三大姓”的1.46倍。
事实上,“地区三大姓”(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精英姓氏集团”。它也明显超出了“全国三大姓”所代表的全国平均水平。上述的五个测评数据,顾、沈、钱三姓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3、2.13、2.03、2.78和1.88倍。
民扬儿在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撰写经济博士论文,他曾是克拉克教授的助研,帮助整理了部分资料,我们父子对克拉克的数据、分析方法和结论诠释也曾有过讨论。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姓氏却是相当集中的:大陆的三百个上下的姓氏覆盖了95%左右的人口,而台湾的三十个姓氏几乎覆盖了人口的全部(98%)。不比英国,姓氏多达27000个,所以克拉克的模型更适合西方的社会,追索小(成功)姓氏样本的长程变迁更容易。克拉克显然注意到了这类差别,他在中国的姓氏上再加上地域的限定,调查了比如象“宁波范氏”、“海宁查氏”、“常熟翁氏”等精英家族的变迁。结论仍旧不变,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从长计议,数百年来依然粘滞,并没有因为社会体制、文化价值的剧烈变动而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要变也是“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的长程演变,在他的“普世常数”的社会流动性规律的范围之内。证据之一是,1949年后大陆和台湾分野,社会体制及其政治干预迥异,但是翻天覆地的折腾之后,社会流动性在两者之间,相差却甚小(台湾的甚至略高一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直接参阅原书。
《子孙照样发达》一书今年三月正式出版,引起了社会关注和各界热评。浏览各家包括不少著名经济学家的评议,很少能对书的数据模型、方法诠释提出质疑的,尽管如此,书中提出的结论还是令人难以“下咽”。正如著名名的哈佛经济学教授(B. Friedman)所说,笔者亦有同感,“我们只能希望,克拉克揭示的规律不是事实。”
在公共政策设计之上,这涉及到了一个更根本性问题。在争议社会分配是否平均时,人们常是把“公正”、“正义”、“公平”、“平均”搅和在一块,难道它们是一个概念吗?如果确有区别的话,我们又应当在哪个层面加以区分?
比如,你可以追寻自己周边的人,同乡、同学、同事等等,“发达”或“不发达”的经历,以及他们前代的经历。开放三十余年以来,各方面的松绑的结果,社会资源的分配确实有了更多的差异,然而这样的进展,难道是更偏离“公正”了吗?
我倒是倾向于相信,怎样使得竞争的场地更为平坦才更符合人类的生存条件(human conditions),才能让竞赛博弈一轮又一轮地健康扩展,广泛激发出全社会的创造能力。克拉克的研究有其建设性的贡献,将为社会分配及再分配长久公义的基地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