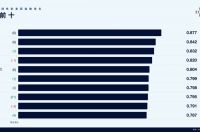■只是十余年,中国的环保NGO却可堪沧海桑田。
■从“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到“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观鸟、种树、拣垃圾”到盯紧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
■从“只有一个志愿者,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到数量已经突破3500家,精确数字无法统计
■从“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到醒目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话语权
■从偶尔“基于私交,联系到高层资源”到“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图/向春
1990年代初期,一位老者经常蹬着自行车来到北京三义庙,叫上一名叫杨东平的年轻人,去不远处的紫竹苑公园,谈话。
这位老者,便是名门之后梁从诫。而杨东平,后来的著名教育学者,得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这本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那时候只有一个志愿者,就是梁先生的夫人,后来变成十个人,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
谁都不曾想到:最早诞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后来的十数年中,成为一支无法忽略的绿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环保NGO已经突破3500家。因为有的机构还未注册,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草根组织加入其中,精准的数字变得难以统计。
又一个白求恩
“观鸟、种树、拣垃圾”
事实上,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境NGO,是辽宁盘锦的黑嘴鸥保护协会。它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发起人刘德天,是《盘锦日报》记者。
作为一块国际重要湿地,那时的盘锦常有国际生态学者前往调研。记者出身的刘德天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诞生,归因于两个外国人的影响。
一位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黑嘴鸥专家英国人梅伟义,他让刘德天第一次听到了“濒危”与“生态”的词汇,“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会给生态网带来损失”。
另一位外国人——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奇博,则让刘德天“想起当年的白求恩”。“又有一位加拿大人,为了世界的、中国的鸟类保护来到中国,这些行为都是跨越国界的。”当年还带有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话,却是两种思维撞击的真实逻辑。
三年后的北京,梁从诫、杨东平等知识分子选择了环境领域,作为提升公共参与的契机和空间。最初的思路,竟也全然来自于他们的西方视野,就连“自然之友”这个名字,都是从香港“地球之友”借来的灵感。
注册问题屡屡碰壁,当时的环保总局最终没有担当挂靠单位,至今,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
紧随其后,1990年代中期,地球村、绿家园宣告诞生。
当时,半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基金会,恰恰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机构。民间力量借由这个空缺,登上舞台。
初期的民间环保行动,后来被概括为“观鸟、种树、拣垃圾”——功能基本都是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启蒙。当时的自然之友连续数年进行媒体的环境意识调查,发现有关“环境”,报纸上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环境卫生”和“绿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处于“浅绿”状态。
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的重工业蓬勃起飞,环境问题也早非种花种草、讲究卫生般简单,当今天的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具有了“深绿”的环境意识,推动政府和公众由“浅绿”走向“中绿”的时候,很难说,不是中国环境问题深度化的倒逼使然。
一切自舆论始
“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变化,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1998年的大洪水、随后北京的特大沙尘暴,一系列灾害性事件,一个个癌症村,唤起了公众的警觉——环境正在急剧恶化。用汪永晨的话来说,“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1995年、1996年,梁从诫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首钢搬迁。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人们理解作为纳税大户的首钢,却不察觉作为污染大户的首钢。
后来,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要求禁绝藏羚羊绒的贸易——因为欧洲是其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布莱尔次日复信表示支持。今天,成龙在电视屏幕上说“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人们习以为常;但在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举。
藏羚羊保护和野牦牛队的成立,拉开了环保议题公共化的闸门。从1995年起,到“野牦牛队”去当一个志愿者,成为民间一种被赋予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
无论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还是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都曾是记者,这体现出民间环保行动成长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借力媒体,一切自舆论始。
2000年,针对都江堰杨柳湖危害生态的水利工程,两个月之内出现180篇(组)新闻报道,工程后被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张学忠叫停。民间环保团体通过舆论对决策的影响,自此开始。
随后,2002年的关键词是“昆玉河”,2003年开始是“怒江”,2005年是“圆明园”、“环境影响评价”和“松花江”。
尤其是围绕怒江水电的争论,涉及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电力企业、专家、民间环保组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密集关注,最后以温家宝总理暂缓建设的批示而告一段落。
而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质疑,在公开参加国家环保总局听证会后,环保组织又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会,经由媒体放大声音后,终于在一个月后促成了整改工程,被看作“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典范”。比起几乎是闭门召开的昆玉河工程争议对话会,只不过事隔三年。
到了2005年,人们已经不得不用“风暴”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
环评风暴,更接近于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和NGO的一次默契互动。环保总局最终升格为环保部,环评一票否决得到确立,之后更延伸出流域限批、区域限批等杀手锏。而环境NGO也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一呼百应,相互联动。
现在已经很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不得不承认:比起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这十余年,环境NGO产生的现实影响是明显的。
中国特色影响力
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但很多时候,舆论影响并不能一锤定音。
自然之友初创伊始,生存多艰,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牟广丰看着着急。他与梁从诫、汪永晨、廖晓义等人是多年好友。
牟广丰正在起草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文件,他试图为好友们的努力正名,不确定地写下“这段时间,出现了‘自然之友’这样的社团,对于提高社会的环境公德、树立社会的环境意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所在社团组织,应大力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
梁从诫问:“这样写行吗?”牟说:“试试吧。”
幸运地,这句话最终没有被修改或删除,而是经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之口,出现在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环境会议上。随后出台的《关于保护环境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1号文件,是国内第一次以国务院决定的形式承认非政府组织的地位。
这是一个中国特色逻辑的典型写照。
在后来的环评风暴和江河呼告中,参与其间的环保NGO也是通过其会员,在全国人代会上递交了反对西南建坝的提案。在接到发改委强调水电工程重要意义的回复之后,一位高层官员直接致信温家宝,由此获得了第一份总理批示。
当事人后来坦承,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以一己之力,递交提案、直接上书领导人的方式,是影响决策的最主要渠道。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坦言:政府官员与NGO领袖的个人魅力和亲密关系,是双方顺利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这个平台才有了意义。”
专业,专业,再专业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
与精英NGO们动用个人资源、力图撬动高层缝隙的行动路线并行的是,草根环保组织顽强地自下生长,有如雨后春笋。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的印象中,2000年前后,民间环保团体专业性、地域性的特色越发明显,到2004、2005年,这样的组织猛地多起来了。
在温州,高中生方明和放弃高考,专门从事他在学校期间创办的绿眼睛环保团体,以19岁的年龄,成为环境领域最年轻的NGO掌门人;在成都,曾经是公务员的田军,创办了河流研究会,从水文的视角关注成都环境;淮河污染问题举国震惊,“淮河卫士”应运而生,直面污染,救助癌症村。
一时间,迅速扩大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推向细致、多样的环境问题,大量项目具体到了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甚至有大学生社团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濒危物种,比如大别山野生兰。
在越来越多的资助和支持力量下,以NGO为载体、以民间身份从事环境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可能性。企业家王石曾被一位SEE生态奖得主的话触动:专职从事环境NGO,“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19岁的方明和,正是基于一家跨国企业的环保奖金的支持,挺过了和小动物们挤在一起入眠的艰难岁月。
近十年内,在中国内陆最活跃的公益基金会之一——香港乐施会,资助各类环保项目的数额,高达人民币数千万。
不得不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亮相,运作具体项目数年之后,2005年开始颁发生态奖,开放资助更广泛的环保项目,奖金由50万元,升至100万元,又升至110万元。
而来自官方色彩基金的系统资助则显得更为艰难,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公益组织井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款资助民间NGO的救灾项目,北京“地球村”的彭州项目获得三百多万元的资助。
在过去的五年间,来自企业和国内机构的款项比重不断提高,早期较多依赖国外组织的情况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
还有更多的力量,综合拉动着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的专业化趋势。
在全球以对抗性姿态著称的绿色和平,自2002年进入中国后,继续延续其果敢激进的色彩,资助上海消费者朱燕玲赴瑞士就转基因原料挑战雀巢公司,将检出有毒物质的惠普电子垃圾作为礼物送到惠普公司的庆祝活动现场。
而以稳妥、善于政府沟通为特点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中国30年,始终稳扎稳打,与林业系统保持良好的互动,其8个办公室的50余名生态专业人员,常年工作在保护区一线。
在杨东平眼中,他们的工作对本土NGO意味着重要的启示——“每个方向都有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拿出高度专业化的调查报告,与决策部门沟通”。这些带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政策室主任,成了阿拉善协会的秘书长;环境促进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现在服务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而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几年前是林业科学院的研究员。
今天,“乐水行”的志愿者们,定期沿着北京的水网步行探访、进行城市水文考察。
这个时候,距离最初的“观鸟、种树、拣垃圾”,已经过去了10年。“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锋,依然是记者。他手持专业望远镜,观鸟时已经能够辨识黑脸琵鹭和棕背伯劳——与十几年前相比,一切显得专业。
低估了开放度?
不再“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困窘依旧存在,组织登记和税收减免的阳光依然难以普照民间环保团体,资金困境是最主要的瓶颈。
尽管从2002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企业的合作深度不断拓展,但囿于体制所限,30年来,在中国开展项目花费的数亿人民币,还是全部来自总部。
绿色和平在香港募集的资金可以满足当地的项目开支,但扩展到中国内地后,财政的缺口就出现了,至今仍然是最大瓶颈。
而草根NGO则从没迎来真正的春天。方明和和他的同伴们,连续多年住在苍南县少年宫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无论冬夏,在一道隔墙后面用脸盆冲凉洗澡。
今天,除了资金的困境,大量环保NGO亟需能力建设,大机构和小机构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反差——部分大机构的官僚化倾向已经出现,资源利用效率受到质疑;而大量小机构的兴衰荣辱,还系于发起人一身。
带着这些现实的掣肘,2007年,因为厦门“PX”、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上海磁悬浮工程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群发,公共参与元年到来了。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
2009年9月,汪永晨回忆80年代在上海采访一位市领导时,对方曾私下说:“上海的水的情况要是告诉老百姓,他们得造反。”20多年后,《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宣布了这一知情权的确认。
作为一个直接对抗流域污染的草根NGO,淮河卫士的故事值得记取。
河南摄影师霍岱珊以淮河治污、环境受害者救助为职业,一度阻力重重,“一进村有人看着,有人盯梢,老百姓和我们一接触,就找老百姓谈话”。几年下来,“一些幻想没有了。比如幻想通过敬爱的领导去解决问题”。
2007年,霍岱珊入选“年度绿色人物”,得奖消息传来的20天前,他还被请到公安局,以避免与前来视察的环保部领导接触。他噙着眼泪说:直到获评“年度绿色人物”,淮河卫士才走出了身陷沼泽的感觉。
杨东平还记得,“以前,我们在6·5环境日那天一开会,就有人在门口转悠、‘关注’,我们一想,这日子离敏感日太近了……”这样的回忆,已成历史。
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项目总监施鹏翔回忆:“在我们刚进入中国内地时,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和平除非抛弃国外的工作手法,否则不太可能在中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放弃机构的DNA,坚持独立,坚持批判,坚持行动带来改变,并且很好地生存了下来。我觉得,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放度。”“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环保行动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一位职业环保人士说。
只是十余年,却真可堪沧海桑田。2009年4月的一次企业与环保组织互动的生态奖颁奖活动中,自然之友总干事感慨连连:“今天中国社会,能够让企业和民间组织聚在一起,用一种特别公开的方式来讨论很多重要的问题,我1994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时候,想都不敢想,那个时候民间组织做事,都觉得自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