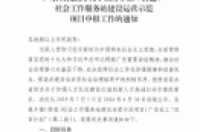自由是我生命的追求
时代的滔滔波浪千重万重,是什么支撑一个人走过漫长征途,跨越山河大海?是信念。2019年,徐永光70岁。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的际遇自是翻转浮沉。
徐永光生于浙江温州的城市贫民家庭。那一代人,几乎都是“风暴之子”。徐永光的“开蒙老师”是有线广播,他常趴在窗台上,醉心于喇叭里传出的红色音乐和时政新闻。1966年,因“站错了队”,他处境困难,无奈之下外避。
两年后,徐永光应征入伍,希冀新的生活,却因一个亲戚的原因而入党受阻。强调纪律和等级的军队锤炼了他,但他更想回家。服役期满,他放弃提干,回到家乡的邮电局当了一个汽车修理工。1973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徐永光报考了大连海运学院。世事多舛,“白卷英雄”张铁生横空出世,全国考试作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徐永光开始思索此生所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为什么活着,怎么个活法。”受温州永嘉学派叶适的影响——“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他总想自由地生活、做事。
1978年,徐永光被抽调到北京参与共青团十大筹备。团代会之后,他一心想回家。团中央组织部领导惜才,挽留他,两人在办公室里一谈就是8个小时。下班时,见徐永光仍不为所动,领导说第二天接着谈。就这样,徐永光在团中央接着干了10年,官至团中央组织部部长——正局级干部。
也许是理想主义者的创新太超前,徐永光推动共青团体制改革的方案捅了“马蜂窝”,竟要做背水一战的准备。面对现实,自知目标大于能力,壮志难酬,徐永光递交了递呈,并提出创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中央书记处评价他为团中央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受了不少委屈”,但也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
李克强(中)、徐永光与希望工程受助学生“大眼睛”苏明娟。
1989年,徐永光终于“下海”,走上公益市场探索之路,继而有了轰动中国的希望工程。“在体制里虽然也能做事,但缺乏自由发挥的空间,这让我走出了体制。也正是这样,中国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多了一个希望工程。”徐永光说,做公益30年,支持他的力量是寻求自由。“政府自由吗?没有人敢说吧;商业好玩吗?九死一生最煎熬;但是公益几乎是一张白纸,有无限的想象力和创新空间,所以公益是自由的。”
在公益空间,徐永光多次联合众师友共同创办、支持、搭建平台,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恩派、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等公益平台。经历迭代后,他又推动了中国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论坛、中国好公益平台。
30年里,徐永光一直在开创中国公益平台,奠定公益伦理,培养公益人才,为中国公益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我生命中铸就的信念是:要真实地、有责任感地生活。”他说。
《中国慈善家》2019年2月刊封面
终结“国营慈善”
快3年了,提起《慈善法》,他仍然耿耿于怀。一部堪称“十二年磨一剑”的高阶法律,有些要害条款在他眼里简直是倒退。
《慈善法》规定,任何一家慈善机构募捐都必须到政府核发牌照的互联网平台进行,只在自己的官网上募捐系违法。“对于这种玩法,有一千个理由说不好,说不出一个好的理由。”徐永光说,这使得慈善组织的大数据资源归零,窒息了互联网公益的创新。《经济学人》把大数据视为“石油”,而中国将是大数据的沙特阿拉伯。徐永光说,富油矿——捐赠大数据是慈善组织资金可持续发展的本钱,“如果连本钱都没有了,何谈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
“石油”去了哪里?徐永光愤愤不平——被拿到牌照的平台垄断了。“这是在用计划经济思维对慈善组织信息化权利进行行政管控。”他呼吁,互联网是公益发展的基础设施,要结束互联网公益的行政管控。“政府的责任是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非用计划经济思维进行行政管控,更不应制造垄断。事实上,政府管得越多,责任越大,风险更甚,除了管死,别无益处。”
被吸走的不仅仅是大数据,还有真金白银。
2018年,南都基金会和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团队共同开发的中国非营利组织GDP(即N-GDP)发布研究结果:2016年,中国社会组织创造的GDP是2789亿元。徐永光将其与另一项数据做了对比:2016年,中国的公益支出为6373亿元。
为什么6000多亿的公益支出,只创造了2000多亿的GDP?徐永光说,份额缩水在于钱出现了逆向流动——基金会从民间募集的捐款,很多流向了政府账户,创造的GDP属于政府,不属于公益组织。
传化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告诉徐永光一个现象,很多县一级地区找不到公益组织和民间组织,即便有,也多是政府办的。徐永光纳闷:改革开放都40年了,十八大也过去6年了,官办慈善的改革无动于衷。“‘国营慈善’不终结,健康慈善生态无望。”他说,结束“国营慈善”继续坐大的局面,让慈善回归民间,是公益发展的基础条件。
说刺耳的话,是徐永光的老习惯。当他推动共青团改革的时候,也曾一篇接一篇地发文,像一个愤青,直指体制之弊。他拿出来的改革方案,更是令他被人攻击为“团中央的叛徒”。转眼,当年的青年70岁了。也有人说,70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老江湖知道边界、深浅和策略。
这些年,中国公益行业外部环境浪潮汹涌,徐永光也预见到未来10年处境之艰难。他鼓励公益同行要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念拥抱困难。他赞同阿拉善SEE会长艾路明的话——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会撞墙,那你干嘛非得把头撞破呢?没有必要。走不过去可以绕着走,实在不行拿着梯子爬过去,总有一条路是可行的。“做慈善是我们的自由选择,我一直讲,我就是为了自由来做慈善的。来做慈善就别抱怨,公益圈要么自娱自乐,要么自我陶醉,要么就自怨自艾,或者睡在昨天混今天,这都不行的。通向理想,通向目标不只是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徐永光原本对互联网公益寄予厚望,在他看来,互联网公益如同慈善组织的生命系统,让优秀的公益组织源源不断地获得公众的捐款和支持。早在20年前他就预言,“在线捐款的选择性、便捷性和透明性,将使那些影响大、信誉好的非营利机构更加迅速地壮大起来。”
移动互联网成全了徐永光预言家的角色,但如今也压下了一个天花板。现实是,任何一家公益组织和没有领到平台“牌照”的互联网、新媒体传播机构或技术开发第三方都被强制出局,在《慈善法》一项条款之下,无缘“互联网公益传播+筹款+参与”的创新模式。
“面对的是一张未经行政许可的‘生死牌’,谁敢冒死而为?逆信息化生存、去市场化发展的中国公益行业,创新已死,前途安在?”徐永光痛心疾首,“‘国营慈善’随时会让慈善公信力毁于一旦,前车之鉴难道都忘记了?”在一次行业会议上,他在台上拍着桌子对年轻人说:“这些问题,你们得去喊、去叫、去争啊!”
2018年9月25日于北大举行的“益行者之夜”是一场希望工程的“老友记”。公益界的“三光”——徐永光、康晓光(左)、陈越光(右),与到场的公益同仁共同回望了自己与希望工程结缘的故事。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如今已年近古稀。
重建互联网公益生态
将近20年过去,互联网世界早已今非昔比。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材料、生物科技、新能源、高端设备……浪潮终将席卷所有人。“赶紧贴上去再说吧。”徐永光说,公益行业再不跟上潮流,就可能被时代淘汰。他总是那么焦虑。
2019年初,徐永光发出《解放互联网生产力》一文,还特意写了一段引言:“此议题关乎信息化社会公益组织的生存权、发展权。提请吃公益饭的同行花10分钟读读。希望引起讨论,也欢迎拍砖。但如果无动于衷,乃至麻木不仁,建议离开这个行业另谋高就为好。”
文中,徐永光建议全国人大就互联网公益募捐修法或释法,把互联网使用权还给慈善组织。他坚定地认为,每一个慈善组织都是互联网公益的主体,拥有自由使用这个工具的权利,同样可以自主选择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互联网公益的合作、开发和创新。“相信市场力量,相信民间自律,解放互联网公益生产力,实乃中国慈善事业突破困境的底线选择。”
徐永光将希望寄托在青年上,他说公益仍然非常不开放,未来要靠青年人“搅局”。因为青年是互联网一代,思维方式天然契合创新,而且他们的社会创新在专业性、情怀和目标的统一上都强于老一辈。他说,“青年作为公益变革的主角登上舞台势不可当。”
在2018年凤凰公益行动者联盟颁奖盛典上,徐永光指着自己和身边的陈越光(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说:“我和越光都六七十岁了,可是这种场合还是我们出来讲话、露脸,看不见年轻人,这是有问题的。”
2018年,徐永光在杭州被95后姑娘杜心童的自信心和能力震撼了。杜心童是播音专业出身,创立了一家致力于矫正语音的机构,一年内服务了240名患者,影响辐射了600多人,其机构广告还出现在纳斯达克的屏幕上。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科室,一年服务一般不过80人。初生牛犊冲老江湖说:“我们必须有做好的决心,才有排除万难的勇气,在命运的抗争中我们赢了,真好!”
每年徐永光都要接触几百名青年创新者,与他们深谈,帮他们解决困境。“青年创新需要资源的支持、需要信任和鼓励,也要给他们犯错误的机会。”
2019年,希望工程迎来成立30年的大周期。在中国的文化里,3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虽然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但作为中国公益行业的“拓荒者”和“带头大哥”式的人物,徐永光会被从各种角度评论。
上世纪90年代就成为希望工程志愿者的陈越光认为,徐永光在中国公益行业的地位主要有两个:首先是行业的先行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希望工程在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一枝独秀,“我们都受到了永光的影响。他做中国青基会的时候,我们都去支持他。”其次,徐永光胸怀开阔,愿意成全所有人。“永光是个愿意托起别人的人,这种品质在我们这个时代是稀有品,极为可贵。”也正是因为这种品质,徐永光常常被人调侃——“永光说好的人,可未必真的是好的。但永光说不好的人,那我们肯定不要理他了”。现在,徐永光更多的是想托起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