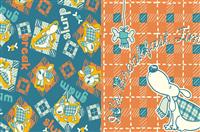
一.过于骄纵的童年,给我的成长埋下了不良的种子
1982年10月,我出生于皖南山区的一个小县城里。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五个姐姐。因为是独子,父母对我当然是疼爱有加,家里几个懂事的姐姐对我也是百般呵护,凡是我想要的,父母和姐姐们都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我。这使得我在童年时代就已经间接地养成了一种蛮横霸道,唯我独尊的不良性格。常常倚仗着自己在家里得宠的身份与地位,对街坊邻居的小孩极尽刁难欺侮之能事,到处惹是生非。四岁那年,当我用一只小号汽水瓶敲破邻居小朋友的额头之后,为人师表的父母才陡然意识到:再不对这个顽劣的孩子进行严格教育的话,迟早会给家庭与社会造成麻烦。于是忍痛将我送到乡下外婆的住处,一心指望艰苦的农村生活能磨平我身上的娇气与暴戾。
父母的这种善意举措,让受宠和放任惯了的我认为:这是他们对我进行的一种恶毒惩罚。这使我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偏执而狭隘的反叛意识。陌生的农村生活给我带来很大的打击。相比那些更加顽皮的乡下孩子,我只有受欺负受打击的份儿,而年迈的外婆整天又忙于家务与农务,根本就没什么时间去处理我被其他小孩欺侮的事情。因此,我愈加憎恨起父母对我进行的流放政策。一年后,外婆将我送回到县城的家中。因为怨恨,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坚持不和父母姐姐们说话。
上学后,我开始将胸中抑郁下的怨气撒向其他小同学,读书不用功,成绩平平不说,可调皮捣蛋、打架闹事却成了我的拿手好戏。当学校老师和其他学生的家长们找到我家门上时,我的父母开始为此大伤脑筋。处理掉学生家长和学校老师的状纸后,父母当然要对我进行一些口头或者手头上的教育,但我对此毫无认错意识。而我越是不服管教,我的父母便越是狠下心肠对我严格控制,并针对我的状况,制定了很多相应的防范措施。比如限制我的活动自由,限制我的作息时间。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发展到最后,恨铁不成钢的父亲甚至对我拳打脚踢。而性格已经偏于内向的我则对家庭和亲人更加地充满怨恨。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我的恶劣行为以及种种不同于常人的叛逆心理,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在家里郁郁不得宠,在学校里又早已经声名狼藉。同学当中,除了一些跟我臭味相投的害群之马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朋友。而各科老师则早已将我列为三不管对象。上课时有我没我根本引不起任何一位老师的反应。我就读学校的中学校长甚至有些无奈地这样对我说:“只要你不犯大的错误,不被街道派出所抓去败坏我们学校的声誉,我保证给你一张高中毕业证,哪怕你每门功课都是零蛋——但是,这可能吗?你就这样继续放纵下去的话,迟早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得到校长这样的评判与承诺,懵懵懂懂的我自以为是地笑了。我甚至以为这是一种多年以来自己和家庭、父母、同学、老师以及学校作不懈斗争的光荣胜利。然而没过半年,我就因为持械伤人、结伙斗殴被绳之以法。颇有远见的校长半年前对我的评判则成了一个可怕的谶语。我异常清晰地记得,那是1996年6月——离校长发高中毕业证书给我的时间最多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二.年少轻狂,遁入黑暗才是光明的开始
被当地看守所羁押了整整半年之后,我因故意伤害罪,被神圣的法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押送到少管所,在一本花名册上签完我的名字后,少管所里的教官示意我可以使用他办公桌上的电话,他让我通知直系亲属,汇报我已经被当地干警平安送到这座少年犯监狱里。
我用一生最难以言状的心情拨通一组号码。然后,在吱啦吱啦的电波声里,我听出了母亲的惊恐与哭泣。她一直梦想着我能一帆风顺地考上理想的大学,像我的几位姐姐们一样成为天之骄子。母亲说,如果是考上大学,哪怕我走的再远她也不会伤心难过。然后是父亲的声音,我听出他好像在小声地斥责着母亲。从小我就能够感受得出,我的父亲和我一样是个具有叛逆思维的男人,他的野心是要把我发配到电影里的大西北或者北大荒去。可惜他一生刚直,却毫无半点权势可弄。我拿着话筒,非常尴尬地感受着母亲的悲伤,我是她用血水酿造出来的一个物体啊,我怎么感觉不到她的悲伤呢?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只好尴尬地挂断电话,跟随着一名表情麻木的老犯人进入自己的监房。
刚进少管所的那些晚上,我整夜整夜睡不着。不敢长时间地看着某一个人,也不敢找他们说话。我一进去就得了一种失眠症。我真的不知道漫长的四年要怎样才能熬到头。我想过用手挖一条地道爬出去,想过龙卷风把房顶和围墙都卷掉了,再顺便把我也给卷出去,想过七仙女或者白骨精们能看中我,飞进来把我变成一个小玩意带出去,还想过洪水来了,教官领着大家集体朝外跑,然后我跑着跑着就跑回家来。我用几个失眠的夜晚,把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都想到了。可我那都是痴心妄想,是穷人盼发财,是傻子望天塌。我能做的事就是规规矩矩坐牢,踏踏实实改造。用管教干部们的话说就是: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你们肮脏的灵魂。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改恶从善才能立功减刑早日新生。
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是第二年的冬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那年冬天之前,我通过电视和报纸看到了我国教育部门又一次提高了退休教师生活待遇的报道,那时候我的内心确实感受到了一种欣喜和安慰。我开始觉得我们的国家是个逐渐强大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也是个健康发展的社会。这种感觉来得非常真诚。
冬天,我们列队从车间回到大院,相比屋外呼呼的北风,拥挤在温暖的监房里打盹或者说笑就会显得非常幸福甚至奢侈。往往是十几个光溜溜的小脑袋互相抵在一起,说些劣质的黄色笑话或者各自早些年的风云,这一切看上去会显得非常和谐,像是青春没有遇到任何可感的阻力。但实际上,这种欢乐真的称不上是什么欢乐。从黄昏到夜色,从阴暗到光明,灯泡将我们交错重叠的影子投放到墙壁上。大多数人会处于一种焦虑的等待状态里。等待开饭或者熄灯就寝的哨声响起,等待明天的太阳或者乌云的出现。等待一个个具体的日子的消逝。除去这些,难有其他更具想象力的想法。偶尔,会在等待中等待着一种虚无、一种无法看清的东西,譬如等待着一辆绿色的邮车,让时间的信使替自己捎来一份上帝隐秘的信件。
尤其难忘,在冬天的夜晚,一个人躺在床上毫无节制地遐思。记得卡尔维诺有个小说叫《寒冬夜行人》,那时候我非常喜欢,总是反过来复过去地看。现在想起来,很可能是因为当时贫瘠、枯燥、周而复始又充满压力的监狱生活吧,反正这样正好可以培养我的趣味。在白天我们把身体献给监规以获取平安,在夜晚,则将内心举到书本的祭台。大量的阅读可以忘却很多具体的烦恼。
我的兄弟,来自全省各地,长短不一,肥瘦各异。他们操持着各地的方言和不同的脾性,生活的关系相互交叉,互为凹凸。任何一间号房里,每天都会发生很多的战争与友谊。在少年犯管教所服刑的整整四年时间里,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越狱逃跑。为了实施这个想法,我曾做了各种有效的准备,常常大汗淋漓地锻炼身体,并时刻都在蠢蠢欲动着。但不知是怎么了,我总是没勇气逾越一切有形的障碍,从入狱一直到刑满,越狱计划千百次诞生,也千百次流产。
三.挫折是福,有破灭,才会有重生
刑满释放后不到一年,我的父母就相继去世,姐姐们早在我服刑的那几年里就相继成人妇人母。回归后我才20岁但一无所长,为了生活,我只好跟几个老乡去上海的一个建筑工地干苦力。其实我也曾想过重新读书,想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更想进大学。可是莫名其妙的,我却很自卑,有些厌世的感觉。所谓家贫如洗,举目无亲,谋生无路,投靠无门。那段时间里很怕回家,最怕看到的就是亲戚朋友们对我白眼。在他们的眼里,我父母的相继去世似乎跟我有着不可抹杀的关系。为此我甚至想过自杀。
我刚上网的那段日子里,曾经和沈阳东北大学的一位女生网恋过。热恋过程里,对方非常武断地将我想象成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学生。这样弄得我很是尴尬,可是出于心理方面的阴暗,我居然默认了。可惜谎言是个非常折磨人的东西,欺骗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价值。比如我的过去,我觉得,隐瞒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即使有过短暂的满足但不会长久。一句话,谎言,欺骗所维系的东西,不可能得以长久。有个非常著名的诗人曾经这样说过:一辈子的虚伪是虔诚/一辈子的欺骗是满足。从诗人的本意出发,我想那绝对不会是怂恿大家以此去进行欺骗,去推崇虚伪。要是那样的话,这个诗人可能也不算什么好东西。
上海打工的日子里,我甚至显得比少管所的监狱生活还绝望。没事就上网发些玩世不恭或者万念俱灰的帖子,恰恰是那段日子,我认识了一位善良的姐姐。她的网名叫作鹤顶红,上海教育总署旗下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当她得知我的一些具体情况后,便一直在循循善诱地开导并鼓励我振作起来。然后她又连续刊登了我的几篇帖子,都是些苍白无力的文章,与其说是我原创,还不如说是被她彻底修改的。当我收到她以私人名义汇给我的二千元时,我懵了,因为任何一家杂志也不可能在稿件尚未刊登之前就寄稿费给作者。接着鹤姐姐就打电话给我,甚至亲自打车到了我正在上工的工地,和我们的工头简单通融了一番之后,她又把我带到了她们的杂志社里,她让我必须每个月都要给她写文章。然后又竭力向主编推荐我,让我给她们做见习编辑。我说我没那个道行说完我就跑了,从上海跑回安徽。
可我万万没想到,我回安徽没几天,鹤姐姐居然特地请假找到我家。人能逃过很多东西,却逃不过善良与期望。鹤姐姐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向我灌输一些浪子回头的典故,她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周处,讲欧·亨利,我终于被她讲得雄心勃发。最后与她一起再次回到上海,在杂志社见习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我正式开始写小说。几乎每个晚上,我都睡在杂志社的电脑桌前,当我用整整一年的晚上完成掉我的第一部处女长篇《无处可逃》时,面朝蓝天我直直地跪了下去。鹤姐姐看我情绪失控时几乎吓坏了,我却一把将她拥住,我说我终于从自己的监狱里逃了出来。
这两年里我曾奔波过不少地方,遇到很多善良而有趣的人们。当然也有坏蛋。对于成功与失败我的感触不多。唯一触心的事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抱怨,我看到社会上很多人都叫嚣着,要时光倒流,把生活重新来过一回。假若回头让我重新来过,我想我会以死相抗。因为我对自己无知的过去,已经非常刻骨地感受到了那是一种深深的羞耻。但不管怎样,我终于能够正视一切了。
从2001年上网到今天,我已经给不计其数的报纸杂志写过稿子,并陆续写出了四部长篇,累计大约有一百多万的文字了吧,这么个过程当然很累,但也感到非常快乐。今年5月,出版社的编辑把电话打到家里,通知我的《云端以上,水面以下》已经被列为〖红鹤文丛·80后青春小说炫势力〗主打长篇,由于我当时不在家,出版社编辑的电话是我姐接的,当我回家时,姐姐以一种极其兴奋的表情把这个消息转告给我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自己只是淡淡地回应了一句,说:“哦,我知道了。”见我一点儿都不开心的样子,姐姐有些担心,问我怎么了。我说太有压力感之后反而没什么具体压力了,这些年我都熬了过来,所以即使再迟点也没什么关系。
后记:目前的我仍在写作,我现在最想的,就是写作。写的时候不觉得,不写,我就会怅然若失。可我的计划总是会被一些杂志编辑们的约稿打乱。其实给报纸杂志写一些时尚甚至商业性的文章我并不讨厌。我既不是什么名人更不是什么名家。而且我也迫切需要源源不断地有钱进来。今后也许我会转行,也许还会这样枪手般地写下去。许多作家以及写手们说创作不累那都是假的。但在创作的过程里我确实可以感受到一种快乐与充实,就像脚在跑步而心却在唱歌那样。
早已失去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