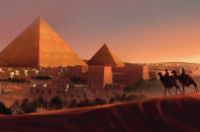
在古老的埃及,他们在医学卫生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可以说已经出现了医学的雏形。在古埃及,对于掩埋尸体、清洁居室、饮食、两性关系等等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说当年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完全是被宗教外衣的条文所约束的。当年埃及的医学与古巴比伦医学是经验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体,这为日后进展到科学医学莫定了可贵的基础。
有许多合乎卫生的条文,实际是来自魔术观念和教徒仪节。例如关于屠宰食用动物的法规,首先由祭司检查是否可以供祭祀,假若不适于祭祀之用,便也不准食用。
埃及关于祭司的身体清洁法规非常严厉,每日和每夜均需沐浴两次,每三日要剃一次头。在第三王朝时规定要按期完全剃光。祭司只准穿白色衣服,禁食某些食物,特别是猪肉和豆;只准饮用开水或滤过的水。
埃及的法令严禁人工流产和弃婴,不准经期性交,在《死者书》中,认为手淫是一种可耻的罪行。
值得一提的是埃及人的婴儿卫生。新生儿要裹以白麻布,但不缠紧。断乳以后喂牛乳,后加青菜。在五岁前不穿衣服,作种种合乎卫生的游戏(球类、铁环等);现今在埃及博物馆内还藏有自古墓出土的大量玩具。年长的儿童有多种运动。有极高的美容术,从古墓发掘中得知头发和指甲不仅使用香料而且还使用染料,脸上还涂胭脂等等。
二、干尸的技术获得很大发展
古埃及人相信死后活在另一世界,因而崇拜死者,所以竭力想法保存尸体。因此干尸的技术获得很大发展。
有一种受人尊重的人专门制作干尸(干尸技师)。尸体的切开由开尸人执行,他用石刀将尸体自左肋腹切开后即行逃去,在场的人则拾起石子作击打他的象征性动作。据希罗多德说,自鼻内将脑勾出,用药洗脑売。内脏有时扔弃在尼罗河内,有时用珍贵的雪花石膏做的瓶子(盖罐)盛起,随葬在墓内。
从第二十一王朝起,内脏则用麻布包襄,仍放在体内。心脏与大血管剥离极少见。尸体用浸过沥青类物质的麻布缠襄,如此可以保存得很好。
古埃及的医生行医受特殊法规的约束。医生在社会上和国家中的地位曾经明白规定,固然由于时代和地点的不同,他们的头衔和职责也不同,但也正可表示出这是经过很长和很慢的进展。
在古代所有各民族中,埃及以出名医闻名。荷马在《奥德赛》(第四卷第231行)中称赞埃及医学是最好的医学。希罗多德说:“医学技术分为各种专门,每个医生仅专治一种病。各地均有大批医生,有的治眼,有的治头,有的治牙,有的治肠,有的专治内科病”。赛丘勒斯说:“在远征或国内旅行时,所有病人皆可免费得到照顾。因为医生受社会的支持,并且按照古代很多名医所制定的医治法行医。倘若医生按照圣书条文医治而病人死亡时,任凭如何控诉仍可无罪;反之,若违背书中条文,则可处死。这是因为制定法律的人认为圣书条文为第一流专家所制定,是经过多年观察的治法,最合乎标准,没有人能超出这种范围”。
由此可知,在古代埃及医生构成了一种特殊阶层。他们常得到属于祭司一类的头衔,但这不能证明他们真是祭司。我们推想这类头衔来自古代,医生曾经享有显贵阶层拥有的尊荣与特权。
赛伊斯和希利俄波利斯的医学校附设于大庙内,但一切都是独立管理。赛伊斯学校的首长称为“太医”,同时又是赛伊斯特有的女神尼滋的祭司长,这一点可上湖到第三王朝(约公元前4000年)。在希利俄波利斯的奥西里斯学校,附设一疗养院,其中的医师长称为“大先知”。
在埃及最古医生的墓中有一个称为“最大先知”的医生的墓。在后于他几世纪所著的埃柏斯纸草文中记载他著有眼病药方。在墓碑(石柱)上记有得到祭司称号的医生的其他职务。在大金字塔的建筑家中有一官员的墓碑的官衔是“托特神庙卫生秘术监督”,另有一人称为“托特神庙薰香大殿监督”。在第四和第五王朝时也有“医师长”、 “宫廷顾问医师”等称号。又在第十一及第十二王朝时(约公元前2500年)有“圣庙大医”的称号,此名称也见于二千年后的二十六王朝。当时对于制药也同样有人监管,称为“配药司监督”。眼科医生时常提到,约公元前3500年,有一医学专家伊皮,他的称号是“宫廷治眼顾问”。
由此可见,在埃及最早有了一个组织完善的医学阶层。在更古的时代,此阶层大约是依附于高级祭司,但是后来在医学校、在附设于庙内的休养所和在公共卫生机构中,逐渐取得了自主的地位。
在医学校内保存了埃及的医经一类的书籍,而休养所则是来自各地的人集聚之处。至于医生墓碑上有祭司头衔,并无多大意义,不能据此认为医生是祭司,如果按真正的意思来讲,就如同现代国家赠给医生的荣誉称号一样。
当埃及被波斯人占领时期,医学和其它艺术和科学一样,也衰落下去。虽然新战胜者曾想保存古代文化,而且后来在托勒密时代,恢复了一些古代医学传统,但是埃及医学仍然衰落下去,成了那些魔术师、卖药人和江湖医的生意经,他们仅仅保存了古代医学的神秘外衣。
东方医学中心到帝国晚期转移到孟菲斯,但已失去了重要性;只有古代魔术医学和古代医学传统的一部分传入科普特医学内,我们从那不勒斯和都灵两地所保存的科普特草纸文中可以找到一些证据。至于埃及医学思想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部分,则于后来传给了希波克拉底学派。
研究埃及医学,可看出那些古代文献如埃柏斯和斯密司草纸文等所记录的医学知识,必是曾经若干世纪观察和研究而得出的总结。尽管我们还不能找出这最初的而已复杂的医学观念的来源,但是也绝不必考虑这些是某一个人的天才创作,或某一个民族的劳动成果,既使这个民族已存在了数百年。
很显然,能有这样复杂而辉煌的成就,且具有深奥的心理知识和广泛的社会性思想,必定是远古人民多年研究的结果,不过他们已无其它史迹留传了。
埃及文化留给我们的印象似较巴比伦文化为深,这或者是由于埃及文物遗存较多,我们知之较详之故。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医学是构成建筑学、宗教、政治等一系列文化的一部门,各种文明都是如此。这一文化宝库显然是由各种不同的来源和不同的时代所构成,今天我们对它的了解比以往更多,也就更使我们赞叹不已。
埃及文化由于其地理位置,与远近各民族多有贸易往来,当然易受这些民族的影响,再加上气候和土地肥沃等条件,明显地带有所有这些方面的痕迹。他们的医学思想的发展,一方面带有新颖和创造性的观察,另一方面则具有严格的法典式作风而拘于仪礼,其原因也在于此。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发展过程是来自埃及人的心理状态,就我们所知,埃及人一方面富于思考力,研究自由,观察深刻;但另一方面,在保存和传授知识成果上则有保守倾向,贵族阶级垄断了知识,给它蒙上了传统、神秘和仪式的面纱,秘而不宣。
古埃及的医学表现为一个复合的整体,正如庙宇大柱上的王候武士的雕像一样:真实,带有人种上的特点,但是一个挨着一个,全然没有考虑到配景的原则,且线条生硬。也如埋藏在庄严巨大的金字塔内的木乃伊一般:它在观察细节方面是精确的,甚至是天才的;在传播卫生律法方面是有远见的,机敏的;在制订社会措施方面是聪慧而深刻的,但是,它却死板地把一切知识宝物藏起,只有头脑清晰的这方面的专家才能知其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