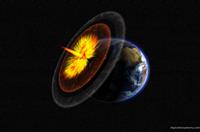一
现存苏轼词作三百余首,以他被贬黄州为界,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在密州的作品,于苏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关键作用,标志着走向别开生面、自成一家的新阶段。
熙宁七年(1074),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至熙宁九年十二月诏命移知河中府,在密州生活了整整两年,其间共填词二十一首,比起杭州任内三年的四十九首①,虽然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有所拓展。
在杭州时,苏词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送别寄远、怀人忆旧和赠答酬和一类叙写友情的作品,其余则属探春、观潮等写景记游方面的。赠答、送别、怀远、忆旧本是诗的题材,前此的词坛较少见,从苏轼开始才较大量地扩展至词的领地。在密州的二年中,苏轼除继续写下一批充满深情厚意的送别寄远词(其中有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外,更写出抒写报国胸怀的出猎词、情真意挚的悼亡词和歌咏田园风光的农村词。
有宋一代,名为“隆宋”,实是积贫积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臣范仲淹,借鉴唐代边塞诗,写下苍凉悲壮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此时,诗风革新运动尚未深入发展,而范仲淹也终究不是文学之士,欧阳修戏呼为“穷塞主之词”,在婉约词风笼罩下的词坛上,尚未产生巨大影响。后来,欧阳修写了一组咏十二月节令的《渔家傲》,最后一首是描写出猎的②,虽豪放不及苏词,也可谓猎词的先驱,但仅止咏景叙事,且夹杂在组词之内,并不特别引人注目。而苏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以出猎抒写爱国情怀,高昂激烈,别开生面,开启了南宋时期爱国抗战词之先声。
在诗歌中,最早叙写悼念亡妻之情的是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其后的五、六百年间,陆续有不少诗人写过这类诗歌,如李商隐的《嫦娥》、元稹的《六年春遣怀八首》等,都是其中优秀的篇目。到了宋代,诗偏重于“言志”、写景、咏物,除了象陆游的《沈园》、李壁的《悼亡》等极为少见的诗作外,歌咏男女之情的题材,早已被排除出五七言诗,让给词体了。可是宋代男性词人也象晚唐五代一样,儿女私情仅限于闺妇怨情、相思别离以及偎香倚翠、偷情幽欢之类,笔触柔美恻艳,而象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深婉而质直、以浅显之语写出真挚感情的词章,着实并不多见。
一般都认为,苏轼是在元丰元年(1078)才写下著名的五首农村词《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的,其实早在两年前(即熙宁九年),他已作有《望江南》:
春已老,春服几时成。曲水浪低蕉叶稳,舞雩风软纻罗轻。酣咏乐升平。微雨过,何处不春耕;百舌无言桃李尽,柘林深处鹁鸪鸣。春色属芜菁。
描写出淳厚的胶西农村景象,向词坛吹来一股清新质朴的新鲜空气。
青年时代的苏轼很少涉猎词的创作,大概因为词需合乐,而他那时还不大通律,他在给堂兄子明的信上说:“记得应举时,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作词”(《与子明兄》),所以不敢贸然从事。今存最早的一首词作,可能是治平元年(1064)二十九岁时写的《华清引》③,而大量写作却是十年后在杭州通判任上④。究其原因,第一,可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努力,他已掌握了词调音律,所作的词不仅能合乐而歌⑤,而且他自己还击节而唱⑥,因而他便放手去写。其次,他到杭州后,结识了退居湖州的老词人张先,并且和友人们可能组织了类似词社的团体⑦,经常聚会唱和,推动了苏轼创作词的兴趣。第三,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和钱塘雄伟的江潮吸引着苏轼,使他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词的形式记叙下这优美的景物,如他三年三次观潮,每次都作词记下深切的感受⑧。
苏轼通判杭州时的词作,不同于一般婉约词人的轻靡浓艳,而是清丽疏放,但存留着欧阳修、张先、柳永等的影响和痕迹,未能自成一家。例如《瑞鹧鸪•咏潮》,虽写出豪兴奔放的情怀,然拿它与受苏轼赞赏过的潘阆《酒泉子》(其十)“长忆观潮”相比较,并没有超脱潘词的词意而建立起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意境。密州时期的词作就不同了,它开始形成了不同于前人的独具的豪放超旷的艺术风格而横绝于世。
范仲淹的《渔家傲》慷慨沉郁,终不免带着凄清衰飒的味道,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不仅描绘了射猎的壮阔场面,而且还抒写出杀敌报国的壮志豪情,他对这类豪放词颇为得意,在《与鲜于子骏》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所以还“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颇壮观也。”后来,到了徐州又相继写了同样风格、内容的《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浣溪沙》“旌旆满江湖”等词作。
与此同时,苏轼还写了格调超旷的词作《望江南•超然台作》,词人在“风细柳斜斜”的春色中,登上超然台远眺,看到“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的秀美空濛的景色,触动了乡思之情,然而欲归不能,但他没有因此而肠断魂消,而是“且将新火试新茶”,来一个“诗酒趁年华”。看,词人的胸襟是何等的超然旷达啊!
豪放和超旷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可是它们同属阳刚的范畴,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有时常常还互相包容。顾名思义,豪放应该包含着豪迈和狂放两个方面;而超旷义指超脱通达。在无所拘束、自由自在这一点上,豪放和超旷有其相通的地方。
苏轼的豪放风格是建立在积极进取、洒脱达观的思想基础上的,儒家的入世、“致君尧舜”是苏轼的主导思想,但同时他也深受佛道思想影响,所以当他在仕宦道路上遭受打击、迫害之时,却能随遇而安,既不蛮干硬拚,又不消沉隐世,而是以旷达的态度解脱苦闷,“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在苏轼身上,豪放与超旷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现;在词作中,这两种风格也往往结合在一起,有时以豪放为主,有时以超旷为主,有时则二者并重。
第一类的如《念奴娇•亦壁怀古》,东坡以激昂的豪情描绘雄伟的江山,高歌赞颂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也抒发了自己被贬谪的郁愤和感慨,词中在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的同时,也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伤色彩和借酒浇愁、故作旷达的情绪。所以词的意境雄放中有清旷。
第二类可以《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为代表,词人在穿林打叶的风雨声中,吟啸而徐行,毫无畏惧。因为,风风雨雨对他说来早已司空见惯、处之泰然了。这首词充分表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胸襟,而“何妨”、“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不也带着东坡特有的狂放不羁的精神特征吗?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妨看作豪放、超旷并重的词作,作者由“把酒问青天”而“我欲乘风归去”,最后仍“何似在人间”;又由责问明月“何事长向别时圆”而设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豁然开朗,提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理想,境界开阔奔放、神奇壮美,情怀超逸高远、旷达乐观。
此外,苏词中尚有婉约、豪放兼具,或婉约、超旷并存的。这里不再一一细述。
夏敬观《吷庵手批东坡词》云:“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慨,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叶嘉莹先生很赞成这一段论说,认为这是“将苏词的超旷之特质分为二类,一类为全然放旷,‘激昂排宕’之近于粗豪者,为第二乘;另一类则是如‘天风海涛之曲’具有超旷之特质,却并不流于粗豪,而‘中多幽咽怨断之音’者,为苏词之上乘。”(“灵溪词说•论苏轼词》)⑨按照叶先生的看法,豪放应纳于超旷之中(至于“第一乘”、“第二乘”是另一个问题,可以别作讨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豪放与超旷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谁也不能把对方包容在自己的名下。苏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但从苏轼的偏爱(下文还要提及)、苏词的主要特征、它在词史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以及东坡乐府的代表作几个方面来考虑,我们认为,关于苏词的风格问题,与其把豪放纳入于超旷之内或将超旷归在豪放之中,不如豪放、超旷并存。这个意见可能并不正确,提出来请批评指正。
二
词原是作为歌(曲子)词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功能是遣宾娱兴,内容不外描写花月闺情、绮罗香泽一类的生活和生老死别、悲欢离合的人生感叹,作者往往把自己的面貌和个性隐藏起来,形成千人一面、异口同声的局面,所以,有不少词人(例如冯延已、晏殊、欧阳修三人)的作品,常常与他人的篇目相混。
苏轼写词与写诗一样,多是为时为事有感而作,不仅如此,更把对人生和社会的感受,把心灵深处的隐秘,毫不隐瞒和掩饰地,直截了当地吐露出来,即使含蓄,也是曲笔地直抒胸臆,让人们清楚明白地看到词人的个性品质、思想修养、胸襟怀抱、他的爱和憎、他的喜怒哀乐。苏轼在密州两年的词作,不只是他这一时期生活的写照,还是他思想心态的写照。
苏轼从繁华热闹的杭州,一下来到荒凉萧条的密州,其寂寞、苦闷的心情于到此后不久写下的那首《蝶恋花•密州上元》词里可见一斑。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贫困,加上密州连年蝗旱灾荒,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就在元宵节之后的第五天,苏轼梦见了分离十年的亡妻,十年的宦海浮沉,更增添了他对亡妻的缅怀,于是饱蘸深情,挥笔写下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那首千秋传诵的悼亡词。词中把对亡妻深沉真切的悼念与仕途凄凉失意之情委婉曲折地交织融汇在一起。当然,苏轼并没有因此而消极颓废下去,他对灾难深重的密州人民给予深切的同情,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灭蝗赈济,减轻百姓负担,恢复农业生产。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使百姓的生活转危为安。他在密州的第二年暮春,心情欢快地写下歌唱田园风光的《望江南》“春已老”。特别使苏轼振奋的是,在祭祀常山以后,他与同事和猎户,习射铁沟,写下意气奋发、豪壮遒劲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表达了抵御外寇、卫国保家的雄心壮志。
但是,理想终归是理想,苏轼外放到偏僻的小城,无法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因而,“进”与“退”、“仕”与“隐”、出世与入世,始终在矛盾着,他的思想始终是不平静的。熙宁九年初春,因劳瘁而病后初愈的苏轼,曾写下一首《一丛花•初春病起》,词中说:尽管桃际花边已微露春意,桃李争先微绽,游人们都在作寻芳的打算,而词人却因衰病少欢愉,有点心灰意懒,便“疏慵自放,惟爱高眠。”他在送别被免职的诸城知县赵昶归海州时,写了首《减字木兰花》临别赠言,词中说:“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是劝勉赵昶,也是苏轼自己的夙愿。⑩然而,居苏轼思想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的淑世精神,虽然“我欲乘风归去”,想找个出世的理想世界,但“高处不胜寒”,他毕竟更热爱人世,所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以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勉慰弟弟苏辙和朋友们。
苏轼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亲人(妻子、弟弟),也热爱友人,热爱生活。他看到梅花盛开,就想象自己和好友在一起,“痛饮又能诗,坐客毛毡不知醉”(《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好友章传武将离去,苏轼写下《江城子•东武雪中送客》,深情地说:“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少清饮。”刚到密州时,苏轼因地方连年旱蝗灾重,所以一连几个月斋素,牡丹花开也无心观赏。到了秋末,牡丹突然又开出一朵花,苏轼闻讯,特地在雨中置酒邀客,乘兴作了《雨中花慢》,词人认为这次“高会”虽能“聊追短景”,可是这清商秋风不会使牡丹“余妍”永久延续,所以希望天公“不如留取,十分春意,付与明年。”让美好的春花永远留存在人世间。
在密州短短的两年间,苏轼已与同事们、当地百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熙宁九年冬,当苏轼得知自己将离开密州赴河中,晚登超然台望月,黯然神伤,多情地叮咛:“莫使忽忽云雨散,今庭里,月婵娟。……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
苏轼在密州时的词,采用以赋为主体的写法,直抒胸臆,情真意深,活画出苏髯品格风貌,虎虎有神,别开生面。
刘熙载《艺概•诗概》中说:“唐诗以情韵气格胜,宋苏黄皆以意胜。”苏轼的诗善于把情、景、理三者熔铸成一体,通过景物或事件本身揭示出哲理意趣,具有丰富的“象外之象”和“言外之意”。苏词也象他的诗一样,不满足于一般的情境交融的意境,而是追求一种新意妙理,用苏轼自己的话说,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这种情、景、理交融的意趣,在之后的黄州时期,由于他贬谪生活的特点和对人生哲理的彻悟,于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而密州时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早已显露出这一特色,而且写得特别成功。
《水调歌头》不仅以想象丰富、境界开阔、充满逸怀浩气吸引着读者,还以富于哲理情趣、意蕴深邃隽永而获得人们喜爱。词人在上片以遨游仙境,出入于天上人间,巧妙地表达出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隐与仕的矛盾。下片以月照无眠,引出“何事长向别时圆”的恨语,再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转出“此事古难全”的自然规律,作为宽语,最后又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一切经受离别苦难的人们表示美好的祝愿。全词妙语连珠,发人深省,委曲深婉,一唱三叹,尤其是结语,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我们不妨把它与苏轼赴密州途中寄子由的《沁园春》作一比较:此词上片写景以况旅途艰辛,引出“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的感慨,下片搬用诗、文、经、史的典事,直接议论。虽然上下片转化自然,写得也很出色,但终是两截。下片以议论入词,直抒胸臆,也不及《水调歌头》那样将物境、事理、人情融合得浑然一体,结句“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相近,可是总觉得缺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这种耐人寻味的光彩。
三
苏轼提倡艺术风格多样化,他说过:“短长肥瘦各有态”(《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对“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李太白、杜子美的“英玮绝世之姿”,“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等不同风格各不偏废,他都学习继承,并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求新,力求“能自出新意”(《书唐氏六家书后》),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他不鄙薄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的风格也多样化。然而,在各种不同的风格中,又特别崇尚自然奔放,这与他的文艺主张是相一致的,他认为创作要做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并多次说过这样的意思:“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评文》)。既要求天然浑成、变化多端,又要求纵横姿肆、气势磅礴,正如他所赞赏的吴道子的画那样:“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王维吴道子画》)能雄浑奔放,挥洒自如。
与对待其它艺术的态度一样,苏轼不忽视词的风格应该多样化,对于张先“微词宛转”(《祭张子野文》),黄庭坚词的“清新婉丽”(《跋黔安居士渔父词》),都是以赞赏态度来评论的。而且在创作实践上,苏词风格的多样性也是人所共知的。苏轼把词看作是“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就是说诗词本是一家,所以敢于突破一般人把“婉约”视为“正宗”的藩篱,要“自是一家”。
他所说的“自是一家”,不是别的,正是不带“柳七郎风味”,是《江城子•密州出猎》式的豪放风格,也即他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革新创造,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一提起豪放,人们很容明把它与粗豪叫嚣联系起来,所以,后来苏轼在元祐初的《答李季常书》中告诫说:不要“豪放太过”,应该是“句句警拔,诗人之雄”。他在创作实践上,也努力将豪放与超旷结合起来,这一点从他对柳永词的评论上可以得到印证。苏轼对柳词是有所不满的,可是柳永《八声甘州》词中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数句,则受到苏轼的大为赞赏,称“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赵令畴《侯鲭录》引)。所谓“唐人高处”,就是指气象开阔,笔力遒劲,境界悲壮高远,这与豪放超旷的风格是相近的。
“论词莫先品”,“诗品出于人品”(《刘熙载《艺概》语)。苏轼豪放超旷的词风与其思想、品格和个性、气质是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说,人品是词风的基础,词风是人品的体现。明袁中道有一篇《次苏子瞻先后事》,拿苏轼与轼辙作对比谈论风格即人的问题:子瞻“少为人雄快俊爽,内无隐情。闻人一善,赞叹不遑;而刚肠疾恶,又善谑笑,锋刃甚利。子由恂恂然,寡言慎重,捐介自守,不妄交游,……而其为文,大略如其为人。子瞻豪肆汪洋,子由冲和平衍。”
苏轼是位思想较为复杂的文人士大夫,儒家思想是基础,又杂有很深的佛道思想。正统的儒家思想,使他有抱负、有理想、有勇于革新进取和积极的淑世精神;他为人耿介刚正,胸襟坦荡,光明磊落,风节凛然;他敢说敢为,直言不讳,自知“平生文字为吾累”,然一遇到危害国计民生之事,仍不顾个人利害得失,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而佛道思想则又使他追求真率自然,不受事物的羁绊,形成狂放不羁和通达酒脱的个性,所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苏轼《论修养帖寄子由》),豪放和超旷在苏轼身上常常互为表里,紧相结合。
他从杭州来到号称“山东第二州”的密州,满以为生活可以过得去,不料“斋厨索然,不堪忧,”不得不同通判宋廷式两人,经常“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但他并不以为苦,却是“扪腹而笑”,并且作赋解嘲: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登过酉,曾怀酒之不设,揽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著噎呕。……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吾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后杞菊赋一首并叙》)
苏轼为人、为文,为诗、为词,都贯串着这种豪爽任真,达观乐天的精神。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自然景物、地理环境对于作家的情感、作品风貌的形成,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四川奇险的山川风光培育着包括苏轼在内的历代诗人豪迈雄放、飘逸超旷的个性品格,正如陆游所说的“挥毫留得江山助”(《……偶读旧稿有感》)。
熙宁四年,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放,离开京城出任杭州通判。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失意不顺心,可是,江南胜地的杭州有秀美的西湖,不但可以赏心悦耳,而且宜于赋写清新明丽的小词。其中每年一次的观湖,排奡雄伟的江潮均激起词人的豪情,乘兴写下笔力矫健、气象开阔的作品,但刹那间的激情消失以后,便又恢复到平时的平静宁谧,他与太守、好友、词人们歌酒往返,欢倾友情,留连风光,兴到神会,一首首清丽疏俊的词作即席而出。
到了密州,境况就大不相同了。境内山川缭绕,桑麻遍野,“山城寂寞”,“风俗武悍”,与繁华、柔美的杭州形成强烈的对比。词境在诗人笔下显得凄楚悲凉:“珠桧丝杉冷欲霜,山城歌舞助凄凉”(《浣溪沙•九月九日》)。但也有令人振奋的,初冬季节,“城东坡陇何所似?风吹海涛低复起。”山峦起伏,如惊风骇涛。“春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祭常山回小猎》)。看到会猎的宏伟场面,激起词人的豪情壮志,纵笔写下劲健有力、铿锵有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州署的西北有园名西园,它北靠城墙。苏轼把城墙上的旧亭稍稍修葺,按他弟弟取的名称为超然台。他经常登台远眺,“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威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超然台记》)。“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心雕龙、物色》)。空渺绵远的山水遗迹,引起苏轼对人生、社会作哲理性的思考,从钱塘到胶西,风物迥异,要“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要有超然尘外、不为物累的达观态度,正如十八年前离蜀赴京师时写的一首诗里所说的那样:“无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入峡喜巉岩,出峡喜平旷”(《出峡》)。熙宁九年中秋,登超然台赏月,触景生情,苏轼不禁浮想联翩,原来他在杭州任满时,请求调到离弟弟苏辙(时在济南)较近的地方,以便常能相见。不料,经由润州、海州、至密州时,却不能绕道济南。后来当他知道即将离任,移知河中府时,苏辙也罢齐州掌书记而回京,又无法见面。至此,感情特别深厚的兄弟俩已有五年没有聚会过一次。仕宦的失意、理想的破灭、弟兄的离别,种种不顺心的情绪再次袭上心头,而超然台上山川风土的感召,使他重度“游于物外之境”,写下这篇“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处”(胡寅《酒边词序》)的杰作。
注释:
①据石声淮、唐玲玲笺注的《东坡乐府笺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非编年词无年月可考,无法计入。
②全词是:“十二月,严凝天地闭。莫嫌台榭无花卉,惟有酒能欺雪意,增豪气,直教耳热笙歌沸。陇上雕鞍惟数骑,猎围半合新霜里,霜重鼓声寒不起,千人指,马前一雁寒空坠。”
③见《东坡乐府笺注》第3页。
④熙宁五年二首,六年六首,七年四十一首。
⑤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在密州曾“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与鲜于子骏》)。
⑥如《阳关曲》“云收尽溢清寒”一词,《书彭城观月诗》云:“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方迁岭表,犹歌此曲……”(《苏轼文集》卷六十八)。
⑦参见西纪昭《苏轼初期的送别词》(《词学》第二辑)。
⑧这三首词是:《南歌子》“海上乘槎侣”,《瑞鹧鸪》“碧山影里小红旗”,《南歌子》“苒苒中秋过”。
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⑩早在十五年前,苏轼初进仕途,签判风翔时,于《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中就提出共同偕隐之志:“寒灯相对见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后赴通判杭州任,途中游镇江金山寺,夜见江心炬火,便向神盟誓:“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寺》)翌年在杭州给老师欧阳修等的和诗中又说:“何日扬雄一廛足,却追范蠡五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