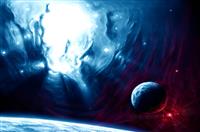陈寅恪生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不仅是社会、政治的转型,更是文化上的转型,他目睹、身历时代的大变,从陈家深深卷入其中的维新运动到倾覆王朝的辛亥革命,从他不无异议的“五四”新文化浪潮到抗日战争,到1949年的天翻地覆,直到“文革”,他没有因为令人目眩的时代剧变而眼花缭乱,他早已打定主意、立定脚跟,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做一个学人,他在意的是追求知识的自由,追求学术的独立,王国维之死让他痛心不已,他写下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至高评语,实际上是自我勉励,无论外在的社会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要执著地追求内心的这种自由和独立。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入世和消极遁世之间,他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他处处讲求独立见解、自由意志,反对人云亦云、随大流、跟新潮。他有过长期的留学生涯,明明精通多种语言,对西方文化非常熟悉,治学的路径也超越了传统的旧方法,却执拗地使用文言文,出书一定要直排、繁体字,这种形式上的守护已成了他捍卫文化传统的最后一步,他不想再往后退,这种心态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的。
陈寅恪一生总是笼罩着一层阴郁,他的命运几乎早已注定,从他少年时目睹父亲陈三立、祖父陈宝箴维新失败被革职,黯然离开长沙的那一刻起,或许就使他的身世蒙上了那种伤感的气氛。年轻时代他一心求学,从此在学术中寻求安慰,晚年只剩颂红妆,显然是别有怀抱、寄托遥深,他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柳如是的身上,她的身世和生命浮沉、尤其是她令人怜惜的才华,遭逢时代的转型,那种花开花落的无可奈何,那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无力感,那种美好的一切一点点被碾成齑粉的伤心……一代学人感慨的岂是一个几百年前的弱女子,分明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一个文人,哪怕有天纵之才,满肚子的学问,也挡不住时代方向的转换。他知道人生的有限性,知识的无限性,他有着强烈的身世之感,他敏感地呼吸到了绵延几千年的文化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他是这种文化的托命之人。他在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中寻找社会变迁的轨迹,在旧体诗中感怀人生,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不是一个学人的学问、才气,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气,是追求知识的自由、捍卫学术的独立性,他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守护这样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他留给世间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那些有形的文字著述,而是无形的人格遗产(其中包含个性、人格完整性),是一个人傲然独立的精神风貌,那才是他穿越时空的力量所在。
在算得上知己之交的吴宓身上,我们也能看到陈寅恪的影子,他们最终都是脚跛、眼盲,在凄凉中告别人间。更早,在自沉以终的王国维身上,他似乎也察觉了守护文化价值的悲剧性,但他依然认准了自己选择的道路。陈寅恪、吴宓他们大体上也是“五四”一代人,那真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回望“五四”,以往我们总是只看到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倡导新文化的胡适、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实践“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只看到齐集天安门前众声喧哗的学生们,我们往往忽略了在他们之外还有另外的声音、另外的身影、另外的追求,“五四”不是如此单一、武断的,“五四”是多元、开放、包容的,《新青年》、《新潮》之外有老牌的《东方杂志》、有同样新兴的《学衡》,杜亚泉的声音不能漠视,《学衡》一群的声音也不能不正视,任何一元化的一边倒的思维方式都隐含着一种风险。虽然陈寅恪那时远在异国求学,但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他与《学衡》一群心气相通,与胡适他们是有距离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甚至赏识,在旧体诗中寄托情怀的吴宓对新文学(如茅盾的小说《子夜》和徐志摩的新诗)都有公开的肯定和赞赏,他们没有偏见,他们只是有自己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建立在追求知识的自由基础上的。说到底,他们也是“五四”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与胡适、陈独秀等一同构成了那个多元的开放环境。
提起陈寅恪,或许人们会想起他那句洪钟落地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想起他的学究天人及“教授之教授”的称誉,不太有人会进一步留意他和他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不太有人把目光投向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其实,离开了那个时代,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陈寅恪、走近陈寅恪的内心,离开了陈寅恪的同时代与他相交很深的学者,将陈寅恪当作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孤零零的天才,我们更无法理解陈寅恪的追求,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在陈寅恪的身边有一批与他做人上相知、治学上可以商榷,并有着相似文化观的朋友,王国维、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杨树达、汤用彤……陈寅恪生活在他们中间,在和他们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中,获得生命的欢愉,学问的升华,人格的砥砺。他们热切地希望拥有追求知识的自由,他们几乎都是学贯中西,却又珍爱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吸收了西方的方法,却不愿臣服于西方的脚下,他们具备世界眼光,同时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情结。在一个急速西化的时代里,他们成为“不合时宜”的文化守护者,几乎是必然的宿命。是是非非,都得从头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