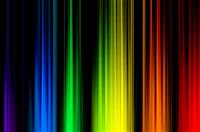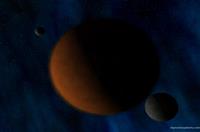【内容提要】林黑儿是义和团时期天津红灯照的首领,号称“黄莲圣母”。红灯照传奇故事曾经广为流传,有着强烈意识形态化的时代特征。尽管清廷保守派曾经认可、放纵义和团,但官方史料中有关“黄莲圣母”的记载却十分稀少。清末民初之人所写的野史、笔记中提及其人,往往捕风捉影、夸大其词。在现当代学者的论著中,多数是突出她在义和团运动中上阵杀敌的英勇表现,将她塑造为革命造反派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偶像、爱国主义的象征。事实上,“黄莲圣母”长期以来被赋予的多重身份——渔家女、圣母、邪匪与革命英雄——并不能确切概括其形象特征。本文力图探究林黑儿被神化的背景、过程与影响,将一百多年来人们对红灯照的描绘、被创造的作为“革命派”、“爱国者”的公共记忆与抛开意识形态面纱后的历史人物做对比分析,还原真实的“黄莲圣母”形象。
林黑儿,义和团时期天津红灯照的首领,号称“黄莲圣母”。她带领红灯女儿飞檐走壁、灭洋反教、治病疗伤的传奇故事流传广,影响大,长期以来具有模式化、意识形态化的特征。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审视、评价“黄莲圣母”这一形象呢?
尽管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保守派(当代中国史书称为顽固派)曾经认可、放纵义和团,但官方史料中有关红灯照、“黄莲圣母”的记载却十分稀少。清末民初之人所写的野史、笔记中提及其人其事,往往捕风捉影、夸大其词(1)。在现当代学者的论著中,多数是突出她在义和团运动中上阵杀敌的英勇表现,将她塑造为革命造反派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偶像、爱国主义的象征(2);也有学者,例如义和团研究专家王致中曾经写过一篇《“红灯照”考略》(3),对红灯照史实详加考订,客观评价,难能可贵。事实上,“黄莲圣母”长期以来被赋予的多重身份——渔家女、妓女、邪匪、圣母与革命英雄——并不能确切概括其形象特征。本文力图探究林黑儿被神化的背景、过程与影响,将多年来人们对红灯照的描绘、被创造的作为“革命派”、“爱国者”的公共记忆与抛开意识形态面纱后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还原真实的“黄莲圣母”形象。
一、从渔家女到“黄莲圣母”
红灯照作为义和团时期的妇女组织,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史料指明其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但一般认为,义和团在1900年春夏之交进入天津,发展迅速,红灯照随之出现:“闻现在津郡城厢内外,时有幼童练义和拳,又有幼女演练红灯照。此种陋风河东一带为尤甚,小营门内外亦有之,以致谣言四起。”(4)其后在陕西、山西以及东北等地均有红灯照活动的记载。相传除十几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女子组成红灯照外,成年妇女、老年妇女、寡妇和妓女分别组成蓝灯照、黑灯照、青灯照和花灯照。当时,民间对于练习红灯照者,有种种神秘描绘,“父母不能禁,常夜半启门,不知所往,有数日始返,有一去不复返。其返者,询何往,则曰至外洋焚洋楼也。”(5)从中可以看出,参加红灯照者人数众多,她们常在夜间活动,练习飞行和纵火术一类的武功,以反教灭洋为目的,是义和团的辅助力量。
红灯照宣称拥有刀枪不入、灵魂出窍的法术,当时百姓深信不疑。甚至义和团团民也认为,要对抗洋人,非红灯照莫属。在当时义和团依赖迷信思想和手段反帝灭教的情形下,出现红灯照借“女神下凡”的招数以振奋民心的现象不足为怪。
一般记载称,林黑儿幼时随父跑江湖卖艺,稍长,嫁与李姓船户之子,靠捕鱼运货谋生,生活贫苦;也有记载称,林黑儿系女巫、土娼。1900年,其父因触犯洋教,遭人毒打,伤重身死,适逢天津城内外有练红灯照者,林黑儿加入其中,很快成为首领,“拳匪谓其能通神,奉为‘黄莲圣母’,备极恭敬。裕禄亦崇信之,派遣道员谭文焕供应一切。”(6)至于林黑儿的年龄、相貌、丈夫及更多的家庭信息,至今无人知晓。但是,有关这位渔家女被“神化”的过程与活动,记载很多,且具有传奇色彩。
当时,林黑儿得到坎字团首领张德成的赏识,在其支持下组织红灯照,在静海独流镇设立坛口,做大师姐,不久欲在杨柳青设立坛口,遭当地地主石元士反对,未成。张德成在进入天津城之前建议她以“黄莲圣母”之名行事。随后,在6月的某一天,林黑儿率众从杨柳青乘舟去天津,途中,如同鬼神附体,她忽然把数百斤重的大盐包投入河中,口中自称“黄莲圣母”下凡,此事迅速哄传。到天津后,林黑儿将船停在北门外,用红绸将船围严,桅杆上悬挂着书有“黄莲圣母”字样的红色大旗,站立于船头船尾的红灯照姑娘,个个红衣红鞋,手持红灯。成千上万的百姓折服于这位拥有无边法力的“黄莲圣母”,聚集于运河两岸,焚香跪拜。林黑儿上岸后,身穿朝服的直隶总督裕禄将她迎入督署,尊崇有加。从此,林黑儿——黄莲圣母成为一位闪耀着传奇色彩的神灵,在侯家后归贾胡同北边的南运河上设坛授徒,人数达二三千人之多。每当举行仪式,“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烛清供,万众礼拜。”(7)这些虔诚的百姓都相信她是救苦救难、灭洋教的神仙。
黄莲圣母所率红灯照在天津城的活动集中于1900年6月到7月14日天津被八国联军攻陷的一个多月间,她们站岗放哨,游行街市,宣传“灭教”,救治伤员,查拿奸细,参与义和团的作战。黄莲圣母还凭借其影响力,承担了调节天津义和团各方利益的任务。具体来说,除了受人顶礼膜拜外,关于黄莲圣母在天津的事迹,史料记载的主要有:
一是参加义和团、清军在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发起的战斗。黄莲圣母率领红灯照在战斗中做后勤补给和给伤员治病疗伤之事(8),但是详细参战情况无从得知(目前尚未发现确切资料,只有文学作品中有生动的描述)。
二是“踩城”,即上街游行。“黄莲圣母”率领红灯照女儿头披红巾,身着红衣,脚穿红鞋,手持红扇、红灯,“每在街上行走,有二三十个男子相随,皆持洋枪,其妹三仙姑行走时,亦有二十余岁之男子数人跟随,传谕人等,皆须闭目不可看,于是皆敬之为神,焚香跪接焉。”(9)每十天左右游街一次,边走边舞,呼喊诸如“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10)等口号,对青年女子号召力很大。
三是为拳民治病疗伤,发放避弹符水。义和团有受枪伤的团民大都抬往黄莲圣母处求治,“其治法用香灰涂抹伤处,谓能止痛收口,故受枪伤者多抬往求治;不效,则曰此人平生有过处,神仙不佑,故不能好耳。”(11)
四是与裕禄联络交接。直隶总督裕禄是主张招抚义和团的一派,他除了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有联络外,还曾将“黄莲圣母”请到督署,求其保护。裕禄对黄莲圣母表现得十分恭敬,交谈时以尔汝相称,为她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黄莲圣母借此为义和团争取到不少军械粮草。
五是戏弄中堂少爷。1900年6月下旬,天津城告急,李鸿章之子、四品京堂李经述欲带贵重物品乘船回合肥老家,途中被红灯照截住,李经述递上名片,要求放行。红灯照指斥道:“你以为是官的儿子,就可违反义合拳的规定吗?”(12)命其“赤足着靴随去,到圣母舟中,呼之跪,即挺然遽跪,跪刻许方挥之使去。”(13)
关于天津陷落后黄莲圣母的最终去向,有多种说法。一说“黄莲圣母与三仙姑被人缚送都统衙门,正法完案”(14);一说她被八国联军俘获,“屡于都署询鞠,无甚要领,遂载往欧美各洲,以为玩物云”(15);又说她在天津陷落后不知所终。
二、创造革命记忆:“黄莲圣母”成为反帝爱国的象征
义和团时期,亲历者将“黄莲圣母”看作仙女下凡,对其焚香膜拜,对红灯照火攻、飞行、刀枪不入、举红灯灭洋舰的法术深信不疑。辛亥革命时期,黄莲圣母成为革命党人政治宣传的工具之一。进入民国,人们将这些法术、巫术看成是愚昧、落后、迷信的行为。1949年后,农民起义被抹上一层神圣光环,义和团——红灯照——“黄莲圣母”成为反帝爱国的革命象征。这种公共记忆的改变,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为“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他认为:“传统的发明”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16)。经历几个特殊时期后,巫术迷信色彩浓重的义和团女首领被推广为反帝爱国运动的民族女英雄,最终通过国家话语和建立纪念物的形式被创造完成。
辛亥革命时期,“黄莲圣母”最早被塑造为反帝爱国女英雄的形象。19世纪、20世纪之交,甲午战败,维新运动流产,义和团抵抗侵略失败,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17)孙中山等人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一批革命者和思想家以树立政治典范、加强舆论宣传的方式号召民众,在各地区创办报刊杂志,宣扬爱国与革命。其中,章太炎将“黄莲圣母”纳入“倡义起兵功烈卓著者”之列,并称“法兰西之革命,亦拥女优为自由神,与义和团之黄莲圣母何异者?”(18)章太炎把黄莲圣母与法国大革命中被尊为自由神的“女优”相类比是为了凭借“黄莲圣母”在民众中的号召力,传播爱国、革命、妇女解放的思想,为其政治宣传服务。
1949年后,在意识形态不断走向极“左”的过程中,中国史学界将“黄莲圣母”创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文革”以前对红灯照与黄莲圣母的研究论著尚少。“文革”开始后,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形而上学盛行,林彪、“四人帮”集团将史学扭曲为法西斯专政的工具,以历史的名义捏造历史,有关颂扬红灯照、黄莲圣母的文章迅速增多,红灯照摇身变成革命造反派,“黄莲圣母”成为红卫兵造反派学习的榜样,爱国主义的象征(19)。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黄莲圣母成为反抗封建孔孟之道、争取妇女解放的历史女英雄。黄莲圣母不但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被频频抬出,在中苏矛盾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抗中,义和团、红灯照与黄莲圣母在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爱国”功能也被无限放大,“黄莲圣母”形象被纳入国家话语体系,赋予革命、反帝、爱国的标记。
时至今日,这种影响力不仅牢固占据历史教科书领域,甚至在当今的义和团学术研究中依然存在,比如有的史学论著将义和团定义为“中国下层的劳苦人民,于此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掀起了一场声势迅猛的反帝爱国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给腐朽的封建王朝和外来的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20)。不少文史资料有关红灯照的文章均会提到“黄莲圣母”,继续将其塑造成民族英雄的形象,重点突出她上阵杀敌、英勇战斗的爱国精神,称赞她是领导中国妇女革命的光辉典范,红灯照是中国妇女革命史的组成部分(21)。至于黄莲圣母用巫术号召民众、盲目排外的行为,则予以掩盖和再造。1982年7月9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将“红灯照黄莲圣母停船场”遗址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4年8月在停船场设立“红灯照黄莲圣母停船场”纪念碑,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学者指出:“某种象征一旦形成,它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覆盖历史便不再重要。”(22)时至今日,具有国家意义的“黄莲圣母”,已从江湖艺人、渔家女、土娼、女巫的身份被改造为民族英雄,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且被社会大众所认同。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有关“黄莲圣母”的传统记忆被加以再创造,主要是为了符合当今政权自身的价值观,同时作为可以信手拈来的工具,不时祭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即便如此,我们却不得不警惕融入国家话语的“黄莲圣母”象征,利用的是清廷保守派与底层民众封建落后迷信的特质,维护的是愚昧保守反动的专制政权,造成的是民族——国家——民众陷于深重灾难。历史如镜,何其明晰!人造的“神圣光环”必须拂去。
三、还原“黄莲圣母”真相
作为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主人公,“黄莲圣母”一直被赋予神秘主义色彩。作为实际存在的个体,“黄莲圣母”形象在很长时期内被国家创造为爱国主义的象征。然而,“对待原有史学的内容,必须要站在人类发展史的高度去重新审视、鉴定,去伪存真,透过真实的历史背景去了解、观察、分析妇女的活动、影响,以及他们的地位与作用,方可作为信史。”(23)因此,我们只有客观、全面分析“黄莲圣母”所处的历史环境,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1.社会环境、个人因素与历史机遇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说:“近年来,西方有关革命运动的学术研究趋向于强调其过程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个人性格与偶然的历史机遇——而非持久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因为成为研究革命起源与结局的焦点而受到关注。
”(24)本文在分析“黄莲圣母”形象的形成背景时也没有忽视这方面的因素,力图将个人因素与社会环境、历史机遇综合起来分析。
首先,天津租界林立,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北京。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使天津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英、法、德、俄、美等西方列强陆续在天津设立租界。到1900年,天津共出现“九国租界”,总面积达2万3千余亩,相当于当时天津城的八倍(25)。随着各国租界面积增大,外国人口增多,西方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等随之传播开来。其中,西方人男女平等的思想和女性着装都对中国妇女尊崇三从四德等传统观念产生冲击。商贸活动的频繁,使不少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
其次,清末的天津,不少妇女迫于生计,放足、抛头露面者增多。在街头走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就习练拳棒功夫,学习杂技表演;在运河沿线打鱼卖鱼的渔家女,不时进入城市;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娼妓业兴盛。从事江湖卖艺、打鱼卖鱼这类职业,女子天足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渔家女整天驾船航行,如果是小脚,不但无助,而且还会碍手碍脚。在传统社会,男权主义、儒家纲常伦理是主导,加上男子喜好“三寸金莲”而形成的变态审美观,致使妇女缠足陋习流传不息,成为传统社会对妇女身体残害的一种象征。尽管史料阙如,但我们不难想象,下层社会女子念书机会不多,思想不至于被儒家伦理完全控制;脚的解放是妇女走出闺房的主要条件,也是女子参加红灯照、习练武功的重要原因。红灯照女子练习平步履水,“立水池之旁,师诵咒喃喃数周后,孩即步行水上,鞋底不濡。”(26)虽然言过其实,但练武功要求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不争事实。
最后,林黑儿的亲人因洋教欺压至死,是她利用巫术神灵反抗洋人的直接原因。在传统社会中,下层妇女既受多重压制,又承担着生活重担。一旦走出家庭接触到社会,就容易激发她们挣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思想。再加上清末天津反洋教斗争由来已久,受洋人欺压的民众早已产生仇教灭洋的热情,他们无从寻找批判的武器,只好借用宗教、巫术为工具,“宗教、巫术等因素往往是起义酝酿阶段必不可少的,是农民领袖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具。”(27)林黑儿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开始利用劫变思想、谶语谣言、“怪力乱神”等文化因素参加到义和团运动中去的。
2.“黄莲圣母”与民间宗教传统
义和团、红灯照塑造“黄莲圣母”的形象,实际上是继承了民间教派假托女神下凡、号召民众的宗教传统。义和团、红灯照是由梅花拳、义和拳、大刀会、离卦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结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扶清灭洋”为旗帜而重新形成的组织。他们一则以“扶清灭洋”标榜,得到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支持与参与,再则以民间宗教的“劫变”、“救世”思想吸引民众。义和团队伍发展壮大,参加者绝大多数是农民和游民阶层,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是民间教派的群众基础。义和团团民平时习练武功,“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凡有正式祈祷,则神必降集其身,跳舞升坐发号令。余众膜拜奉命,即赴汤蹈火,咸俯首惕息,无敢稍抗。”(28)天津红灯照在静谧地方诵念口诀,举行仪式,练习刀枪不入和飞行之类的法术,还声称会火攻敌营,举红灯灭洋舰,不一而足。这些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行为,当时上下人等却趋之若鹜,心甘情愿匍匐在“黄莲圣母”的脚下。这类神秘怪诞现象在义和团时期非常普遍。红灯照之外,还有蓝灯照、黑灯照等名目。除了天津有“黄莲圣母”之外,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圣母”、“娘娘”类人物纷纷走上神坛,如北京有“金刀圣母”、“龙天圣母”,河北宁津有“王母娘娘、九仙女”,山西有“杨娘娘”,等等。
在传统社会,现实苦难使妇女“从做人的不确定性逃进一种虚幻的、必然是固执的肯定之中”(29)。宗教为妇女的自我肯定提供了途径,明清民间宗教因为同情、尊崇、重视女性而得到广泛发展。弘阳教的《混元红阳血湖宝忏》说:“阳间妇人生产男女,秽污不净之水集聚一处,名为血湖。妇人死后,个个执碗饮尽血水,方得出期。若请红阳道众立血湖圣会,讽诵赦罪真经,即赦释前愆,归依大慈悲佛。”弘阳教特别注意争取妇女信徒,有专门为死去的妇人脱离血湖地狱而举行的“破血湖”仪式。时至今日,弘阳教在京津、冀、晋仍有活动。
弘阳教、黄天教、西大乘教、龙天教等民间教派多有女性首领,主要成员也是女性,她们主张同男子一同吃斋诵经,烧香念佛,甚至习练拳棒。黄天教的《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说:“无生法,遍天境,男女同修。”但在统治者看来,这种男女共同从事宗教活动的行为不成体统,往往加以镇压。民间教派不仅承认妇女的价值,有的甚至将女性置于很高的地位;有些教派中女性占大多数,有些民间教派甚至是由女性创立的。西大乘教《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第二十三品中说:“无为教,四维祖。西大乘,吕菩萨。黄天教,普静祖。龙天教,米菩萨。”四个教派中,吕菩萨、米菩萨是女性创教者,黄天教的普静被列入佛祖之中。明清民间教派都认为世界的创世神、救世主是一位具有慈母形象的女神——无生老母。马西沙指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父严母慈深入人心,人们对慈母怀有无限的依恋和深厚的敬慕。这一点在宗教信仰中得到了反映。”(30)在各教派中,宗教首领往往把神圣的无生老母具体化、生活化、世俗化,假托某位女性,转世人间,以此巩固民心,团结民众。红灯照的“黄莲圣母”就是这样被神化的女性。两年后,成都地区红灯教拥戴廖九妹为“廖观音”,声震一时(31)。
红灯照中“黄莲圣母”这一形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民间宗教继承了塑造女性神灵的传统,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层背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义和团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采取的手段。
从乾隆年间山东八卦教分支清水教首领王伦在教内分别文场(气功)、武场(拳棒武术)之后,八卦教等民间教派继承了这一传统,演至清末,民间教派与民间武术团体融合,形成了一套带有严密规范、浓厚宗教色彩的“请神附体”仪式。义和团作为民间教派与民间武术团体融合的典型,加入者、练习者举行仪式、取得神力是其中最重要的情节。义和团为了扩大声望,竭力鼓吹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法术,如《闭火分砂咒》云:“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32)义和团首领更声称有灵魂出窍、指草木为兵、让死人复活等特殊法力。借助这种超自然力量,义和团成员在与“洋鬼子”、“二毛子”的战斗准备中神采飞扬,士气高涨,表现得格外英勇。但结果是,义和团的“英勇”最终敌不过洋人的钢枪火炮,降神附体之类的法术成为加速死亡的推力,伤亡惨重直至失败是必然的。义和团创造的红灯照、“黄莲圣母”也是这样。
民间教派对于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深信不疑。义和团声称,造成其神奇法力在战场上失效的原因更多的是客观环境因素,比如说,大雨冲犯法术或(敌人)利用女子的污秽物来破坏义和团的法术(33),“各洋楼架大炮甚多,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所以避炮之法不能行”(34)。类似故事四处流传。有鉴于此,义和团认为,以青年女子组成的红灯照在战场上有保护其法术实施的能力,习练红灯照的女子比他们的法力还高,“谣云:红巾一掷,巾能变灯,灯到处,大火立至。背插飞刀,能远取人首级,且能屹立不动,魂出交战,一切军器皆不畏惧,枪炮遇之即不能燃。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35)如此,就可用更具威力的法术维系百姓的信心。林黑儿是天津地区红灯照的最高首领,将其树立为拥有无边法力的“圣母”,就可以弥补义和团法术的某种不足。
这里要说明的是,“黄莲圣母”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宣扬“神助灭洋”。义和团视红灯照女子为“仙女”,尊林黑儿为“黄莲圣母”,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红灯照主要从事后方补给工作,至于流传的她们“起落游行状如红星然”、“飞往各国阻其来兵”、“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等均是不实之事(36),宣传这些神乎其神的谣言只是借此造势,提高红灯照、“黄莲圣母”在民众中的威信。这种方式对于愚昧世界(无论是朝廷命官还是下层社会民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影响所及,就连生活在天津租界的外国人也对“黄莲圣母”的预言忧心忡忡(37)。当然,清廷对于“黄莲圣母”的推崇与其特定的动员、利用义和团政策有关,一旦政策转向,义和团、红灯照就成了“邪教”,“黄莲圣母”就成了女匪,“如查有聚众演技、念咒、跳神,谬称红灯照等邪术者,查明属实,应即严拿,送交刑部讯办”(38)。
四、“黄莲圣母”——男人历史中的女人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男性为主体和权威的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礼教显示了男子的崇高地位。作为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的妇女,处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底层。一部二十四史,不仅是一部帝王家谱,也是一部男人的历史。妇女进入史册,除了皇后、公主之外,其固定位子只是《列女传》,并且记录的都是以男性立场赞扬她们服从封建礼教的事迹。一言以蔽之,男人的历史中没有女人的地位。
然而,“黄莲圣母”多次作为爱国主义的象征出现在叙述近代中国历史的文字中。这种在男人历史中的女性主角历来都是凤毛麟角。因此,“黄莲圣母”很容易被人描绘为近代妇女解放潮流的代表性人物。事实上,“黄莲圣母”领导的红灯照具有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之说是不能成立的。这里从外在、本质两个方面略加评说。
红灯照女子抛弃梳头、缠足等习俗,习练武功,而且抛头露面,每隔十天举行一次“踩城”游街活动,为义和团站岗放哨、救治伤员。表面上,红灯照不梳头、着艳服、反缠足等行为符合女子放足、剪发、入学和婚姻自由以及要求参政权、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的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但实际情况颇有差异。
美国学者曼素恩(Susan Mann)在研究盛清时期的妇女时称:“女性角色和社会性别关系是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这些历史进程涉及18世纪特有的国家政策、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学术品位和审美感觉。”(39)这种视角同样适用于“黄莲圣母”等晚清妇女。清末西方近代文明随租界的建立而传入天津,尽管上至清朝贵族女子下到底层妇女均感受到西方女性着装和思想较之清朝的优越性,但是底层妇女因为受经济、文化程度等限制,他们受到影响最多就是行为上的盲目跟风,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到西方妇女解放的进步性。
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的、女性视角来看,红灯照违背封建礼教行为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底层妇女谋求自身生存的需要。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就连审美观都是以男性为标准确立起来的,从缠足成为一种风尚的怪异现象中即可见一斑——“倘若裙下莲船盈尺,则戚里咸以为羞;若天足出嫁,则夫家以卑贱视之。”(40)“黄莲圣母”与红灯照女子反缠足、不梳头的举动并非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以保种救国为出发点,将废缠足与兴女学等妇女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也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女革命家秋瑾从“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41)的男女平等角度提倡反缠足。从清朝妇女主动参与缠足的心理来看(42),红灯照女子放足走向社会的原因主要是迫于生活压力而从事生产劳动的需要,是出于民族危机之时起而反抗的需要,因而,其不缠足等行为是被动无奈之举,与“妇女解放”无涉。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宗教不是滋养女权运动的土壤,林黑儿被神化为“黄莲圣母”不是女权主义的反映。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由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于19世纪末提出,意指主张男女在社会上、政治上与经济上平等的一种思想、社会言论及政治协助行为(43)。女权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造就一批新型女性,她们发起维护自身权益的妇女解放运动,陆续登上政治舞台。革命党人秋瑾抨击清廷、宣传民主共和以及争取妇女社会地位的文章流传甚广。五四时期,女工、女学生等大量女性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参与到追求婚姻自由、财产分配均衡、男女平等的斗争之中。与之相比,林黑儿是以民间宗教信仰与武术相结合的传统方式参加、领导红灯照。王致中认为:“红灯照在当时整个运动中的作用近似于‘巫’。”(44)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核心作用的是它的具有标志性的仪式——‘降神附体’、‘刀枪不入’。”(45)西方亲历者也以“鲜艳的服饰与据信可使信徒具有刀枪不入神力的怪异仪式相结合”(46)来描述他们对红灯照、义和团的印象。
林黑儿被塑造为万人膜拜的“黄莲圣母”形象,获得与男子一同参加战斗,甚至享受到高于男性的礼遇,只是义和团宣传、利用的需要。红灯照与“黄莲圣母”并没有女权意识,也没有改变广大女性地位的现实举措。所以,她们的行为属于传统中国社会农民自发反抗斗争的类型,不过面对的是“洋人”而已。
结语
洋兵大炮攻城,张德成、曹福田各挟了重资,逃出城外去了。所有拳众,都脱去了红衣,撕去了符咒,手执大日本顺民、大英国顺民、大法国顺民、大俄国顺民、大德国顺民等旗号,争着跪接洋兵了。那些红灯照,也都脱去红衣,逃入娼竂当婊子去了。黄莲生(圣)母与三仙姑,被人缚送都统衙门,正法完案。九仙姑投水而死。
张德成逃至王家口地方,向盐商索取供张。……盐商不能堪,村人愤甚,一拥而入,擒住德成,都说咱们拿刀斫他,瞧他能够避刀剑不能。德成到此地步,居然也会屈尊降贵,伏地叩头,呼饶不止。众人不听,一阵乱刀,斫为肉酱。曹福田易装逃出之后……直到次年正月,潜归故里,被里人缚送到官,受了个凌迟之罪。最奇怪不过,他那无边法术,到此竟然不灵(47)。
天津陷落,义和团溃败,拥有降神附体法术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跑了,宣扬救世济人的“黄莲圣母”死了,众团民落荒而逃,全没了往日神明护体的威风。当神灵巫术失灵、团民的精神支柱轰然垮塌之时,义和团组织的松散性、落后性、悲剧性就暴露无遗。
义和团、红灯照的大师兄和大师姐们,沉迷于对宗教的崇拜,如痴如醉。如果从宗教冲突角度解释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虽然与基督教的战争失败了,但是宗教力量对人的精神控制是成功的(48)。宗教创造为人们实现愿望的神灵,给人以精神寄托,借此对人们进行精神控制。基督教相信上帝的力量,同样民间宗教特别推崇女性神。明朝罗教将“无生老母”奉为创造世界的最高女神,用慈母般的关爱普度人间受苦受难的信徒。至清代为大乘教、八卦教等民间教派接受,且逐渐形成神化女性为女神的宗教传统。
“黄莲圣母”、“廖观音”等被塑造的女神,在民间宗教信仰中受人顶礼膜拜;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与“革命”、民众运动合流后,还增添了维系组织、提高威望的作用。她们在社会中争取主角地位的行为貌似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体现,事实上,社会对她们的狂热崇拜只是为了现实需要,一旦剥去宗教外衣,她们仍然受政权、神权、夫权的制约,成为男人历史中的牺牲品。
然而,“黄莲圣母”形象并没有同她不知所终的结局一样被历史遗忘。在历史和记忆之间,“黄莲圣母”为满足现实需要,从江湖艺人、渔家女、土娼、女巫到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象征,如演员般不断地更换角色。身为历史学者,必须从客观的、历史的角度还历史一个真相。
注释:
(1)参见罗惇曧:《拳变余闻》,《清代野史》第1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陆士谔:《清朝秘史》第107回“义和团大闹天津卫、聂提督殉难八里台”,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3等。
(2)有关义和团时期女性领导发动农民斗争的论著,一般都会提到黄莲圣母,参见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义和团在天津的反帝斗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刘蓉、徐芬:《红灯女儿颂》,《天津师院学报》1975年第2期,以及相关文史资料。
(3)王致中:《“红灯照”考略》,《甘肃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4)[日]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9页。
(5)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1页。
(6)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478页。
(7)罗惇曧:《拳变余闻》,《清代野史》第1辑,第276页。
(8)常佳骐的《义和团在天津城乡的反帝战斗》(《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与《义和团》(四)中均有提到。
(9)(11)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二),第37、36页。
(10)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7页。
(12)天津市西郊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津西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第73页。
(13)(15)管鹤:《拳匪闻见录》,《义和团》(一),第487页。
(14)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第58页。
(16)[英]霍布斯鲍姆、兰格著,顾杭等译:《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7)《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18)《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42页。
(19)参见《天津地区红卫兵小将盛赞红灯照,誓把头号野心家批倒批臭》,《光明日报》1967年4月28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红灯照创作组:《红灯照》(歌舞剧剧本),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印,1967年。
(20)庄建平等:《义和铁拳英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21)如《武清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津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静海文史资料》第2辑、《霍县文史资料》第3辑、《廊坊市文史资料》第4辑等。
(22)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23)李小江等主编:《批判与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1页。
(24)[美]裴宜理著,池子华、刘平译:《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中文版作者序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5)参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天津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26)[日]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二),第244页。
(27)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2页。
(28)(清)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29)[美]贝格尔著、高师宁译:《天使的传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30)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31)“廖观音”,四川华阳县石板滩客家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推举为华阳县红灯教首领,旋被神化为“观音”,仇洋反清,最终被捕处死。参见孙昉、刘平:《女工·女匪·女神——义和团时期四川“廖观音”形象研究》,提交“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聊城大学,2010年8月)。
(32)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154页。
(33)[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第四章详细介绍了义和团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
(34)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51页。
(35)佚名:《遇难日记》,《义和团》(二),第163页。
(36)《义和团》(一),第470、244页。
(37)[英]布莱恩·鲍尔著、刘国强译:《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1918-193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3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8页。
(39)[美]曼素恩著、定宜庄等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40)参见暴鸿昌:《暴鸿昌文集——明清史研究存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41)《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0页。
(42)致力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力图改变“五四”史观关于传统中国妇女普遍受压迫的观点,以女性为主角,来解释传统中国社会性别与社会权力、等级的关系。其代表作为《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3)Francoise Barret-Ducrocq, Le Mouvement Féministe Anglais d"hier à Aujour d"hui, Paris: Ellipses, 2000, p. 6.
(44)王致中:《“红灯照”考略》,《甘肃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45)[美]周锡瑞著、张俊义等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5页。
(46)[美]弗雷德里克 A.沙夫、[英]彼德·哈林顿编著,顾明译注:《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7)陆士谔:《清朝秘史》第107回“义和团大闹天津卫、聂提督殉难八里台”。
(48)参见[美]柯文:《义和团、基督徒和神》,《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来源: 《安徽史学》201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