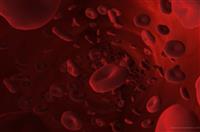
斯维特兰娜虽被称作“克里姆林宫公主”,但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却在与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角力,由此也决定了她人生历程的奇特和崎岖。
【“掌上明珠”的叛逆与情感坎坷】
斯维特兰娜生于1926年2月28日,是斯大林唯一的女儿,斯大林和妻子阿里卢耶娃把她视作掌上明珠。在父母的呵护和家庭教师的教育下,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在学前阶段便能读写俄语和德语,会画画和捏泥塑,且能根据别人的钢琴弹奏写出乐谱。
1932年11月8日阿里卢耶娃自杀身亡后,斯大林对这个在6岁半便失去母亲的小女儿给予了更多的父爱。在家里,他常和她玩“命令”游戏:作为“女主人”的女儿给作为“第一秘书”的父亲下达书面命令,“第一秘书”则谦恭地表示“服从”、“遵命”、“马上完成任务”;倘出差在外,他便用工工整整的印刷体给她写信,给她邮寄她最爱吃的水果。在母亲去世后的整整10年里,这对父女的关系显得融洽而亲密。
1941年冬,斯维特兰娜从外国杂志上得知了母亲死亡的真相--并非像家人一直告诉她的那样是因病而死,而是自杀。这件事对她震动很大,也改变了她对父亲的看法。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被摧毁了,也摧毁了我对父亲的意见、意志、每一句话的绝对服从……”
由于这个缘故,也因为青春期来临,斯维特兰娜开始变得有些叛逆。1942年冬,16岁的她竟然爱上了40多岁的电影导演阿o雅o卡甫列尔。为了拆散他们,斯大林的警卫员鲁缅采夫对卡甫列尔提出了警告,并建议他离开莫斯科,到较远的地方出差。卡甫列尔虽当场骂了鲁缅采夫,但终究还是没有承受住压力,决定到塔什干去拍片子。然而就在他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之时,却突然以“英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后被流放5年。斯维特兰娜则遭到了父亲的严厉痛斥:“现在战争打得这样,可你却干出……”“也不看看你自己,可有谁需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的女人,你是个糊涂虫!”盛怒之下的父亲甚至狠狠地打了她两记耳光。自此,父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冲突接连发生。
中学毕业后,斯维特兰娜打算报考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因为她喜爱文学,且老师也建议她学习语文。不料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你想当文学家?你就喜欢风流名士派!他们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人,你也想做这样的人吗?……不行,你必须受良好的教育,哪怕是考历史系也行。”女儿虽极不情愿,但为了不致与父亲闹僵,还是于1943年秋进入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
次年春天,正读大一、刚满18岁的斯维特兰娜与她中学时期的同学、当时正就读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莫罗佐夫(犹太人)结了婚。对于这桩婚事,斯大林虽不满意,但也没有执意反对,只是说:“这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硬将他塞给你的。”“见你的鬼,愿意怎样就怎样吧。”不过他明确表示,决不允许她把丈夫带到家中。结果是,斯大林一次也没见过这位女婿。
结婚第二年,斯维特兰娜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约瑟夫。她把孩子交给佣人照看,自己则继续读书。1947年春,这对结婚刚三年的年轻夫妻因感情破裂而离异。
离婚后,斯维特兰娜又感到了孤独,而她那个不能与外界接触、犹如孤立城堡般的家更让她感到憋闷和烦躁。为了排解心中烦闷,她经常到原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日丹诺夫的家中做客,由此与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o日丹诺夫有了较多接触。1949年春两人登记结婚。
两人的婚姻其实并无感情基础。他们虽互不讨厌,但也并不相爱。斯维特兰娜坦言,她之所以嫁给尤里,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可以使我有可能进入另一个家,给我哪怕是一点点的自由,给我打开接近人们的大门。”而日丹诺夫家之所以愿娶斯维特兰娜,则不能排除她的父亲是斯大林的因素。当然,禀性耿直、满腹锦绣的尤里不是喜欢攀龙附凤之人,但他的母亲却非常市侩,而尤里在家里又恰恰唯母命是从。
斯大林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他一直希望两家能够结亲,这不仅是因为两家门当户对,日丹诺夫成为他的亲家有助于他权位的巩固,还因为他对尤里这个小伙子也十分欣赏。但他更希望尤里能上门做他的女婿,随着年事日高,他对独自一人的生活已感到孤独。在得知两人将喜结连理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人在他的孔策沃别墅增建一层楼,以期两人能高高兴兴地住进去。不料女儿却坚决要求带着她的儿子约瑟夫住到日丹诺夫家,这让他感到有些委屈和伤心,愤愤地对女儿说:他家的那些女人会把你吃掉的!但女儿还是住到了丈夫家中,一年后生下女儿喀琪娅。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尤里在婚后仍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回家,也很少注意妻子的生活和情绪,而斯维特兰娜也考取了苏联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两人各忙各的,难得进行感情沟通,夫妻关系日趋恶化。1952年两人正式离婚。斯大林对此虽感到惋惜,却未加阻拦。
与尤里离婚后,斯维特兰娜仍未与父亲住在一起,而是住进了父亲另外给她安排的一套房子。这时她已很难见到父亲,1952年10月28日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想见到你……如果允许的话,如果这不会使你感到不安的话,那么,我请求批准我在你身边度过11月的两天节日--11月8日和9日。”
然而,1953年3月2日,斯维特兰娜突然被从课堂上叫到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身边。她后来写道:那几天,“我爱父亲是那样强烈和温柔,胜于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
【拒绝特权待遇,心境苦闷彷徨】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为了安慰死者家属,于1953年3月21日作出决定,给予斯维特兰娜及其子女如下物质帮助:(1)把沃伦斯科耶别墅及其服务设施送给斯维特兰娜一家无偿使用;(2)给予每月4000卢布的临时生活补助;(3)可随时从部长会议汽车基地叫车。当天,斯维特兰娜致信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一方面对政府的“同情和关心”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表示自己无权享有这些待遇,因而拒绝接受。信中只是请求,允许她在夏季的时候,在茹科夫卡苏联部长会议别墅区里租用2~3个房间,房租由自己支付。但苏联政府坚持认为,特殊待遇不能取消,只是鉴于斯维特兰娜在信中提到了在茹科夫卡别墅区租用房间的问题,决定把原打算让她一家免费使用的沃伦斯科耶别墅改为在茹科夫卡别墅区的一栋别墅。
11年后--1964年11月17日,斯维特兰娜又致信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再次请求收回给她一家的特殊待遇。信中说,我们一家虽对政府给予的人道主义帮助一直心存感激,但“我们在道义上无权永远享受这种人道主义”。额外享有的这种权利,“使我在朋友面前很难为情,总之,在所有人面前都感到不自在”。考虑到一个月前赫鲁晓夫刚被废黜,斯维特兰娜担心刚刚上台执政的新领导可能会对她此时提出这个问题产生误解,所以在信中又特别写道:我“不想让人把我的行动理解为某种示威”。“恳求您,阿列克谢o尼古拉耶维奇,正确地理解我,不要拒绝我的可能有些特别的请求”。
尽管如此,柯西金在收到这封信后,还是派人同斯维特兰娜进行了这样的谈话:“我们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有别墅还不要的事。相反,人家还求之不得呢!你们这是怎么啦?这造成一种印象,就像用这种形式向新政府抗议似的。”“当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再向你们收回别墅好了。现在你们尽管用,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斯维特兰娜一家只好继续使用该别墅。
斯维特兰娜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后,先是在莫斯科大学教授苏联文学和英语,后于1956年调至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从事历史、语言及儿童文学研究,1962年她又到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在此期间她编写和翻译出版了多部著作。学识渊博且从小就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的斯维特兰娜一直相信,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能够干出一番业绩。因此,她对政府强行给予她的某些“照顾”和“特权”一向采取抵制态度。
顺便指出,在对待自己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由此所享有或可能享有的特权问题上,斯大林三个子女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斯维特兰娜在谈到大哥雅可夫时写道:“任何人提到他是什么人的儿子,他都非常厌恶……他一贯真诚地拒绝由于他的家庭关系而可以得到的特权,所以他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特权。”二哥瓦西里则对他的特殊身份和享有的特权自负、喜欢得要命,并不惜一切手段加以利用,屡试不爽的利用结果又使他变得藐视尊长,目无法律,逞性妄为,骄纵无忌。以致在父亲去世后不久锒铛入狱。斯维特兰娜虽与大哥同父异母,与二哥同父同母,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却与大哥一致。
从1953年春开始,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苏联社会进入了“解冻”期,历史上的一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了平反,斯维特兰娜的一些亲戚也走出了牢房,纷纷向她诉说了自己的冤情和在监狱所受的非人待遇。这些都对她震动很大,她开始用审视的目光看待父亲统治下的那段历史。因此,1956年2月末,她在读过米高扬交给她的、尚未向各级党组织传达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她父亲的“秘密报告”后,并未作出如当局所料的那种激烈反应,而是平静地对米高扬讲道:“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像是真的……”一年半之后--1957年9月,她把自己的姓改成母姓“阿里卢耶娃”。
在父亲去世后的10年间,由于当局对“斯大林问题”的热度始终不减,而在对他的评价上又忽高忽低,时褒时贬,斯维特兰娜越发感到了作为斯大林女儿的巨大精神压力,以致彷徨苦闷。1962年春,她在莫斯科东正教堂接受了洗礼,并坦言:“我感到这是我内心的需要,教条于我无大意义。”1963年,她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又向她的朋友作了这样的倾诉:
和以往一样,我生活在父亲盛名的庇荫之下……一些人关怀,一些人憎恶,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对我抱有好奇心,应得的和不应得的烦恼和激动,以及那许许多多的受之有愧的向我表示的热爱和忠诚--所有这一切都从四面八方压挤着我……
我继续过着奇怪的,无所作为的,具有两重性的生活。和十年前一样,我的生活仍旧是:表面是一回事,内心完全是另一回事。表面上和从前一样,我的生活是安定而有保障的,处于“上层”的大树和叔叔阿姨们的庇荫之下,然而我的内心生活,和以前一样,和他们在兴趣、习惯、精神、事业、语言、文字上完全格格不入,不过我今天的这种感觉比以前更加强烈罢了。
【出逃美国,被当局称为“歇斯底里病患者”】
正是在上述心境下,1963年冬,斯维特兰娜爱上了来莫斯科治病的印度共产党员勃拉哲士o辛格。辛格比斯维特兰娜大17岁,已近花甲之年,而看起来又比实际年龄老出不少,且病得“似乎一阵风能把他刮倒”。两人的结合固然令人意外,可更让人不曾料到的是,此事竟导致了斯维特兰娜与苏联当局一次又一次的冲突。
1965年4月7日,斯维特兰娜开始与辛格同居。5月3日,两人来到了莫斯科的一家婚姻登记所,询问登记所需的材料和手续。不料第二天斯维特兰娜就被召到了柯西金的办公室。这位政府首脑对她劝阻:您,一位又年轻、又健康的妇女,难道就不能在咱们这里找一个健壮的年轻人?您要这个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干什么?不行,我们大家都坚决反对。我们劝您别去办理婚姻登记,我们也不允许。“因为要是根据法律他把您带到印度去该怎么办?”
1966年10月,病情急剧恶化的辛格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向斯维特兰娜表达了想死在印度的愿望,斯维特兰娜遂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请求允许她把辛格送回自己的故里,
信中表示她在印度不会呆很久。代替总书记作答的是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又一次拒绝了斯维特兰娜的请求。
当月31日,辛格在莫斯科病逝。11月3日,斯维特兰娜分别致信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请求允许她把丈夫的骨灰送到印度他的家人那里。信中保证:“旅行只需7~10天,不会再多。”除丈夫的侄子--印度外交部长迪内希在印度首都德里的家和丈夫在恒河岸边的老家卡拉康卡村外,“我什么地方也不去。除了最亲近的亲属以外,我谁也不见。我向您保证,从政治立场方面绝不会发生任何可受指责的事情。”
11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电话表决后作出了如下决定:
责成谢米恰斯内(克格勃主席--作者注)同志派两名工作人员陪同她前往印度。责成别涅季克托夫(苏联驻印度大使--作者注)同志在他们在印度逗留期间给予帮助。
当天,柯西金把斯维特兰娜召去作了5分钟的谈话,告诉她中央决定准许她出国,但条件是不得和媒体接触。
11月11日,斯维特兰娜拿到了出国护照。在出国之前,斯维特兰娜并无居留印度的打算,只是想按照签证期限在那里逗留一个月。但12月25日这天她在见到迪内希后却突然提出她想留在印度,并请他提供帮助。迪内希答应为她效力。第二天,斯维特兰娜写信给苏联大使馆,宣称她要在卡拉康卡村住到1月18日,因为她的签证是一个月,至1月20日才到期。接着她让卡西洛娃回德里,向大使馆转交此信。自此,她摆脱了政府派来的这位女翻译。
在卡拉康卡村的这些日子里,斯维特兰娜与辛格的亲人及其邻居相处得很融洽,并毫不隐讳地向他们表达了她想留在印度的愿望。他们为此感到高兴,并纷纷为她出谋划策,认为她可以到美国大使馆申请避难,待有了美国护照后再长住印度。这个主意对她启发很大。
几经波折,来到美国使馆后,斯维特兰娜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并提供了相关的证件,请求美国人帮她实现自己的心愿。美国人则要求她写一份包括简历在内的声明。她于是在声明中写道:
我在印度和丈夫的亲属和朋友会了面,因此我开始认真地思考留在印度的问题。可是我发现这不可能,因为无论是印度政府还是苏联政府看来都不会让我这样做……
美国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帮斯维特兰娜尽快离开印度,但并不急于让她进入美国,因为她目前的决定有可能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因此,不如先让她到中立国家呆一段时间。
苏联驻印度使馆发现斯维特兰娜失踪后,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外国报刊对斯维特兰娜出逃一事作了各种各样的报道和评论,感到脸面尽失的苏联当局遂通过塔斯社发表了为自己打圆场的消息:“斯o阿里卢耶娃打算在国外住多长时间--这是她个人的事情。”
斯维特兰娜在瑞士逗留了一个半月,美国国务院派原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o凯南等人同她进行了长谈,对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了解。斯维特兰娜除一再表示她“决定永不返回苏联”外,还表示愿在美国出版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最后,她获准于4月21日飞往美国。
“红色公主”背叛自己的父亲和国家,这使斯维特兰娜立刻成了新闻人物。她自己也表现得十分活跃。4月21日刚在纽约机场走下飞机,便和等候在这里的记者见了面。几天后,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讲了苏联人是怎样生活的,她是如何抛儿别女、脱离自己的祖国的。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电视台对这次招待会进行了报道,在苏联当局眼中,这是一场反苏反共的强大攻势。作为对这一攻势的回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6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记者招待会上讲道:“斯o阿里卢耶娃是个精神上不稳定的人,她有病。对那些企图在政治上利用她的人,我们只能表示惋惜。”莫斯科的《文学报》则发表文章称,斯维特兰娜从来就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和偏执狂”。
其实,斯维特兰娜把这次出走看得很简单,她只是想摆脱父亲的阴影,只是想要过彻底自由的没有束缚的生活。
【彻底背叛父亲,失去祖国国籍】
除了与美国各方面人士接触外,斯维特兰娜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她《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的出版上,经过与多家出版社交涉,终于与它们达成了在1967年10月底用几种语言出版该书的协议。这一消息发布后,苏联方面深感不安,因为该书的出版时间恰值十月革命50周年前夕。
其实5月份苏联当局就已从斯维特兰娜在莫斯科的一位朋友那里查抄了这部书稿的复写件,里面写的主要是家庭琐事,虽对斯大林有些贬损,但更为斯大林作过开脱,认为贝利亚是实施残暴镇压的罪魁祸首,而他父亲只不过是受到了贝利亚的蒙蔽。无论如何,它对斯大林及苏联阴暗面的揭露远未超过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程度。尽管如此,苏联当局还是认为,此书在西方出版后必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炒作,而这无疑会对恰在此时举行的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带来不利影响。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决定设法让这部书稿提前数月面世,这样当50周年庆典举行时,由此书的出版所引起的喧闹便已趋于平息。为此,他命人把查抄到的书稿复写件交给了与克格勃关系密切的英国记者维克托o路易,并让这位记者在克格勃人员的配合下向斯维特兰娜的子女强行索要家庭照片。随后,路易以不太高的价格将书稿复写件和家庭照片卖给了英国弗莱贡出版社,接着又卖给了西德《明镜》画刊。8月初,附有家庭照片的该书已经上市,而《明镜》画刊也开始连载这部书稿和照片。斯维特兰娜虽在事后打赢了与“盗版者”的官司,且将她的“正版书”的出版时间由原定的10月底争取到了10月初,但安德罗波夫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出版后,斯维特兰娜又开始了她的第二本书--《仅仅一年》的写作。该书讲述了她自1966年12月至1967年12月整整一年的出逃经历,同时也谈到了苏联的某些历史问题。与她的第一本书不同,这本她出逃后在美国人影响下写成的书,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苏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不满,例如:
……“斯大林主义时期”,是个人专制时代,是血腥恐怖、经济困难、残酷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反动时代。
那个精神空虚、冷酷无情的人……那个伙同自己的同谋将国家变成监狱--在那里凡有生命、有思想的都被扑灭,无一幸免--的人,那个引起千百万人恐惧和憎恶的人,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其经济意义来说像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关系方面这是某种奇怪的杂交品种:官僚军营式的制度,其秘密警察有如德国的盖世太保,而我们落后的农业使人想起19世纪的农村。
1969年秋此书在美国出版后,西方国家马上将其作为重磅炮弹,掀起了又一轮反苏浪潮,而且宣称斯大林的一切做法都是从列宁那里继承来的,“恰恰正是列宁应当对在苏联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而此时苏共中央正在紧锣密鼓地部署纪念斯大林诞辰90周年(1969年12月)和列宁诞辰100周年(1970年4月)。
面对这种情况,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寝食难安。1969年11月5日他致信苏共中央,提出“为了转移世界舆论对于敌人利用斯o阿里卢耶娃《仅仅一年》一书而掀起的诽谤性宣传运动的注意力”,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根据斯维特兰娜的子女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表示对其母亲叛国行为的愤怒这一情况,起草一封给斯维特兰娜子女的公开信,并寄给对斯维特兰娜持有不赞许之意的《纽约时报》副主编哈o索尔兹伯里,让其在国外发布。同时将这封公开信和对斯维特兰娜子女的访问放在欧洲的一家重要杂志上发表。
第二,向西方报刊灌输这样一种说法,即斯维特兰娜的新书是一大群人集体炮制出来的,包括一些声名远扬的苏联的狂热反对者和擅长捏造苏维埃国家历史的人。在阐述这种说法时,应加进一些克格勃掌握的能让这些人名誉扫地的材料。
第三,由曾与斯维特兰娜关系密切的苏联知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给她发一封集体签名的信件,抗议她捏造苏维埃国家的历史和诽谤列宁。这封信件可通过克格勃渠道转交给斯维特兰娜,同时设法透露给国外报刊。
第四,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揭露西方国家情报机关活动的文章中,应指出这些情报机关是从那些私人生活方面和工作方面都有缺陷的人那里获取材料的;他们为了得到反苏材料,竟不惜利用斯维特兰娜这样一些堕落和令人厌恶的人物。
第五,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对《仅仅一年》一书进行分析,以求判明书中可能隐藏着的敌人的新的态度和意图,以及他们在此基础上安排的在列宁诞辰100周年之际的意识形态上的破坏性宣传活动。
此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69年12月19日作出决定,因斯维特兰娜“犯有败坏苏联国籍这一称号的过错”,剥夺她的苏联国籍。
【重回苏联与再次出走】
因这本书的出版引起的喧嚣渐渐平息后,斯维特兰娜也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她的生活之路依然充满坎坷。1970年4月,她和刚认识了三个星期的美国建筑师彼得斯匆匆结婚,第二年45岁的她生下了女儿奥尔加。但在孩子只有半岁多的时候,夫妻关系便出现了危机,她先是带着女儿与彼得斯分居,后又于1973年5月办理了离婚手续。此后她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教育女儿身上。
她对苏联虽仍采取敌视态度,并于1978年11月宣誓加入美国国籍,且登记为美国共和党党员,接着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兰娜o彼得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美国人对她的虚情假意也越来越感到厌恶,越来越觉得“两个超级大国是如此相似,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于是,她于1982年8月带着奥尔加离开美国,移居英国。
1982年底,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执政后,采取了一些缓和东西方关系的措施,也解除了移居西方的斯维特兰娜与国内接触的禁令,斯维特兰娜遂得以与在莫斯科的儿子通话。通话中儿子表示希望她回国,因为“我们需要你”。
对西方世界的失望和对国内亲人的思念以及儿子所表示的希望,使斯维特兰娜终于作出了返苏的决定。1984年9月,她向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提出了回国申请。
苏联政府对斯维特兰娜的这一决定感到高兴,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这位叛逃者迷途知返,而且也非常有利于苏联的对外宣传,不仅马上批准了她的回国申请,而且在她带着女儿回国后还给予了娘儿俩一系列政治和生活方面的待遇:立即恢复了斯维特兰娜的苏联国籍,给她发放退休金、安排住房、配备汽车;给予她的女儿奥尔加苏联公民权,安排她入校就读。
斯维特兰娜回国后也做了一些让克里姆林宫满意的事情。她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进行了谴责,“我在自由的国度没有一天是自由的”--这句话和她当初逃离祖国的举动一样,再次让全世界震惊。她还对位于斯大林故乡哥里的斯大林纪念馆投入了很大热情,亲自设计了其中一个展厅,并把她掌握的部分斯大林遗物拿来展出。
但苏联当局虽看起来对她百般照顾,实际上仍把她视作特殊而敏感的人物,对她放心不下。如她所言:“我一回来,美国护照就被收走了。开始指示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此外,当局还暗中派人对她进行监视……斯维特兰娜再次决定离开苏联。1985年12月她给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信说:“由于我们来苏联的目的未能达到,而且我家里的人同我们合不来,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再呆下去。我们情愿离开。”
戈尔巴乔夫当局觉得,如果进行劝阻,此事又会闹得沸沸扬扬。何况奥尔加在18岁以后有理由要求返回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加上斯维特兰娜并没有说她决定离去的原因是因为对苏联现政府的不满,那么,就遂她所愿,由她去吧。
1986年4月,斯维特兰娜带着奥尔加离开苏联重返美国定居。回到美国后,她否认了她在莫斯科发表的对美国的那些谴责之词。1988年4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政令,同意斯维特兰娜和女儿奥尔加放弃苏联国籍。3年之后,苏联解体。
晚年的斯维特兰娜孤身独处,默默无闻。2011年11月22日,她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病逝。
去世之前她曾这样对人感叹:“我这一生太沉重了,沉重得不堪倾诉,更不堪活下去。”然而她竟活了85岁。在自传《遥远的乐声》里,她曾经写道:“我总是听见另一种鼓点。还在苏联上中小学,后来上莫斯科大学时,我就一直如此。我怎么也无法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孩子齐头并进……我总是合着自己个人主义的乐声,踏着另一种节拍前进。”逝世前,不知她是否会想起,当她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同学的父母不断被捕,她向父亲求情,最后得到的一顿咆哮:“他们是叛徒,是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须被消灭,就像踩死一只臭虫!”
也许从那时起,她已经离克里姆林宫越来越远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