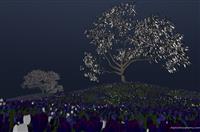对文艺学界的文艺学著作,我历来有一种翻翻即止的坏习惯,能够激发我“欲罢不止”之阅读冲动之著甚少。高楠先生的新著《文艺学:传统与当代的纠葛》(以下简称《纠葛》,其后文所引均只标注页码)之能吸引我并一口气读完,乃在其精思妙论背后那独特的学术个性所蕴含的厚积而发的学科思想激情和极富使命感的学术锋芒,这种学科思想激情和学术锋芒,具体展开为对文艺学的历史现实的反思、证伪、批判。因为在著者看来,真正的学术探索,始终是实践理性精神的张扬与磨砺,即永远是反思,是证伪,是批判,是在反思、证伪、批判之进程中谋求启蒙与建构。在学术探索中,无反思、无证伪、无批判的建构,永远是伪建构、虚建构,是标榜建构的无建构;无谋求建构的反思、证伪、批判,是盲目的、无目的的:这样的反思,是缺乏理论实践理性的反思;这样的证伪,是流于感觉经验或沉醉于自我偏好的证伪;这样的批判,是无内力和锋芒的做秀式的批判。《纠葛》以反思、证伪、批判为武器、为手段,以最终谋求真正的建构为目的,紧紧围绕“建构具有中国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当代文艺学何以可能?”之主题,首先检讨“为什么要建构文艺学的中国主体性和主导性?”并证伪和批判了当前文艺学领域的各种盲目姿态与种种错误观念,然后着手解决当前文艺学“凭什么来建构中国主体性和主导性?”之问题,以此谋求一种新的建构。在《纠葛》的理路中,反思、证伪、批判,是起步,启蒙是手段,建构是目标。对沉疾膏肓的文艺学来讲,没有反思、证伪、批判,就不可能有启蒙;无历痛苦的启蒙之礼,则难有建构之功。所以,反思、证伪、批判,乃是当代中国文艺学建构所最缺乏者,亦是其所最需要者。
文艺学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作为一种语词语言的艺术,语词语言本身就规定了它的特殊性,那就是,文学本身就是民族的艺术。因为在人类语言体系中,只有人工语言才是人类共通的语言,自然语言却属于特定民族的语言,并构成民族文化、思想、情感和精神守望的集中表征。文学作为以表征民族文化、思想情感和精神守望的特殊艺术形式,自它产生之时始,就深深地烙印了民族个性和民族根性的胎记,构成了民族文化、思想、情感和精神守望的时代性传创的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也无论社会以怎样的姿态和步伐走向全球和世界,民族性是文学在追求世界之普遍性进程中张扬其特殊性,在探寻人类共性之美的同时,更加绚丽夺目地创造着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个性和生存风采。文学的这一自身定位,决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身立足点和构入世界对话之域的独特姿态。正是基于此,中国文艺学始终只能是中国的文艺学,这是中国文艺学的命运。正是这种既定的命运,使《文艺学:传统与当代的纠葛》获得了思想审查的独特时代个性和开创新象的理论风采。-
客观地看,20世纪百年进程中,中国文艺学始终没有获得自身的应有定位,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其没有获得自身的研究对象。世纪之交,李春青与王修华在其《对当前文艺学研究的几点浅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20年来的文艺学仅仅是完成了观念的更新而已,至于方法的建设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起步。”“由于缺乏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所以人们都不敢涉足文艺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了,但是一个学科要真正有所发展却恰恰有赖于在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突破。……”[] 百年文艺学的大半时间,是研究革命文学(前期是革命文化,后期是政治革命)并为革命文学提供理论依据,其关注的焦点是文学的革命问题和如何革命文学的问题,至于文学本身这个对象被无形中阉割了。20世纪80年代初始,文艺学进行了自身转向,但其全部努力似乎只实现了一个目的,即通过观念革命和方法革命而在文艺学领域证明了西方各种观念、主张、方法的绝对正确性和普遍适用性,至于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同样被弃之而不顾。一种没有自身对象的文艺学,自然难以形成“基本理论建设”方面的“起步”和“进步”了。
二是由于其革命文化和政治革命,文艺学成为“无根之学”,其表现就是它丧失了其本应该有的国度性和民族性,现今各大学中文专业的文艺学教材,虽然层出不穷,但却不能在任何一本标榜“新”和“权威”的教材中,找到一丝中国文艺学的实质内容。
三是“新时期”以来,继续着革命文化和政治革命仍在悄然进行。这种“三管齐下”的革命,使文艺学本身处于寻求独立而无法独立,吁求建构主体性而远离主体性,期盼构入世界对话的进程获得主导性而却又无时不在消解其主导性的多维困境之中。或许正因为如此,新世纪开元,“取消文艺学”的论调弹出,“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自我质疑漫生。在这样一种时代性的学科背景氛围中,建构当代中国文艺学成为不可再回避的、关涉其生死存亡的根本任务。要建构中国文艺学,其主体性和主导性问题成为焦点。然而,文艺学在其“三管齐下”的继续革命进程中要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则首先需要切实解决其“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是奠基,也是根本。
这是《文艺学:传统与当代的纠葛》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背景,亦是该著所探究的主题:它敏锐地抓住中国文艺学当代建构之根本问题和奠基问题,围绕其主体性和主导性建构“何以可能”,予以系统、深入地反思与批判,并企望通过这种根本性反思和批判而导航中国当代文艺学之健康发展。
正如《纠葛》所论,“建构”之于任何领域,都是一个实践理性概念。建构,就是在实践层面展开理性,或者说必须运用理性来指导实践同时通过实践来求证理性,因而,建构是实践理性的行动展开。当代文艺学的建构,就是要运用理性来指导其理论的实践并通过理论的实践而创造新的理性(学科思想、精神、理论、方法)。
《纠葛》指出,任何领域的实践理性的行动展开,都需要一个特定的能够使行动得以展开的平台。这个平台不是行动本身所创造的,而是先于实践行动展开的实践对象所给定的。因而,实践行动展开的首要前提,是将其实践行动本身置于其先在的由实践对象所生成的平台之中,这是实践理性的真实敞开。基于此,当前文艺学建构所指涉的对象是所需要建构的当代文艺学;建构当代文艺学,其所先于理论实践行动的平台,即是中国文艺学的当下境遇。
要明确文艺学的“当下境遇”,首先得明确“境遇”这个概念,所谓“境遇”者,乃处境与遭遇:前者乃空间在场的当下概念,意指“我”之当下存在敞开所面临的环境,其表征生存的现实性和在场的空间度;后者乃不在场之在场的时间概念,意即“我”之外的各种力量、各种因素从各个方面向“我”汇聚并在我身上相遇相交相对相融, 从而形成“我”之存在敞开的深度背景,其表征为不在场之在场历史的当下朝向和不在场之在场的未来朝向之当下期待。以此为视野,中国文艺学的当下生存状况、表征历史的中国文论传统之不可逆的现实指向、表征享有世界对话权和世界主导性之中国当代文艺学对当下的全面期待,此三者,构成了中国文艺学全境视域的“当下境遇”。
在理论探索领域,其实践理性的行动张力,来源于当下境遇的张力;其实践理性行动展开所形成的思想、理论、方法的对话锋芒,同样来源于其当下境遇所生成的三维视域融合的张力。《纠葛》之深度反思所形成的理论锋芒、思想张力、方法论穿透力,均来源于它对中国文艺学“当下境遇”的三维视域的逻辑把握。
基于中国文艺学的当下境遇,建构是其主题。然而,在《纠葛》看来,自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界在喧哗“建构”时,“为何而建构?”和“凭什么而建构?”的问题,却往往被抛在一边。因而,建构中国文艺学之热忱,可以说洒遍了20世纪整整一百年每一步歪歪斜斜的脚印,然而,时至当前,中国文艺学的建构,仍然处于方兴未艾和百废待兴之期待状态中。这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文艺学界数代同仁的全部努力,都是在不知反思“为何建构?”和“凭什么建构?”的认知荒原上展开的,它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实践理性。
“建构”这个概念,是指构设创建。建构的先期工作或者说其奠基工作是清场,清场工作之于理论建构来讲,需要反思,反思是最实在的实践理性之思,是最具有批判锋芒和对话张力的理性之思。正是这种先行的实践理性的清场之思,才为学科及其理论建构扫清道路,奠定基石,提供方向。对“为何建构?”和“凭什么而建构?”之问题的严肃拷问与全景式反思,就是对真正意义的学科理论建构扫清道路、奠定基石、提供方向。《纠葛》就是这样一本清基方面的实践理性批判之作,它以“建构当代中国文艺学及其主体性和主导性何以可能”为主题,围绕“为什么要建构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和“凭什么来建构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和主导性?”而展开,从而彰显出其应有的理论实践理性个性,张扬出其难得的理论实践理性批判之锋芒和多元开放的对话张力。
在《纠葛》看来,主体性和主导性问题之所以构成建构当代文艺中国文艺学的根本问题,是在于自新时期以来,文艺学至今仍然在整体上缺乏其应有的主体性品质和主导性立场,还只是游戈于他乡的“他者”,没有获得本生的学科身份和应有的中国学术个性。基于这种认知,该著围绕此而倾力反思如下三个实质地促使文艺学丧失自身主体性并使其主导性空位的具体问题:一是中国文艺学的当下生存状况;一是形成其当下生存状况的文化奠基的空位;一是形成其生存状况之全球化姿态的扭曲。
学术始终是人的学术,学科的建设或发展,乃是此一学科的学者们的学术人格、学术精神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汇聚性结晶。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既涉及到“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的问题,更涉及到“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内容以及何以要选择这种方式来研究”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才是根本的。因为“为什么”的问题事实地牵涉并托出了学者们的学术姿态和生存姿态问题,并且,学者们的学术姿态又实际地由他们的生存姿态所主导。从根本上讲,中国文艺学的当下生存状况,受决于中国文论学者们实际生存姿态。中国文论学者们的特有生存姿态,汇聚形成了中国文艺学界的整体生存状况。
“出于历史原因,大家共同参与了这座公寓的建造,用热血、用真诚,然后大家共其中,共研共教其中。这是中国才有的文艺学的‘革命公寓’。‘革命 ’,是这套公寓式理论的突出特点。”(P259)这既是中国文艺学界的历史状况,也是其当下状况:20世纪百年来,除了政治文艺学,除了西方文艺学,除了各种文艺学之外的理论主张、方法大杂烩炒卖的观念文艺学,再没有属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中国文艺学。 中国文艺学的历史与现实,一直处于寄生状态,它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本生性。中国文艺学的寄生性,直接地来源于中国文艺学界之生存的寄生性。文艺学界之生存的寄生性,既具有历史的绵延性,又具有多元开放性,从革命文化(20世纪初始)到政治革命再到观念、方法革命,这是一条绵延拓展之路;新时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观念革命和方法革命,同样在持续着对“中国文化”的革命,而在这种裹持着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观念革命与方法革命,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政治文艺学的“根本指导”。
中国文艺学界以丧失其本生性而追逐并快乐地游戈于其寄生性,才共同创造了这座坚若磐石的文艺学“革命公寓”。这座文艺学的“革命公寓”,是以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革命为奠基、以政治革命之成果----政治文艺学为钢筋铁架、以西方文艺学理论和西方其它各学科观念、方法为洋材料而建造起来的。
生存于这样一座能够轻松地就获得衣食饭碗和生存安全之政治保障的“革命公寓”中,做文艺学课题,写文艺学文章,出文艺学专著,只需要政治文艺学之指导思想的保障,只需要对西方各种文艺学的或非文艺学的观念、方法、理论的组合性贩买,只需要“趋新骛奇”(P176);在这座共建的寄生性“革命公寓”里,追求“四平八稳”,是其共识性努力(第194-197),经营“非学术化生存”,是其正常状态(202-205);在这座用革命和被革命之历史与现实打造起来的寄生性“革命公寓”里,文艺学研究不需要对话,自话自说以及相互照顾地保障人人不受侵犯之独白权利,即使偶尔产生论争,大家也“都乐于把否定对手的锋芒隐藏起来”,隐藏学术锋芒,“只是顺应时下语境的策略”(P19)这种人人独白而人人自得的学术生存状况,这种“偶尔露峥嵘”而始终隐藏学术锋芒的学术生存“策略”,恰恰最为真实地展示了无根之游的文论学者们怎样沦为丧失自我主体性和没有自我学术个性的“他者”(P192)。
因为,寄生性必然使学科成为他者,但寄生性首先使学者们成为他者,文论学者一旦在寄生中沦为真实的他者,就只能追逐西方人的屁股“跟着说”、“照着说”并进而“帮着说”(P192)。由于这种跟着说,照着说、帮着说的观念、方法、路子、模式,都差不多,即或时有说的方式、说的情态有所不同而产生了一些差别或“论争”,那也是说的技术问题,其相互之间从根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彼此都是寄生在西方文艺学肥沃土壤里和西方各种理论、观念、方法的保险战壕里“跟着说”、“照着说”和“帮着说”的战友与同志,相互维持这种共寄同生的战友和同志间的友谊纯洁性和独白权利的完整性才是根本,因而,这种“论争”也只不过是为“革命公寓”里四平八稳的枯燥学术生存制造一点瞬间的寄生性学术的活跃氛围而已。这就是20多年来国内的历次文论争鸣都“没有更深入地展开,常常是几个回合便悄然收兵”(P201)的根本原因。
寄生性与本生性是相对的。在自然世界里,寄生性是寄生者的本生性;在人的世界里,寄生性必以寄生者主动或被迫抛弃他的本生性为前提。因为在人的世界里,人的生命及其生存、人的精神及其探索,都是本生的。仅就后者是而言,人的精神及其探索的本生性,首先表现为它是传统的承续,其次表现为它是有民族文化、精神、思想的滋养。因而,本生性即是其自身之“格”的规定性。这“格”,就是指其自身存在与生存的本位、位态、范围、规范。在其“格”中,本位决定位态,也决定范围;范围决定规范。以学科为例,每一学科都有它成为其学科的既定的“格”,这个“格”规定了此学科在众学科之中的本来位置,这一本来位置使它获得了伫立于众学科之林的特有姿态;从这一本来位置出发而所形成的特有姿态,必然指向其对自身范围的规定性,即此学科“为何研究”、“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三个基本问题也由此构成了此学科的三个维度的自我规范,超出此,则是“越格”。
以此来看中国文艺学,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自身对象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纯正的中国体认方式、中国思维式、中国审美方式、中国情感方式和中国表达方式的艺术成果;中国文学的这些所有纯正的中国方式都必须通过中国语言体系来启动与实现,如前所述,自然语言永远只能是民族语言,中国文学永远只能是中国语言的表达与创造,因而,中国语言承载了中国体认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情感方式和所有的文学表达方式,并从而从内外两个层面规定了中国文艺学的自身本位。同时,也由于中国文学的中国语言化和中国(体认、思维、审美、情感、表达)方式化,形成了中国文艺学之自身血脉必然是纯正的中国化的:中国文艺学的自身血脉有两个东西,一是中国语言体系,即中国文艺学必须在中国语言体系中产生并运用中国语言体系构建自身;二是中国文论传统,即中国文艺学必须生根于中国文论传统并在其文论传统的土壤中开花结果。
中国文艺学的自身本位,决定了它必须属于自身并彰显自身的特有位态,那就是它必须朝向中国文学,必须朝向中国语言体系和中国文论传统。中国文学、中国语言体系、中国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文艺学建构的内在三维视域。以此本位和位态出发,中国文艺学“为何研究”、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之问题,才获得其自身的范围界定和性质规范。
当我们以此为视野来看,《纠葛》对中国文艺学那寄生性的历史与现实,来反思中国文艺学的“无根之游”,其目的是为呼唤当代中国文艺学回返自身的本生性,在其自身的本生土壤中重新建构自身的主体性,以此获得构入世界对话的主导地位。该著的意寓及其所张扬的理论实践理性批判精神,以此获得了划时代的特别意义,它体现出(相对文艺学界来讲)前所未有的锋芒和力求建构真正具有中国主体性和主导性的中国文艺学的时代雄心与学术勇气。
在《纠葛》看来,中国文艺学的“无根之游”,在于中国文艺学丧失了中国本位。中国文艺学对“中国本位的丧失”:一是丧失对中国文学本身的关注,这种丧失表征为在不同时期将此本位关注转换成非本位的革命关怀,20世纪初文论学界所关注的是如何以西学为武器来革中国文化的命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文艺学主题是政治革命;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其兴趣所在是西方的文论研究。正是这种对象与主题的偏移,使文艺学的文学导向功能丧失,形成中国当前文学的全球化“浮华体验”和媚俗化“漂浮”(P225—232)。二是丧失对中国语言的关注,从而用西方的概念语言来全盘替换中国的体验语言,用西方的概念思辨理性来取代中国固有的有机整体性的生存体验理性,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来化解中国的有机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第3章)三是丧失了自身的中国文论传统。
中国的文论传统,不仅体现其特有的体认方式、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而且包含了文艺学研究的独特方法,即有机整体性方法。由此独特方式与方法表征着中国人的特有精神智慧、生存方式和存在理想。当文艺学抛弃中国自身文论传统,也就是在抛弃中国文艺学的自身生存,因为“传统是一个连贯而下的历史过程,并且体现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只能是传统在那一阶段的表现,都只能是那一阶段表现出来的传统,它不可能是传统的全部,就像任何一条河流的段河床都不可能是整条河一样。”(P26)传统的不可抛弃性,就在于它具有家园功能和自我生长功能:“传统是家园又是魂魄。每个生存者都是有家园的,这是他所由出生的故土。在家园中常常会形成家园的启动,这导致家园中的家园缺失。当家园中生存时,家园即构成他的生存,生存很容易在生存中消隐,就像躯体在躯体中消隐一样。”(P5) “传统又是生存的魂魄,它是生存的随形附体,它激发生存智慧,活跃生存的生机与活力,并制导各种生存行为。”(P6)当我们对不可抛弃的传统予以主观想象的人为抛弃时,也就抛弃了我们的家园:家园之于我们是起点,也是目的;是土壤,也是生长本身;是过去,也是现实,并且同时也是未来。我们抛弃了传统,就抛弃了自己的生活起点与目的、生存的土壤与健康的生长本身,更是抛弃了我们得以生长的血脉承传与对未来的守望。一旦这样,我们就只能无根存在,随风漂浮。百年中国文艺学之所以最终没有建构起真正的中国文艺学,就在于它抛弃传统的无根性生存;新时期20多年来,中国的文艺学对自身主体性建设之所以举步维难,同样在于它在抛弃传统的忘形自得中无根漂泊:“我们是把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文艺理论之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伟大性学理深刻性,是已经被实践所检验了的,自不必说;但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的文艺学,把自己的根设定在一个西方思想体系之上,无论这个体系是何等的伟大与精深,倘若不经由真正的民族根本即传统的必要转化,也只能是外来的理论营养而不可能成为理论之根。”(P17-18)
因而,反思文艺学的“无根之游”,就是要重新认识传统、重新续弦被我们自为“断根”的文论传统、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智慧、思维、体认、表达传统,使之获得民族根性和文化根性,唯有如此,主体性建构才成为可能,文艺学走向世界对话的主导性才成为现实,文艺学学科建设才可真正拥有其不可取代和无可替代的学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