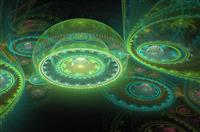到北京参加《原道》创刊二十周年纪念会回来,我一直在思考儒学在今天的状况和可能的安排与前景。这个问题在北京会议时由陈明先生提出“习大尊儒,儒门应当有何回应”的问题而受到关注。尽管前段时间对俞荣根教授和盛洪先生进行访谈时也提到,但这次在北京的讨论却格外引发思考。这次会上,我当时主要就中央党校赵峰教授提议儒学应当为目前的中国政治提供说明的问题作了一个表态,大意是说要遵循儒学的传统来讲政治和社会治理,把儒学自身的东西讲清楚是最重要的。当政者喜欢就采行,不喜欢就拉倒。为目前的政治做说明,那可能主要还是党校学者的事情。由于时间限制,这个表态没有展开讲为什么要这样。 这几天我越发觉得必须对儒学前景的相关问题做个讨论,才能明确今日儒门到底应当干什么,以及如何回应与政治方面合作的问题。
古代的儒学是一套整全的东西,具有一个文明系统基本形态的全面规模。它包含了从精神信仰和精神生活,到政治治理、社会建设和家庭生活,乃至天下秩序,以及各种知识追求和文化艺术等众多方面的东西。这样的儒学作为形成于三代传统,并在汉武帝之后获得官方和民间主导地位的学说,的确是一份丰厚的思想文化资产。但是,当今天习近平尊儒而再次提出儒家是不是应当重新回到过去那种在朝在野状态的问题时,这存在今天时代儒学格局的安排和前景这一新问题。问题远不只是目前情况下儒家跟官方政治合作与儒家道统的关系问题,或者儒家是不是应当还有独立性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儒学经由现代性而出现分化后,如何来界定儒学自身的问题。
应当特别强调儒学经由朱子“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路线后,实际上是开始了一个更加重视“分殊”,重视对天地万物分门别类地去求其所以然之天理和所当然之天理,并将其置于把所知之天理“存心”并“豁然贯通”以充实人心的天理内涵和“全体大用”,进而最终实现“法元亨利贞之天德”以“成圣”这样一个精神历程和框架中来的进程。这在知识的方面,实际上就导向了“科”学,亦即对天地万物进行科别化的系统地格致研究。各种关于我们如何处理人类和自然事务的问题,均从我们“格物致知”后所获得的道理和知识去寻求解决。如此,儒学就出现分化。那些由“格物致知”的路线所出现的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会越来越有其独立的知识标准和学科范式,并作为独立的学科,不再被认为是儒学或儒学的分支。比如,我们不可能把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称为儒学或儒学的分支。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囊括一切知识而最终不可避免地分化出独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当然,断了骨头,还须联着筋。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也应当从科学事业的文化精神层面重新回归儒家,特别是回归前述朱子系统的根本精神上来,使科学置于儒家文明的精神动力之上,避免单纯靠实用功利经济目的搞短平快的科学研究,如此才有可能在基础科学领域有重大建树。这自然是科学界的事情,咱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儒学的地盘还剩下什么呢?儒学能够持守的东西,或者说今日儒学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今日儒学的内容应当包含作为规模整个儒家文明,并作为其文明核心的宗教性儒教及其建立的精神生活,包括精神信仰、道德的修养塑造和礼仪生活等。这些方面可能更多关涉私人生活的领域。不主张儒教是宗教的学者,至少还是主张儒教应当在精神生活和道德教化方面扮演角色。这个方面属于儒家最传统的地盘。这一点应当不会有太大分歧。第二是政治哲学。尽管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也研究政治,但作为有明确价值立场和传统,并承担着通过人类基础秩序来实现某种传统理想和价值的政治哲学,却不是政治学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儒家经典传统相当多的内容涉及政治文明及其政治哲学那些非常基础的方面。因此,今天的儒家应当持守儒家基础政治哲学的地盘,应当在公共领域的基础性层面,包括基本宪制秩序方面仍然发挥作用(参见拙文《儒学的公共精神及其儒学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和贡献》)。当然,即便在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儒学仍然也有必要把涉及非基础层面的政治和政策问题交给各路左右派政治及其理论家,并谨慎地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如果左右派政治哲学家们也涉及到人类政治哲学的基础性问题,那么儒家自然还是秉持自身传统去寻求一个主流的保守地位。古典传统对当今政治生活的影响,往往是作为一种背景文明来提供一些非常基础的观念和道德,或者在基础宪制秩序的大关节目上提供某些深层次的框架,并非过度地走向前台去执政,或者充当国家意识形态。陈明先生提出儒教作为“公民宗教”的定位实际也涉及这个问题。第三是儒家本身的道统传承,特别是要讲清楚今天时代我们所梳理的儒家道统及其经典系统。这是我们用以指导儒家自身生活的依据。上述三个方面,如果用我本人的新古典儒学来讲的话,也就是新古典儒学儒教论、政治论和道统论。这三论的范围也就是儒学在今天的地盘,是可以被称为“儒学”的东西,其他则大体都分化出去独立成学成科了。
如果从上述安排来看“习大尊儒,儒门应当有何回应”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说我们将迎来一个儒学在朝从政的机会。这不是习大是否尊儒的问题,而是在儒学自身出现现代性分化的格局下,今天如何执政理政,应当奉行何种政策的那些事务,大多已经不在儒学的地盘上,而在各种具体政治理论、主张和科学的地盘上了。儒学坚守的精神生活和基础性层面的政治秩序,也许仍然会影响政治,但不是直接地执政。即便儒学家讲到今天哪种具体政治和政策问题,那也主要不是作为儒学家的身份来讲,而是作为其他方面的身份来讲。一个在儒学的领域作为“儒家”的人,当然也可以是政治上的左派或右派,可以对公共生活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可以上朝从政,也可以在野民间,但这跟儒学本身没有关系。就像一个基督教徒或神学家可以去从政或主张各种政治和政策,但这跟基督教本身没有关系一样。
一个远离具体政治事务的儒学对儒学本身来讲,可能更加便于发挥其在精神生活和基础秩序方面凝聚人们的作用。设想一个儒家的政党,或者把共产党儒化成一个奉行何种儒家具体政治主张的党去从政,无论它是政绩卓著,还是声名狼藉,这对儒家本身追求的基础性层面作用来讲都可能是失败的。因为那意味着儒学及其文化传统作为中国人民长期的主流思想和文化对这个国家和天下广泛沟通联接的作用,以及避免把政治分歧过度引向人类生活的作用都不可能实现。而这一点,在一个生活世界被人的过度自由日趋搞得崩溃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儒学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牌,请多珍惜,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易出手!什么问题非要儒学家出面说话,那恐怕一定是非常地严重,或者涉及非常基础的事情了。总之,儒门不能放水,要慎重安排和对待自己的角色。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2014年12月27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