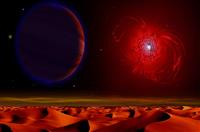【摘要】静安大火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建构有效的问责制来督促政府责任行政以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的难题。基于我国特色的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我国行政问责机制在面对这类重大事故时虽具有高效全面的优点,但却因为难以保证问责的长效性与深入性而难以保证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对此,需要建构公共参与问责制来弥补其不足。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行政问责制建构的其他问题,尤其是行政价值多元性所决定的行政问责制的类型化建构问题。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重大事故问责;公共参与;行政价值;类型化
民主体制如何保证政府去做他们被期望去做的事情?对这一问题的简单回答就是政体通过坚持其雇员要对他们的表现负责来确保有责任心的行为。更为完整的回答则是要求考核政府雇员所面临的角色期待和可用于处理公共部门问责关系的机制的范围。[1]就此而言,问责制不仅包括了对被问责者的惩戒,还包括着如何使被问责者去实现问责者寄予他们的期待。应该说,对问责做这样的理解是抓住了问责制建构的核心,即问责的目的不在于惩戒,而在于通过包括惩戒在内的系列方法、程序来让政府回应、实现人民的需要。这一点,对于重大事故的责任问责制尤其重要,因为面对引起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事故,最重要的是如何避免损害的再次发生。而这,正是本次静安大火给我们提出的难题。为此,本文以静安大火问责过程为起点,尝试对如何建构我国的重大事故行政问责制提供一孔之见。
一、对本次问责过程之梳理
可以说,这次事故引发了一阵强力的行政问责风暴。从媒体反映来看,此次问责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可,几乎没有人对其提出异议。笔者认为,这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因:
(一)问责具有高效性与全面性
所谓高效性,是指政府的问责措施以及负责措施能够迅速到位,不拖延、不推诿、不逃避,迅速回应人民的各种需要:救助、善后以及问责;所谓全面性,是指对违反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乃至政治责任的所有公务员都能够予以严格问责,不使一人游离于责任之外。高效、全面的问责既有利于落实责任、提升问责的有效性从而增强问责对其他公务员的警示作用,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又有利于恢复甚至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因此,问责制度的建构和实施必须满足高效与全面标准。从此次静安问责事件来看,我国问责体制一旦行动起来,还是能够满足这两个标准的。
1、政府迅速动员起来全面承担善后责任
一是补救。政府不仅迅速动员起来救治伤员,并对受灾居民展开及时的心理干预。与此同时,政府迅即成立相关机构组织研究部署灭火救援,指导抢险救援和事故调查等工作。除此之外,政府还立刻启动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日常检查制度的建构工作,严管建筑节能改造、禁改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并对建筑市场开始整顿,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是赔偿。政府不仅迅速决定依法为每位遇难人员提供约96万元赔偿和救助金,而且对受伤、受灾人员将分别按伤残赔偿、政府综合帮扶、爱心帮扶等方面给予赔偿和救助;房屋赔偿问题按照“市场价格、全额赔偿”的原则进行,确保其公平性;财产理赔问题也通过由居民自主选择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受灾居民家庭财产评估的程序来为依法赔付提供依据,确保公正、公平性;对受灾居民的回搬工作也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和建议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抓紧推进实施,确保合理性。[2]
2、政府迅速动员起来对相关人员进行全面问责
在行政国家时代,控制公务员已经变成民主政治的最紧急事务之一。[3]这是因为,国家权力在制度层面上是由各种国家机关所掌握的,但实际上是由具体的官僚所行使的。如果仅仅只注重对行政机关施加责任控制,那么各级官僚就会在机关责任的庇护下逍遥法外,权力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正如哈耶克所言,当今人们责任感之所以削弱,是因为责任的集体化;如果要让责任有效,那么责任就必须是个人的。[4]因此,行政问责制的主要针对对象应该是官僚,应该通过有效的公务员个人问责制将责任切实落实到具体公务员身上,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惩戒与制裁。
首先,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静安区长等在不同场合都自承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表达了对受害人和市民的歉意。这是一种政治责任的承担方式,体现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自我问责。
其次,事故一发生,上海市、国家安监总局和公安部就成了相关机构来调查事故原因和责任。事故于2010年11月15日发生,2011年8月2日政府就完成了对全部26个刑事责任人的法律问责;而在此前的6月底,国务院安委会即已经通报了事故调查处理结果,并对相关党政机关及相关国有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作出了处分建议并获批准,从而完成了对其他责任人的行政问责。
再次,这次问责风暴不仅席卷了上至上海市副市长这样的省部级高官,还囊括了下至派出所消防民警这样的科员级别的国家公务员。可以说,凡是其职责和事故具有一定关联、且被认为对事故之发生具有一定责任的公务员,都被施加了惩戒性问责。
(二)问责具有正义性
1、刑事问责。根据判决,此次共有近20个政府公务员或国有企业中的具有公务员色彩的国家工作人员(如上海市静安区建设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被施加刑事责任。其中静安交委主任高伟忠,因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两罪并罚判处17年刑罚。副主任姚亚明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刑罚;静安区建交委综合管理科科长周建民与静安区建交委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权则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处以13年6个月的刑罚。[5]而作为事故的直接责任人的那两个民工,一人缓刑一人免于刑事处罚。政府官员获重责、而直接责任人免责的做法既充分体现了政府机关自我问责的态度,也体现了对事故责任真正原因的认识,因此赢得了大众、专家、受害人和媒体的认可。
2、行政问责。行政问责首先意味着被问责官员的行为和事故并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他们无需承担刑事惩戒。在这个意义上,法律问责制的实施符合了法治的要求,被施以非法律问责的公务员并不因为事故的严重性而遭受不应有的惩戒,其公务员身份并不因为事故而失去,其身份权并不因此而被剥夺。其次,非法律问责也意味着他们虽然无须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但仍然对事故具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责任,即国务院国务院安委会所指出的事故原因第四、第五条、第六条:上海市、静安区两级建设主管部门对工程项目监督管理缺失;静安区公安消防机构对工程项目监督检查不到位;静安区政府对工程项目组织实施工作领导不力。[6] 因此,对他们的问责总体上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
二、我国重大事故问责制的内在逻辑及其反思
(一)我国重大事故问责机制的内在逻辑
上述这种针对重大事故而启动的问责机制之所以全面而高效,自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这三大根本原则,[7]以及这三大根本原则所决定的诸如公务员的非政治中立化、党管干部原则、行政管理的双重领导制等原则。
首先,从政治伦理上说,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原则决定了党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因此,只要发生了事故,不管这个事故是否由政府引起,党和党所领导的政府都必须站出来组织善后、问责与补救。从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原则“不把个人和政府对立起来,个人被同化在政府、国家之中,也克服了中间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取消了社会—国家的二元对立。社会的就是国家的,是国家的一部分”。[8]因此,党和政府必须对整个社会负责。而面对社会所出现的问题,人民也会寻求党和国家的解决,党和国家要是不能回应人民的需要,就会面临正当性方面的质疑。因此,一旦人民群众的要求足够集中和强烈,党和政府就会主动站出来善后、问责。
其次,这些原则决定了政府体制的统一性,进而决定了政府在面对灾难实施问责时的高效性与全面性。基于党的领导与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旦上级党政机关作出了决策,下面各级政府、各部门就会迅速运作起来,补救的补救,问责的问责,而无需体制外大众、媒体的驱动。就此而言,尽管重大事故往往侵害了许多人的利益,这些人是最为主要的问责主体,问责动机也最为强烈,但基于上级党政部门的主导作用,这些受害人往往无需启动问责就能看到相关责任官员被问责。
再次,这些原则决定了对公务员的问责不仅可以通过明确的法律来进行,而且在无法通过法律来问责的时候,还可以通过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于公务员的非政治中立化而运用高度政治化、强制化的公务员伦理乃至党员伦理来问责。如此一来,不仅领导职公务员不能逍遥与责任之外,而且是办事级别的公务员也不能游离于责任之外。
最后,这些原则决定了问责的相对理性化。针对公务员的问责,不管是来源于党和政府之外的力量的推动,还是源于党和政府内部力量的推动,最终都要回归到党和政府组织的层面,回归到组织内部官僚等级制问责逻辑,从而实现问责的相对理性化。进言之,尽管有些问责,从一开始是由外部推动的,具有西式政治问责制色彩,[9]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官僚等级制问责逻辑。而这种逻辑比较能够实现责任追究的理性化。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问责本身要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效果,还因为官僚制问责的逻辑本身。细言之,官僚问责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上级权威和所能掌握的资源,[10]而只有问责的公平性和理性化才能实现和维护问责的权威性,否则对于官僚制团体内部士气就是一种打击,所以上级机关在决定惩戒种类与手段时,必须考虑问责的理性化问题,必须考虑责任分配的公平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大抵可以被归为域外的政务类公务员序列,但静安区长、区党委书记、副市长等人的责任并不相同,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表明这些人虽然都承担性质类似的领导责任,但其责任还是与其职位职责成正相关关系的。
(二)当前重大事故行政问责机制的不足
基于我国政治与行政体制的上述特点,一旦重大事故发生,上级党政机关总是能够迅速站出来主导问责。[11]但是,问责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迅速而全面的对受害人的补救,也不仅仅在于猛烈而全面的惩戒,更在于通过问责确保行政对人民负责,确保行政能汲取教训、改过自新避免类似灾难的再次发生。进言之,问责的要义是督促和确保政府将来去做什么,而不仅仅是在做了什么之后如何追责。那么,这种党政主导型问责制能否确保这样目的的实现呢?
在我看来,当前这种上级党政机关主导问责的模式,可能会因为过于依赖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这两大法则而忽视并缺乏外部渠道的持久、有力的督促,进而影响问责的深入性和长效性。所谓问责的深入性,是指对事故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反思,并对其进行问责,进而找出相应的对策,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1、难以确保问责的深入性
事故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更深的行政管理价值取向之争。有学者将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大体分为三类:经济而目的明确的政府的价值,即成效提供价值;忠实与公平价值,即操行价值;安全与适应性价值,即适应性价值。[12]一般而言,上级党政机关更倾向于成效提供价值,但也同时希望下级机关在实现这一目标时确保安全和适应性;老百姓更直观于操行价值与安全价值,同时也希望成效提供价值所推动的繁荣;行政机关更喜欢安全价值,但绩效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体制内的地位。而且,由于官僚制对上负责的特点,行政机关总是习惯于服从上级所既定的政府议题并向这方面倾斜政府执法资源。[13]在这种成效提供价值的驱动下,行政机关往往奉行管理主义以促进成效提供价值,并且不太注意对操行价值的遵守(比如组织性失误)和对安全与适应性价值的遵守。由此可见,重大事故除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等原因外,往往和这种成效提供取向的行政管理模式有关。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地方政府GDP而违法征地搞房地产、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或是忽略环境保护默许高污染企业扩张正是因为这一价值取向。因此,要有效避免重大事故的再次发生,除了强化监管与制度设计外,还需要警惕事故背后的管理主义倾向,强化操行价值与安全价值。而恰恰是对这一方面,当前上级党政机关主导的问责制难以有效发挥问责作用。在既定的成效提供价值取向下,由上级党政机关主导的问责,通常会优先于或集中于比较浅显的问题,而不会集中于其他的大众所关注但又没有有效表达出来的、或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关键问题,更难以上升到反思并改进政府管理价值取向与方向的层面上去。也就说,问责的议题是由上级党政机关所安排并主导的,
所以它并不会去反思其它可能和事故原因有关的议题,更不会为此作出相应的政策性改变。比如,此次问责的炮火集中于各级政府对建筑市场的监管不力以及消防部门的工作不力,但却没有涉及其他问题。比如说有的人质疑基于节能减排的需要而在静安区这样一个非工业化区搞公寓节能改造是否有合理性,[14]但此次问责过程并没有就此进行回应,事后也没有看到因为这个理由而停止节能改造的安排。这说明,在政府可能不想否定其既定的行政目标的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外在力量的介入,政府就很难会反思事故背后更深层、更长远的原因。而恰恰是对于事件背后更为深远的原因的反思以及相应的调整,才有可能真正避免类似事故再一次发生。
2、难以确保问责的长效性
一方面,因为缺乏强力的外在监督,被问责对象比较容易复出,这就降低了问责的警示性与权威性。很多问责在起初声势浩大,对被问责者给予了强力惩戒,给其他官员带来强烈的警示效应,大众也很满意。但一段时间之后被问责官员却没有向公众作出合理解释,就悄无声息地复出。这不仅会给其他官员带来不好的暗示,从而影响问责的警示效果,而且会引发大众的不满。
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后续的监督,仅凭问责难以促使下级机关与公务员真正形成勤勉廉政的作风与制度。上级党政机关主导的问责必然导致问责者与被问责者之间存在这样一种模式:下级机关与公务员引发事故——上级党政机关启动问责——上级党政机关完成问责功成身退——被问责者落实补救与改进。在这样一种问责机制下,一旦上级党政机关完成事后问责,下级机关又一次处于缺乏外在监督的状态,下一次事故又可能因为下级机关缺乏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而发生,然后上级党政机关不得不再一次启动事后问责。如此循环,但问责所要实现的效果却没有真正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问责机制的效力取决于问责的警示作用和被问责主体的自律机制,但因为缺乏长效的在场监督,在时隔一段时间之后,地方官员就有可能放松警惕,故态复萌,或腐败、或懈怠,对违法违规现象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甚至放纵或是不下基层不强化监管,那么事故的风险就会越积越多并从量变质变为现实的灾难。
三、事故问责应当借助公共参与
(一)公共参与问责的必要性
针对业已发生的重大事故,政策该如何变迁、制度该如何建构以避免灾难的再一次发生,管理学界提出了两种理论,一种是警惕衰退理论,另一种是议程设定理论。限于篇幅和主旨,本文不打算详细介绍这两理论及其对公共行政管理的影响。笔者所想指出的,无论是警惕衰退理论,还是议程设定理论,都指出如果想要避免事故的再次发生,就不能不依靠公众持续、有力的参与。在警惕衰退理论看来,事故的再一次发生,是因为行政机关外部的公共团体没有给行政机关提供持久刺激,以致他们丧失了对事故的警惕,放松了管理;在议程设定理论看来,事故的再一次发生,是因为没有外部团体参与公共行政管理的议程设定,没有引导或导致公共行政议程向有利于事故规避的方向转变,由此导致事故在既有的行政议程之下再一次发生。[15]
由上可见,借助公众参与式问责,一方面可以解决上级党政机关问责之后监督乏力的困局,另一方面则可以群策群力,全面、深入的探究事故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探究如何解决事故背后的原因,甚至参与决定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以及政策变迁。当然,其前提是公共参与是持久的、有力的,因此,建立有效问责的公共参与机制必须注重公共参与的组织化,实现公共参与者的问责联盟。
此外,有效的公共参与还可以缓解党和政府所面临的问责压力。诚如沈岿教授所言,舆论的聚集毕竟有瞬间性、一时性、情绪性、易变性、复杂性等特点,不见得能够形成较为冷静、理性的思考和观点。若一味顺从舆论,也会导致“为了阻抑舆论”而问责,不仅问责官员感觉委屈,也容易导致作为补偿的快速复出。[16]因此,建立第三方的有力而长效的公共参与平台与公共参与组织,通过吸纳、集中、提炼公共意见,引导公众通过辩驳而形成理性化的公共舆论,就可以形成比较深入、比较全面、比较客观、比较有力的公共意见,就能有效缓解党和政府所面临的问责压力,推动政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问责。
(二)公共参与问责的限度
限于篇幅,本文不欲在此探讨如何建构公共参与问责制。[17]笔者所想强调的是,在建构这一机制时,必须注意其内在限度。
其一、公共参与问责制是非正式的问责制。公共参与虽然是现代民主的重要发展与重要形式,但其毕竟不是票选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其民主性有限。进言之,公共参与仅仅是提供一个大众参与国家管理、公共管理的平台,决不像票决民主那样具有效力。因为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任何制度性的有效力的民主都必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框架下才具有合法性,公共参与的问责绝不能指望自身有着法律效力。[18]因此,公共参与固然可以对政府问责产生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绝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效力,而其影响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也不完全由公共参与自身来定,其为政府的接受程度,由党和政府自行决定。也就是说,公共参与的问责,只是非正式的问责,起补充作用的问责。其意义不在于问责有无效力,而在于为更为全面、深入和高效的问责提供外在的、理性的、长久的动力与支持。当然,也无需因此认为公共参与就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域外学者基于对我国的实地考察,发现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西式民主官僚制度的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地方上的社会团体的非正式问责,督促地方政府提供法律本身并没有规定的社会服务。[19]因此,我们无需对非正式的公共参与问责制的作用妄自菲薄。
其二,尽管基于我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公共参与问责制虽不至于发展为西方多元民主制下的以利益交换为实质的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政治问责,[20]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公共参与问责的平等性问题。毕竟,公众自身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的人、不同的团体参与公共问责,都有着各自的价值追求,这就难免会出现组织能力强、参与意愿强烈、偏好表达明确的组织或团体把持公共问责议程、进而以此为基础向政府推行其组织偏好并排斥其他社会团体或大众表达问责关注的现象。这不仅违背了公共参与问责制群策群力、吸收不满、凝聚民意、增强民众信赖的主旨,还可能导致公共参与问责制因为缺乏大众参与而后继乏力、无以为续。因此,公共参与问责制要建构相应制度来确保内在的平等性和参与的广泛性。
四、代结语:行政问责制度建构所需要注意的其他问题
行政管理行为是如此重要……,以致任何有着宪政政府的国家都不可能允许行政管理完全放任而不履行其责任。[21]对此,大多数论者认为,要有效的问责公务员,应当建立统一的法制化问责体系,而我国当前问责制制度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统一的问责法制体系,问责制度没有法制化,问责的标准、原则、被问责对象的权利救济等都没有明确规定,严重影响了问责制度的实施。[22]可以说,问责的法制化已成为法学界的广泛呼声。
然而,完美的控制行政既不是一蹴可就之事,也不是一部法典就可以完成之事。从本次静安大火问责就可以看出,法制化的问责存在着重大缺陷,在问责标准、适用对象、问责事由以及问责程序方面都存在着种种限制。[23]例如,在此次事件中司法机关之所以能对部分官员进行刑事责任问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构成了刑法上违犯刑法义务的行为。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证明他们违反了刑法义务,那么法制化、明确化、正当程序化的问责就难以进行。同样,如果没有明确的条文与依据证明官员违反了行政上的职务义务、他们的行为与事故存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法制化、明确化、正当程序化的行政官僚等级制问责也难以进行,那些慵懒的官僚由此就逃离了问责制的控制。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出如下几个结论,或者说,行政问责制度建构所需要注意的其它几个问题:
1、问责制度的建构应该以本土为基础,在注意他国或地区行政问责制之教训与不足的基础上吸取其他国家或地区问责制的优越之处。正如新加坡公共管理学者Haque所指出的,问责的内涵经常随着其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构成、意识心态倾向以及文化信仰而不同。[24]因此,根植于西方多元民主、自由主义法治与现代官僚制体制的问责制及其学说尽管可以作为我们探索与建构本土问责制的智识资源,但也不可完全照搬,其分析方法与理论框架需要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其成就与教训要经过全面的总结与反思。比如,多有学者认为对我国公务员的问责,既没有遵照正当程序原则,也没有遵照权责一致、过罚相当原则,并由此主张应当实现公务员内部行政责任处分的法治化。然而,姑且不论西方战后公务员管理体制宪法化以来公务员管理体制的低效化与无力化是否适应问责公务员的需要,[25]单说这种法治化的主张就并不符合我国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及其背后的宪政体制。基于我国公务员之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其任务的强烈政治性,对公务员的处分,除非其剥夺公务员的公务员身份,否则只能交给有经验的行政管理者来认定和处理,法律人很难有专业的法律训练来做出裁断。因此,这样的惩罚行为必然要因为其高度技术性和政治性而被认为是立法不允许审查或不适合审查的不可审查行为。[26]反过来说,我国之所以规定行政机关内部人事行为不可诉,其根源不在于所谓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而可能根与于我国这种行政责任与政治责任混一的体制。
2、就像人类自身如今所身处的乃是一个诸神反复争斗的世界一样,行政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相互竞争的价值所带来的压力。如前所述,操守与成效提供、成效提供与安全等价值取向都会对行政管理的方向产生根本性影响,并导致行政管理者承载着多种甚至相互冲突的责任,进而面临着交叉的问责压力。[27]因此,我们在面对问责这一问题时,也不能不靠虑这些价值的影响并反思依据某种单一标准而问责的正当性。正如罗姆泽克所言,选择何种问责制来问责,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即机关任务的本质(技术层面的问责制)、机关领导者所采取的管理战略(管理层面的问责制)和机关活动的制度性内在(制度层面的问责)等三大因素来灵活决定。[28]
3、行政责任的多样性决定了问责机制的多样性,决定了问责制建构的多维性,也决定了问责制之分散性。或者说,行政问责制必然是由多种内在逻辑各异的类型所组成的问责体系。而且,行政价值的多元性必然会导致不同行政问责制类型之间存在冲突,必然会决定它们不可能统一到一部所谓的问责法典中去。换言之,所谓统一的、法制化的问责制,也不过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它所体现的,表面上看来是对完美无缺的法律世界的追求,实际上则是对法律帝国主义的迷信,对理性和确定性的迷信。这一倾向,是我们法律人所应当注意的。
陈国栋,大连理工大学法律系讲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1]Patricia W. Ingraham ,Barbara romuzek, New paradigms for government:Issues for the Changing Public Service,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Inc Pub.1994. 263。
[2]上海11.15特大火灾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实录,http://news.163.com/10/1123/17/6M6JR6QU00014AEE.html
[3]Rourke, F. E. "Responsiveness and Neutral Competence in American Bureaucrac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2,(6).
[4]Friedrich A.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Liberty, Chicago: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978.p83.
[5]专家称轻判上海大火案2民工体现对弱势群体宽容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8-04/013722929595.shtml
[6]国务院安委会通报上海高楼火灾事故处理结果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7-12/154822800817.shtml
[7]关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这三个根本法的内涵的阐述,
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8]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9]美国学者罗姆则克将行政问责制分为四种,其中法律(legal)问责制和政治(political)问责制由行政机关外部主体推动并落实,官僚等级制(bureaucratic)与专业(professional)问责制由机关内部主体推动并落实。参见Barbara Romuzek,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1987(3)。我国学者宋涛据此认为由外部媒体、网络或公众推动的问责属于政治问责的范畴。参见宋涛:《社会规律属性与行政问责实践检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78-79,181-184页。
[10]Barbara Romuzek,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1987(3)。
[11]根据宋涛教授的总结,在中国行政问责实践中,党政部门是唯一的问责起动者,并且问责启动者几乎全部为“上级党政部门”。在195个行政问责事件的问责起动构成者中,“上级党政部门”占97.4%,体现了非常显著的集中趋势,显示作为影响问责事件能否立案处理和问责发动机制构成要素的问责起动权力几乎全部掌握在“上级党政部门”手中。宋涛:《社会规律属性与行政问责实践检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12]Christopher. Hood,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1(69).
[13]这正是选择性执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换言之,有的时候政府在某些方面执法不足,是因为它认为其它方面更需要加强执法,或是认为这方面加强执法会导致其它行政目标的受损。参见胡智强:《论选择性执法的法律规制》,《学海》2011年第2期。
[14]斯伟江:《检讨上海大火的10个关键词》,http://news.sina.com.cn/pl/2010-11-18/105321492623.shtml。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节能减排就是事故背后的深层原因,笔者只是以此为例指明事件背后可能还存在着其他有待进一步反思的原因而已。
[15]Robert Schwartz 、Raanan Sulitzeanu-Kenan,Managerial Values and Accountability Pressures: Challenges of Crisis and Disaster,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14, no. 1, pp. 79–102 2004。
[16]沈岿:《问责官员复出规范化及其瓶颈》,《人民论坛》2010年第5期。
[17]对此可参见王锡锌教授的相关文章与论著。
[18]关于民主集中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生活与政党体制的决定性影响,参见赵宬斐:《民主集中制: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
[19]LILY L. TSAI,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7(2).
[20]罗姆泽克也承认,政治问责是一个更为开放和代表性政府的基础,尽管它“看起来在政府项目的管理中会促进偏私乃至腐败”。See Barbara Romuzek,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1987(3)。对此也可以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版;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周军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1]FRANK J. GOODNOW,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An Analysi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s, National and Local, of theUnited States,England,FranceandGermany.New York: G. P. Putnam, 1893. p.135.
[22]如曹鎏:《行政官员问责的法治化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版;陈国权:《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高志宏:《困境与根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考察》,《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0期。
[23]详尽的阐释,参见陈国栋:《行政法律问责制探析》,待刊稿。
[24]M. Shamsul Haque, Significance of accountability under the new approach to public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00(4).
[25]See D.H.Rosenbloom, Som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Drift Towards Liberation of Federal Employees. Public AdministrationReview, 1971 (4);David H.Rosenbloom, Robert S. Kravchuk, Public Administration :Uderstanding Management,Politics and Law in the Public Sector(5th),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p565,
[26]See K?C?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text(3rd),Minn: West Publishing Co,1972, p508.
[27]BarbaraS. Romzek、PatriciaWallace Ingraham,Cross Pressures of 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 Command, and Failure in the Ron Brown Plane Cras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3).
[28]Barbara Romuzek,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1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