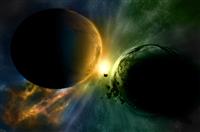摘要: 全球宪政纠正了国内宪法体系因全球化而日益增长的缺陷,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合法化的契机。全球治理和全球宪政的依托和互动,催生了对国际法宪法化趋势和宪政理论的探讨。传统国际法缺乏与制宪权理论相称的法理,无法完全论证国际法在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现代国际法出现了共存、合作与宪政的国际法三者具有内容的递进性和时间的共时性的发展,宪政的国际法成为国际法三分结构的最新分支。当代国际法的宪政转向,在实践中表现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人本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与此同时,全球宪法化的过程是有条件的并存在路径依赖,国际法的宪政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近20年来,全球治理理论在多个学科甚至跨学科中广泛运用于对国际事务的描述,特别是更新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和权力导向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念。尽管同样是针对全球或国际问题的一种理论,全球宪政理论的兴起仿佛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如果说全球治理强调“没有政府的治理”,全球宪政则暗示着“非国家的宪法”。本文试图揭示全球治理与全球宪政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对“宪政的国际法”进行理论建构。
一、全球治理和全球宪政之依托和互动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日益成为一种普通知识,应运而生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一种描述,全球宪政理论则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宪政视角的国际法律分析框架。有学者认为,全球宪政依托于联合国、欧盟和世贸组织等全球治理“位置”,宪政、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为其主要发展和争论问题提供了跨学科的分析[1]。与格劳秀斯时代主要关注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问题相比,今天,代表着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或者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问题”,以及牵涉到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区域问题”,成为了关系到全人类福祉的新领域、新问题。这些全球问题和区域问题突破了传统的地域和主权界限,以其如同核爆炸式的放射性后果令各国牵涉其中。
全球治理之使用“全球”而不是“国际”措辞,表明全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活动的多层次特征,倾向于淡化国际、跨国或者国内层面的区分。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除国家及其政府外,全球治理的主体还包括正式的国际组织以及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等。全球治理理论也强调在营造共识的基础上,以协调的方式构建多层次的网络,对全球问题实行各种路径的综合治理。简言之,全球治理具有对象的全球性、主体的多元性、层次的多级性和方式的多样性等特征。实际上,在冷战后包括近年来的“反恐”、“低碳”时代,全球治理使主权国家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之中:一方面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另一方面却在经历着一个权力逐渐分散和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国际社会成为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超国家组织”、形成中的跨国甚至全球公民社会共同治理的领域。“治理”以各种方式发生在地方、国家、区域、国际和跨国、全球或世界等各种层面。有学者提出,所谓“治理的国际法”正在出现,其主要特征是国际法的主题事项显著扩展、国际法的制定程序逐渐削弱了国家的同意与国际法义务之间的关联以及国家在解释和适用国际法时,逐渐失去了灵活性。特别是国际和跨国的制度、机构和实践日益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简言之,“治理的国际法”正在使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界限逐渐模糊[2]907-931。在此基础上,既然“治理”以各种方式发生在各种层面,相应的“宪法化”或“宪政”也可能发生在超出国家以外的其它层面,并被认为是“全球宪政”、“多层次宪政”、或者“宪政网络”(constitutionalism network)[3]39-41。
全球宪政理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全球治理理论,而且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并发展出独特的全球宪政的国际法学面向。其关键在于,全球治理理论本身不能使全球治理获得合法性,而只是一种描述性的阐释[4]1079;而全球宪政理论则以宪政为视角①[5]203,提供了使全球治理合法化的契机,具体体现为规范、功能和价值三个面向。
在规范的意义上,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全球宪政理论要求并认为国际法体系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等级。国家宪法的基本功能是,宪法在所构成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效力上的至上性,不仅组织了一种法律体系,而且位于法律体系的顶端。而现实的发展在于,国际法已经出现了体系化、纵向化甚至宪法化的趋势。就传统国际法而言,国家自创立时起就置身于国际法某些基本性质的规则的框架中,这类规则确定其基本的权利和义务,而无须(without)其同意。这类基本规则主要是指国际法中确定其渊源、主体和适用以及国家管辖范围的分配之基本原则和规则[6]37-115。从现代国际法来看,有些国际法规范甚至有违(against)国家的意志,例如被认为处于国际宪法核心的国际强行法规范[7]195-374。这类规范超出了国家与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特别是国家的“立法”功能之外,成为国际法的高级法(higher law)[8]217-243。简言之,国际法的宪政发展,使全球治理活动逐渐合法化,并为全球宪政的正当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功能的意义上,全球治理意味着各种非国家的国际组织、国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同样分担着国家的治理权力。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简言之,权力已经分散,而且不得不分散。
问题在于,当主权权力或者公权力日益在国际层面直接或间接由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者行使或者主导行使时,就需要论证这类行为者的权力如何生成和发展,以及其边界和限制。而全球宪政理论的强项之一,正在于为其提供一个公法视角的法律基础。全球宪政关注在国际或者说非国家层面政治权力的分配、构成和限制,强调公共决策的权力及其控制日益从民族国家向区域和职能性的非国家行为者乃至非政府行为者转向。正如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秩序的宪法化是指国际法秩序主体权能组织和再组织、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9]51。根据国家层面的宪政理论,政府由宪法构成,以限制其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即所谓有限政府;这同样适用于超国家和国际机构形成的自治网络,谋求在国家权力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正当地建构国际公权力。有学者认为,确定公权威(public authority)如何行为的方式之基本法构成了国家的宪法,以此比较国际政治过程,在全球政治体(global polity)中管制政治活动和关系的最重要规范的总体,可以被称为国际宪法[10]1380。简言之,全球宪政谋求通过国际法规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公权力,进而实现规制国际政治社会。
在价值的意义上,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按照全球治理理论,政府“统治”权威的最终保障来自于对合法暴力手段的垄断,其以强制为特征;“治理”的权威主要源于共识,以自愿为本据,离开了普遍认同,治理就难以真正发挥效用。而全球宪政理论为所谓普世价值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从而为全球治理在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提供指南。这体现为全球治理不仅要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且应彰显“共同之善”(common good),并创设政治框架促进对共同之善的宪法商议②。全球治理具有或需要具有对共同目标、共同命运、共同遗产以及对全人类的共同关注,这些公共物品所体现的全人类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统称为“共同之善”。例如,以国家之间为主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最典型的共同之善[11]15。正如有学者认为,全球宪政是指推动按照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指导政治权力的全球性法律共同体,主张国际体系的宪法特征是奉行和保证基本法律价值,以按照共同价值和共同之善规制和引导各政治强权实体[12]86。
总之,全球宪政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全球治理,又能动地为全球治理提供补偿、基础、保障和指南。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宪政理论的这种依托和互动关系之中,催生了对国际法宪法化趋势和宪政理论的探讨。从国际法的相应发展来看,可以认为,全球宪政既是指一种思潮和政治设想,倡导在国际法领域施行诸如法治、制衡、人权保障和民主等宪法原则,旨在改善国际法秩序的有效性和公平性[13]1-2;也是国际法逐渐出现宪法特性的现实过程,尽管形式意义的国际宪法尚不存在,国际法秩序中的基本规范的确履行着宪法功能,全球宪法即管制全球政治体中政治活动及其关系的最重要规范[14]397-411。全球治理的全球宪政面向,要求在国际法学中建构一种宪政理论,分析全球宪政趋势,解释国际法的宪法和宪政问题,提出国际法宪政的理想前景以及指导国际法的宪政实践。本文以下即对此作出初步立论,以求批评及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1964年,德裔美国国际法学者沃尔夫刚•弗雷德曼(Wolfgang Friedman)在《变动中的国际法结构》中提出,国际法的结构一般经历了从共存(co-existence)到合作(co-operation)、再到共同体(community)的发展。从共存的国际法到合作的国际法,是国际法从主权行为之间的协调过程到国际法本体的发展,宗教、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多种多样将对合作的普遍性提出挑战。共同体的国际法在支持共同体利益优先于个体国家利益的进程中不断进展,特别在国际环境法、推动国际共同体关注自决权问题的一系列规范和人权的国际保护中得到体现。弗雷德曼指出,如果人类希望实现更有效的国际(社会)组织化,则国际法必须发展为宪法[15]60-71,131,152-160。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霍夫曼也对国际法体系结构进行了审视。霍夫曼认为,在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三种国际法:关于政治架构的国际法,诸如界定基本状况、某些基本准则和国家间开展政治博弈规则的一揽子协定;关于互惠的国际法,规定在各种具体问题领域中形成和发展国际关系的条件和规则,一般受关于政治架构的基本法规限定;关于共同体的国际法,处理那些不能以相互分离的、处于竞争状态的各国国家在利益上的互惠为基础,只能以其行动超越了狭隘国家利益的共同体为基础才能得到最佳解决的问题[16]205-237。
德国国际法学者图姆夏特认为,国际法逐级成为一种复合的体现,将经历共存的国际法、合作的国际法、作为全面指导社会生活的国际法和国际共同体的国际法等四个阶段。在此意义上,“国际法可被视为人类的宪法”[17]37-50。
我国学者易显河提出,国际法在冷战巅峰时期表现为共存,在缓和时期表现为合作,在冷战后表现为共进(co-progressive);所谓共进的国际法是一种包罗万象,在道德和伦理进步方面比在其它方面更为专注的法,以人类繁荣为终极目标[18]55-68。
我国学者古祖雪提出,传统的共存国际法以国家间的共存、独立与平等为价值,主要规定国家对国家的义务,强调维护国家行使主权的权利。合作国际法以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与发展为目标,主要规定国家对国际社会的义务,要求让渡国家行使主权的权利。人权国际法原本属于“合作国际法”的范畴,但它以人的存在与全面发展为诉求,主要规定国家对个人、国际组织对个人的义务,主张约束国家行使主权的权利[19]37-38。
在上述对国际法的三分结构分析中,一个共同点是在国际共同体、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个人的关系之中展开对国际法发展形态和状态的叙述,主旨都是试图破解国家主权、国家间关系和国家利益等“三国”之咒,以国际法的应有价值或者说“共同之善”建构国际法的理想前景。
在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论基础上,笔者提出,当代国际法出现了共存的国际法、合作的国际法与宪政的国际法三者具有内容的递进性和时间的共时性的发展,宪政的国际法成为国际法三分结构的最新分支③。
在国际社会结构未有根本变革的国际法体系中,共存与合作的国际法仍然是主流,但国际法的宪法化趋势及其宪政发展是前沿、前瞻和前景。
与共存的国际法、合作的国际法相比,宪政的国际法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规范的意义上,共存的国际法确认国家以独立为核心的基本权利,主要适用于国家间的法律关系;合作的国际法确认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人格,主要适用于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之间的法律关系;宪政的国际法确认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适用于国家、国际组织与个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其所构成国际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第二,在功能的意义上,共存与合作的国际法,都以作为公权力的国家主权权力在国际层面的确立、约束和让渡为基础,是一种一元法律关系;宪政的国际法还涉及国家主权权力和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国际层面的二元法律关系。主权权力在国际层面的运行既需要宪政的构成,也需要限制,而个人的基本权利对公权力的抵抗功能同样在国际层面得到彰显。
第三,在价值的意义上,共存的国际法关注国家的价值,合作的国际法关注国家和国家之国际社会的价值,而宪政的国际法除了国家和国家之国际社会的价值外,还关注个人的价值和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其中,仅从“法益”的角度看,个人的价值是国际共同体的国际法中的初始和最终价值:国家、国际组织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所需要考虑的公共利益,对个人的权利加以外在而不是内在的制约。
就国际法的历史发展而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和约是近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起点,以其为基础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16世纪分别由马基雅维里和布丹所首次提出的“国家”和“主权”话语,为源于欧洲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践行。主权特别是内部主权强调领土内所有成员服从于一种中央权威,结束了中世纪社会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彰显了国家本身的价值。但是,延绵至今的威斯特伐利体系并没有解决国际法在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的主流逻辑是不关注国家、主权及其国际法的正当性,而以主权论证国际法体系的合法性,并反之以国际法论证国家及其主权的有效性。
从宪法学看,宪法学所建构的合法性理论,以人民主权和个人的基本权利为起点,以制宪权表明制定宪法的合法性。宪法合法性是指宪法秩序在规范或者道德上的可接受性,一方面,规范性的合法性以宪法内容为基础,即对宪法内容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也以宪法如何制定的程序为基础,即对制宪程序的可接受性[20]423-463。宪法学以制宪权(pouvoir-constituent)原理对宪法合法性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宪法由制宪权所创建,其合法性来源于人民主权和个人的基本权利。程序上,宪政推定国家权力行使合法化的基础是得到人民的预先同意,宪法的制定必须是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宪法的诞生和生效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或确认。实体上,宪法的内容要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原理,即保障人权的实现并抵抗国家权力对人权的侵犯。
与宪法学相比,国际法只是建构了有效性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尚未解决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这种状况,源于国际法及其国际共同体与国内法及其国家共同体的诸多迥异。
第一,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的传统国际法,贯彻了有效性而不是正当性的特质,并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国际法所传承。国际法的合法性观念表现为有效性而不是也一般无须追问正当性,进而为国际法的各种规范所彰显。例如,这种合法性观念反映于国家的构成标准上,根据1933年12月《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领土和人口这两个标准实际上受制于第三个标准,即“有效的政府”,强调的是政府对领土和人口的事实状态下的控制和统治,是一种统治有效性而不是正当性的表达。第四个标准“对外交往的能力”显然受制于国际共同体内其他主体的承认,而对国家或政府的承认是一种典型的单方行为[21]101。因此,传统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的构成要素,都是静态的、形式的而非实质条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对实证事实的表达,而不是对正当性的一种追求和体现。
第二,在缺乏能够全面代表国际共同体并具有最高权威的中央机构的情况下,作为个体行为者的国家不仅是国际法实施和适用的主体,更是国际法的“造法”主体。国家的各种行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对国际法的创制产生影响。由于国际法依赖于国家自身,因而对一种违反“先前”国际法的行为的接受,或者相当于催生了新的国际法规范,或者是改变了其适用的效果,无异于使违法根据产生的结果成为合法。例如,在所谓正义战争论和战争权被认为是合法的时代,19世纪的国际法学者霍尔就认为,没有可以推翻国家某种行为的“共同体”力量,对于国家(一般是强权国家)所形成的大多数国际情势和事实,国际法体系只有接受,或者虽然主张其不合法然而迫于现实而逐渐接受。
第三,国际法的逻辑起点建构在国家主权而不是人民主权之上。法国学者西耶士认为,本质上人民主权存在于国民的制宪权中,制宪权与人民主权如同一体的两个面向心[22]85-86。制宪权理论与人民主权学说一脉相承,是人民主权学说在价值形态上的合理延伸,其价值功能在于推动间接民主的实现和保证各种法律规范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基础[23]560。制度化、实证化的国家权力由宪法直接确认,使自然法意义的人民主权转化为国家主权。而现代国际法所强调的国家主权在理论渊源上深受19世纪德国的国家法人说影响,该说认为主权归于国家本身,身为主权主体的国家自身就是“最高的法秩序”。尽管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说与宪法的国民制宪权说并非直接抵触,人民主权说直接反对的是君主主权而不是国家主权;但是,国际法学认为国家就是国际法的“制宪权”本身,而主权同时是国家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实证意义的国家主权显然不足以解答正当性意义上的国际法合法性问题。
第四,宪法学以制宪权理论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实质划界,而国际法仅在领土与有效控制方面实现了形式划界。在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力中心的结构形成之后,必将直接影响国家权力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宪法成为设置不同群体的政治优势或障碍得以实现权力制衡的充分表达。国际法学认为国家主权具有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两个面向,其中内部主权解释了国际法在国家法律秩序中的效力依赖于国家的同意。因此,在传统国际法关于其效力根据的学说和实践中,国家的同意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传统国际法被认为在更大程度上与私法而不是公法相似,即一种平等主体之间自治的法。
第五,国家的基本权利不具有与个人基本权利相似的“先宪法性质”。在宪法学上,国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先于国家而存在,为宪法所确认和保障而不仅仅是宪法所规定的。在宪法不够完善的国家,某些不可剥夺、不可减损的基本权利仍然具有不成文宪法的意义,要求国家予以遵从。其不可反驳的规范性前提在于保护人性尊严这一宪政价值的核心[24]36。在此意义上说,基本权利既是宪法价值体系的核心,其实现程度也成为合法性的检验标准。而国际法上的国家基本权利,传统上主要指独立权、平等权、管辖权和自卫权等,与人性尊严这一宪法核心价值并无直接关系。正如德国公法学者施密特指出:国家本身没有真正意义的“基本权利”,国家只能作为一种制度而受到宪法律的保护[25]。在传统国际法中,国家主权不能被视为是一种用以朝向国际共同体“共同之善”的权力,而是一种为国家自身利益而行使的主观权利[26]217-384。但国家本身不是目的,是为其作为人的国民服务的,国家没有个人人权天赋的那种特质。实际上,有学者将国家的基本权利作为国际法效力的根据,也因缺乏坚实的法理基础而未获得普遍认可。
从实践看,自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是共存的国际法为国际法主流的时代。这一时期所签订的条约,主要是主权统治者之间签订的双边条约,其内容多为在发生战争时获得相互之间的援助,或者旨在通过建立新边界或确定以前的边界来恢复秩序和调节边界纠纷。而且,这些条约通常没有创设国际行为的一般规则,本质是促使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存而不是制约主权的自由裁量。因此,传统国际法在本质上是双边的,不能被认为超出了其主体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总之,国际法由于缺乏与制宪权理论相称的法理,无法完全论证在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在理论上无法充分解释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在实践中经常屈从于事实状态下的国家权力。
传统国际法并不能提供足够的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依据,而这正是近年来全球宪政以及国际法宪政命题的一种主要针对问题。随着现代国际法的宪法化发展,这种正当性的缺失正在得到弥补。
国际法的宪法化和全球宪政是两个密切相关而有所区别的概念[27]931。前者描述一种过程,后者相当于一种精神态度或一套完整的体系[28]12-16。宪法化是对既定法律秩序中宪法的出现之简称,意味着一套规范发展为宪法,或者一个实体制定了宪法。宪法化概念意味着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揭示宪法或宪法性法律可以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生成和成长,也意味着法律文本在一种积极的反馈过程中获得或者最终丧失了宪法特性。因此,最简单地说,国际法的宪法化即出现、创制和确认国际法秩序中的宪法要素的持续过程[29]397-411。另外,宪政要求宪法是良宪,是具有正当性的宪法。宪政所包含的价值,是宪法实质和制度规定的基础。不同宪法的具体规定可能很不相同,但可能其体现的宪政价值是相通的[30]3。在此基础上,宪法化所指向的宪法应当是宪政宪法或正当宪法。
尝试将宪法规则适用于国际领域是宪法主权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间占主导地位的象征,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一定的复兴[31]。在日本学者筱田英朗看来,宪政或立宪主义是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绝对国家主权和世界政府之间倾向“折中”的政治表达。国内宪政的要旨是约束国内社会中公权力的宪法规则的主权权威。同理,所谓全球宪政也可通过约束国际社会中的公权力的国际规则的相同主权权威而获得实现。既不存在国际宪法也不存在国际立法机构的事实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宪政思想模式毫无关系,宪政或立宪主义的政治含义是指对基本法律统治的信仰。所以,筱田英朗用“宪法的”一词表示一种“全球宪政”的理论倾向:制定一套效力高于主权原则的基本规则。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法从本质上从一种“弃权性质的守则”,正在向“积极的合作性质的规则”发展。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旨在提供国际共同体的“公秩序”,从而更新了主要建立在双边承诺基础上的“私秩序”,并通过大量的多边条约为作为整体的国际共同体提供了依托。国际法不再限于消极的弃权守则,而且包括要求国家以特定形式对“国家之社会”采取行动的积极义务。除了管制“边界本身的问题”外,许多国际体制的国际法现在也试图解决“跨边界问题”和“边界背后的问题”[32]7。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利益催生了国际共同体的概念构成,进一步使国际法向具有价值判断的“宪政性质的规则”发展。正如国际法院审理“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法官Bedjaoui认为:国际法在20世纪初尚为明显的实证主义、自愿主义和对国家同意的强调,但现在逐渐实现了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变。国际法应是一个更加客观的概念,应更加反映集体良知和所组织共同体内国家的社会必要性。国际法的新发展是国际法从共存向合作的逐渐转变以及“国际共同体”概念的出现,这类发展使诸如强行法义务、普遍义务或者人类共同继承遗产之类的概念不断确立[33]226;270-271。在笔者看来,Bedjaoui所谓国际共同体概念的出现,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而尚未指明国际法的更新发展是出现了宪政的曙光。
国际共同体可以说是一种“作为法律共同体的国际社会”,由所有国际法的参加者构成,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人民和少数者、交战团体、个人等[34]472-481。国际共同体强调以共有价值为基础旨在保护人类集体利益的规则、程序和机制的总体,国家应当是国际共同体而不是国家自身的代言人,“甚至在没有或违背了个体国家的意愿的情况下,国际共同体对某些基本价值提供了保护”[35]289-438。所有这类价值,都源于国家不过是工具,
其固有的功能是服务于本国公民的法律所明确规定为人权的利益。纽黑文学派代表学者赖斯曼甚至主张,根据现代国际法,人民主权已经取代了国家主权,国际法事关国民而不仅仅是国家的[36]642-645。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原则,并非仅仅是对主权的限制,而是主权平等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37]837-851。主权平等是由国际共同体的宪法来界定和保障的国家的法律权威和自治,国家的自治是国家自决的空间,而国家在国际共同体中的身份平等。这种外部主权确定了共存与合作国际法的总体结构和本质内容。宪政的国际法则对传统主权施加另外两种限制,分别是任何国家都有义务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相随的国际共同体及其所有成员的共同法律利益[38]132。在宪政的国际法的主权观念中,现代国际法不仅应保障国家主权平等、保障宪法自治权、对国际共同体的参与权、联合国中的主权平等,也应增加包括全人类和个人在内的“国际共同体导向的主权平等”。
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尽管对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影响,但也促进了像人权、法治和民主这样的越来越受到国际保护的宪政价值。这一进程的效果正日益反映在价值观和政策领域中,文化和社会特殊性或多样性并不限制对人权的保护或对民主制度的加入。宪政的国际法和国际法的宪政,使以有效性为特质的现代国际法增加了正当性的价值判断,逐渐转化为对国际法合法性的法律话语和现实诉求,终将影响到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变迁。
笔者认为,全球宪政反映于国际法的面向,主旨在于借鉴国家宪政在制度设计和政治设想上的成就,以人权保障、国际法治和民主治理等宪法原则组织国际法体系的规范等级,形成国际共同体的基本法律秩序,指引主权权力在国际和跨国层面的运行,实现对国际共同体中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保障和协调,旨在促进国际法秩序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与宪政所包含的人权、法治和民主相应,当代国际法的宪政转向,在实践中表现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人本化、法治化和民主化:
第一,国际法的人本化主要是指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更加重视对个人权利和利益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确立、保障和施行,国际法的理念和价值中逐渐增多了以个人为导向的发展[39]89-103。
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蓬勃发展,不少规范已经成为国际法中具有宪法至上性的国际强行法,并进而波及其他国际法的领域。不仅在外交保护、引渡、庇护和难民这样直接与个人相关的国际法制度中更加关注对个人权益的保障,国际法的人本化对国家主权豁免、外交法、国际刑法乃至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等也产生重要影响。
笔者认为,国际法人本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尊重人性尊严。与国家宪法相似,人性尊严同样是国际法宪政的“基本规范(Grundnorm)”。在宪政的国际法中同样存在“权利宪法”,是指以人之尊严作为基本规范,以基本权利的国际化所形成的国际人权规范作为价值体系和价值基础,确认并保障与国家和国际组织相关的个人的基本权利,使国际法的宪法秩序得以确立公权力行使的界限。
第二,国际法的法治化意味着在当前无政府、但是有秩序的转型世界中追求和建设法治。国际法治要求在不同的层面实现“良法”和“善治”,即内容与目标设定良好、形式完善的规范在国际事务中被普遍地崇尚与遵行[40]63-64。
实践中,国际法各领域的法治发展是不均衡的,有些尚处于萌芽,有些处于合法化过程,有些则已经达致宪法化阶段。在国际层面,法治原则并非如同国家那样明显,但是国际法治的第一要素即法律对政治的优先性和法律确定性原则是存在的。
国际法治致力于国际关系的合法化。国际关系的合法化即国际关系逐渐由规则和程序而不仅仅是权力和利益所调整。合法化具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双重意义,描述性意义上是指合法化的实际过程,例如更加依赖于条约这类硬法、更精确的规则和争端解决的法律模式。规范性意义上的合法化则是指应加强国际关系的法治,以法治的原则和方式管制国际秩序[41]15。
国际关系合法化的目标是国际法治,而国际法治根本上应奉行国际宪法之治。据认为,法治的基本要素载于《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规定,为了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法治”一词应理解为指宪法法治,从而使政府机构的权力与限制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均在一部法典中给予承认并加以规定,该法典高于从属立法,并需要根据人民的主权意志予以批准或修改④。
第三,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民主化是指国际法的制定和实施程序日益民主,国际法的内容及其实施结果体现民主价值,国际法逐渐确认民主权利和出现了增进和保障民主的国际法制度。
宪法化是一种深层次的民主化过程。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国际法的民主化进程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际人权法律制度和机构,但“民主的国际法”和国际法的民主化内容显现出相对独立的面向和趋势。这一进程正促成建立在保护民主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原则规则和体制机制基础之上的国际民主制度,其中包括在联合国实践中增进民主和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有些区域性国际组织例如美洲国家组织采取集体行动保护民主的“集体民主体制”。就参与国际共同体的各种成员而言,所谓纵向民主即公民的民主参与,例如国家议会代表和跨国公民社会参与国际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作为对行政机构在国际层面运行的监督。所谓横向民主即国家在政府间决策中的参与,是指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国际法制定和实施的权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与。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法已经出现了与国家相平行的宪政实践和理论发展,全球宪政通过宪政的国际法实现治理,而不是或不仅仅是依赖权力。全球宪政实际上纠正了国内宪法体系因全球化而日益增长的缺陷,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合法化的契机。国际法的宪政,是逐渐有差别的和有等级的国际法的简称,是政治统一体的象征,旨在加强国家之间的法律联系,并建构国际共同体的组织结构[42]853-909。宪政的国际法,关注国际共同体中的个人价值,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国际层面受到国际宪法体系和宪政价值的限制,个人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的保障得到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全球宪法化的过程是有条件的并存在路径依赖,共存的国际法和合作的国际法仍然在宪法化的世界里存在。而且,当代国际关系中存在诸多反宪法化的趋势。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当下关注,全球宪政的规范、原则和目标价值如何能够取得认同和达成,法律统一性和普遍性的目标如何与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之间相协调。
注释:
①宪政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宪政与一系列实质性价值相关联,诸如民主、负责任性、平等、分权、法治以及基本权利,在集体行动和保护的框架内的个人自由和福利;程序上,则作为实践理性的行使,这类价值通过制度加以明确、解释和平衡,并因此通过商议和决策的形式诸如宪法契约和公民投票之类,以满足所涉及的合法性需要。
②共同之善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在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各有其义,一般地说是指对一既定共同体绝大多数成员所共享和有利的“善”。在自然法理论的传统中,保护和促进共同的善对于法的权威性来说是充分而又必要的条件。对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来说,共同之善要求容纳个人在社会中的基本权利,使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负责任的行为而自由选择其生活,实现公民美德和遵守道德法则。
③与弗雷德曼和易显河等学者的措辞使用相似,共存、合作与宪政的英文单词都以“co”开头。
④参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促进和巩固民主的进一步措施》的第2002/46号决议。
【参考文献】
[1]See Jeffrey L. Dunoff and Joel P. Trachtman. Ruling the World?: Co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Governance[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Mattias Kumm.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A Constitutionalist Framework of Analysis[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15.
[3]Anne Peters.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Revisited[J].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2005, 11.
[4]Amichai Cohen. Bureaucratic Internalization: Domestic Governmental Agencies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J].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5, 30.
[5]J. Tully. The Unfreedom of the Moderns in Comparison to Their Ideal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J].Modern Law Review, 2002, 65.
[6]Bardo Fassbender. UN Security Council Reform and the Right to Veto[J].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
[7]Christian Tomuschat. Obligations Arising for States Without or Against Their Will[J].Recueil des cours, 1993, 241.
[8]B. Simma.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Law[J].Recueil des Cours, 1994, 250.
[9]Erika de Wet. The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 Order[J].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006, 55.
[10]Armin yon Bogdandy, Philipp Dann and Matthias Goldmann, Developing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owards a Legal Framework for Global Governance Activities[J].German Law Journal, 2009, 9.
[11]A. Watts,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J].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3, 36.
[12](德)克里斯蒂安·图姆夏特.国际法中的立宪主义:评德国的一个建议[J], 柳磊,译.国际经济法学刊,2008, 15(2).
[13]Anne Peters. The Constitutionalist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s and Cons[J].NCCR Trade Working Paper, 2006, 1.
[14]Anne Peters. The Merits of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J].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Summer, 2009, 16.
[15]Wolfgang Friedman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J].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16]Stanley Hoffman.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17]Christian Tomuschat. International Law as the Constitution of Mankind[M]//International Law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ew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ssion, U. N., 1997.
[18]易显河.向共进国际法迈步[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7(1).
[19]古祖雪.国际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20]Philipp Dann, Zaid Al-Ali. The Internationalized Pouvoir Constituant: Constitution-Making under External Influence in Iraq, Sudan and East Timor,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 Law[J].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 2006.
[21]James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J].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2006.
[22]许志雄.制宪权的法理.许志雄.宪法之基础理论[M].台北:台北稻禾出版社,1992.
[23]莫纪宏.实践中的宪法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4]Finn J. E.. Constitutions in Crisi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ule of Law[J].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M].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6]Bruno Simma.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Law[J].Recueil des Cours, 1994, 250.
[27]Mattias Kumm.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A Constitutionalist Framework of Analysis[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15.
[28]Philip Allot. The Emerging Universal Legal System[J].International Law Forum, 2001, 3.
[29]Anne Peters. The Merits of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J].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2009, 16.
[30]J. H. Weiler, M. Wind, Introduction, in Idem(eds). European Constitutionalism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J].Cambridge UP, 2003.
[31](日)筱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M].戚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2]Christoph Humrich, Bernhard Zangl.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Legislation, Prsentation im Panel Fragmentierung und Konstitutionalisierung in Recht und Politik jenseits des Nationalstaats[J].DVPW-Kongress Kid, Dienstag, 2009.
[33]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CJ Reports, 1996.
[34]Detlev F. Vagts.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New American Ways of Law Reading[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3, 4.
[35]Christian Tomuschat, International Law. 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Mankind on the Eve of a New Century[J].Recueil des Cours, 1999.
[36]W. M. Reisman. Coerc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Construing Charter Article 2(4)[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4.
[37]Bardo Fassbender. "The Meaning of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M]. in Ronald St. John Macdonald and Douglas M. Johnston(eds), Towards World Constitutionalism: Issues in the Legal Ordering of the World Community, 2005,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
[38]Bardo Fassbender. Sovereignty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M].in: Nell Walker(ed.), Sovereignty in Transition, Oxford, 2003.
[39]曾令良.论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07, (1).
[40]何志鹏.国际法治:一个概念的界定[J].政法论坛,2009, (4).
[41]Jeremy Waldron. The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J].Harvard Jouranl. Law & Public Policy, 2006, 30.
[42]Macdonald, Ronald St. J..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Legal Community", in Ronald St. John Macdonald and Douglas M. Johnston(eds), Towards World Constitutionalism: Issues in the Legal Ordering of the World Community, 2005,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陈喜峰,男,湖北麻城人,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法学研究。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