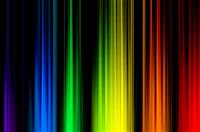
【摘要】宪政和民主是现代政治体制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如果说民主是河,宪政则是提。为了限制民主的冲动性与盲目性,美国人制定了成文宪法,在代表制基础上实现了宪政民主。与国会、总统一样,美国最高法院也是民意代表,只不过更为间接和持久。通过解释宪法,美国最高法院不断修补宪政之提,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引导民意,将宪政民主转向民主宪政,维护了自身的地位与权威。
当今世界上,真正的民主国家,都具有宪政基础,没有宪政的民主,只存在于古代雅典小国寡民式的城邦时代;所有的宪政国家,都以民主的方式治理,缺乏民主的宪政,只能是军政、训政乃至专政。
民主要求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充分尊重人民意见,完全执行人民意志。在古典城邦时代,公民通过辩论、投票、抽签表达自己的意愿。在现代世界,人民通过代表表达意愿,通过各种各样的代表机构,将古典的直接民主,转换成现代的代表制民主。这些代表机构,包括选举产生的议会、总统、总理、首相,也包括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法院。
为了划分这些代表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更好地体现民意,履行代表职责,很多民主国家都制定了成文宪法。其中,美国的《1787年宪法》是比较典型的一部。该宪法前三部分分别交代了国会、总统、联邦法院的权责,是一部典型的分权宪法。
分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为了建立更完善的联盟。因此,美国宪法的分权也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种形式。这种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定安排,就是宪政制度。
一、宪政民主
宪政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出发点是个人权利,正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宪法才要求限制与划分政府权力。在历史上,规定政府权力的文件很早就有了,比如亚里士多德记载的《雅典政制》,英国的《大宪章》,这些都是可以称得上是宪法性文件。但这还算不上是建立了宪政制度,因为《雅典政制》讲述的是平民与僭主斗争的经过与结果,《大宪章》则是国王与贵族妥协的产物,均非源自个人权利。
在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为了保障个人权利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是美国《1787年宪法》。这部宪法在两个方面开创了近代政治制度的新纪元。其一,它以成文宪法作为政府基础,宪法不是政府的产物,而是人民构建政府的产物,宪法先于政府。其二,它以代表制的形式,将古典民主转换成为现代民主,也就是代表制民主。
代表制民主融合了古老的民主理念与贵族时代选代表议事的传统,所不同的是,选出的代表不再是贵族、主教,而是普通民众。这种建立在民众基础之上,用宪法加以保障的代表制民主,就是宪政民主。
从本质上讲,民主要求及时而不受限制地表达民众的意愿,具有现时性与直接性,雅典城邦民主就是原型。而宪政则事先设定了民众决策的界限与程序,具有先定性与约束性。“从这个角度看,宪政实质上是反民主的。宪法的基本功能是将某些决定从民主过程中清除出去。”{1}
由此可见,所谓的现代民主,或者说代表制民主,其实早已背离了古典民主的本义。现代民主之所以会背离,或者说改造古典民主,有两大原因。其一,使民主制度可以大范围地运作起来。古典的直接民主,只适合于小国寡民式的城邦,面对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现代国家,代表制的间接民主,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治理模式。其二,改变民主制度的负面形象。在世界历史上,民主制度往往和暴民、混乱相连,古典时期的多数政治思想家都认为,民主制度无法长久,比较稳固的是混合政体。进入中世纪,“民主”一词更是被人彻底遗忘。近代早期英国的政治斗争,也只是以自由、权利相号召,视民主为洪水猛兽。到了北美殖民地独立建国时,“民主”一词才在制宪前后的政治辩论中多次出现。为了证明自己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制宪者对民主作了限定,以说明新生的美国不会滑向暴民统治。
为了防止暴民政治,美国人创造了成文宪法,以书面条文的形式,约束民主的范围与程序,将古典民主改造为现代的宪政民主。
美国《1787年宪法》,是一部授权宪法,政府不得行使没有明确列举的权力。两年后的《权利法案》更是再次强调,联邦政府不得干涉个人的某些基本权利与自由。这些都严格限制了民主的范围。
除了范围外,美国宪法还通过代表制度,规定了民主的程序。从理论上讲,国会、总统、最高法院,都是民主的代表机构。所不同的是,众议员是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和总统是间接选举的,{2}最高法院大法官则是由间接选举出来的参议员、总统商量任命的。可见,众议院的民主性最强、参议院和总统次之,最高法院最差。
虽然最高法院的民主性最差,但其宪政色彩最为浓厚。根据宪法,最高法院拥有独立的司法权,是联邦法律问题的终审法院。宪法制定后,通过联邦党人的辩护和解释,最高法院获得了完全的司法审查权,有权就宪法问题作出最终解释,可以宣布国会和各州的法律违宪无效。凭借这一点,美国最高法院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法院。
二、民主宪政
由于最高法院具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又缺乏直接的民主基础,很多民选政治领袖对此颇为不满。19世纪初期的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就曾公开批评约翰·马歇尔和他所领导的最髙法院,认为总统、国会与最高法院一样,都拥有宪法解释权,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并不高于总统或国会对宪法的理解。{3}1832年,在否决国会延长合众国银行法时,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更是公开质疑司法审查理论。“国会、执法部门和最高法院都必须按自己对宪法的理解来行使各自的职责。在宣誓效忠宪法时,所有联邦官员效忠的是他所理解的宪法,而不是其他人所理解的宪法。……对于国会来说,最高法院[对宪法]的意见并不比国会自己的意见具有更高的权威,反过来也是如此;在这一点[理解宪法]上,总统独立于国会和最高法院。”{4}
进入20世纪后,由于最高法院既保守,又能动,阻碍了“新政”变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甚至准备增加大法官数量,改组最高法院。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沃伦法院的司法能动,更是引发了尼克松和里根等共和党总统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竞选或就职演说中曾明确表示,要通过任命大法官途径,改造最高法院。
沃伦法院浓厚的自由主义司法判决,为美国带来了一场权利革命,也引起了学界对司法审查与民主关系的激烈争论。曾在最高法院担任过大法官助理的耶鲁法学教授亚历山大·比克尔就提出,最髙法院缺乏民主性,其司法审查行为违背了多数选民的意愿,造成了“反多数困境(难题)”.
为了缓解这一困境,美国学者从维护基本价值(权利)、捍卫民主程序等层面,为司法审查辩护,证明司法审查并非完全反民主。比如杰西·绍伯就主张,司法审查应在维护个人权利与美国基本价值上发挥作用,才不容易遭到立法机构的抵制,也就是说司法审查尽量不要涉及民主立法。但是,另一位著名学者约翰·哈特·伊利不同意绍伯的看法,他在《民主与不信任》一书中,质疑最高法院识别基本价值的能力:如果对全体美国人而言,这些价值真的是“基本”的,那么,代表多数人意志的立法机构为什么就一点都没有感受到这些基本价值的制约呢?他表示,美国宪法首先关心的是“程序与结构”,而不是“对具体实体价值的识别与保护”,因此,司法审查应该关注立法的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价值,这样才能保持司法审查与民主的一致性。{5}
沃伦法院之后,最高法院逐渐趋向保守,但仍然能动,通过司法审查否决国会立法的次数有增无减:沃伦法院时期(16年)23次,伯格法院(17年)达到32次,伦奎斯特法院(19年)则增至40余次。{6}否决州立法的次数就更多了。
如此保守且能动,使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依旧紧张,学者们的批评也愈加激烈。左派学者指责最高法院过于保守,右派学者则抱怨最高法院不够尊重各州立法机构。总之,最高法院干涉民主立法,就是越庖代俎,缺乏正当性。为了证明最高法院的正当性,有学者提出,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最高法院最好就事论事,不解释宪法原则;也有学者主张,回归两百多年前的“民意”,根据制宪者的“原意”解释宪法。这两种意见,看似可以使最高法院少受批评,其实极难施行。作为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怎能不解释宪法呢?如何能够不顾宪法,只审事实呢?就事论事固然可以免除一时烦恼,但缺乏明确的宪法解释,只会引来更多的诉讼,造成宪法理解上的混乱。至于回归“原意”,姑且不说很难探清制宪者与批准者的本意,就算真的存在一致认可的“原意”,以两百年前的“民意”制约今天的民众,难道就具有民主性了么?岂不也违背了民主的现时性与直接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批评司法审查的基本出发点,是最高法院不能像国会、总统一样,代表多数民意,缺乏民主性。果真如此吗?国会、总统就一定总能体现多数选民意愿吗?也不尽然,就总统选举而言,普选票的多寡并不直接决定总统职位归属,以州为单位的选举人票才起决定性作用。由于赢者通吃,在美国历史上,赢得普选票输掉大选的事并不鲜见,很难说这样选出的“少数票”总统能代表多数选民的意志。至于国会就更谈不上真正的多数了,参议员与众议院都是各州选举的,代表的是地方利益,根本不用考虑其他州和地区选民的意愿。而且,无论各州大小、人口多少,参议员都是每州两名,选民基数相差数十倍,如果小州的参议员联合起来通过某项立法,这样的法律很难说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
当然,总统与国会是民选机构,它们比最高法院更能直接感受和代表民意,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难道非民选的最高法院就能脱离民意吗?事实并非如此,在2005年的一项盖洛普民调中,相信或很相信国会的占到了受访者的22%,相信或很相信最高法院却超过40%,这说明最高法院的判决深得人心,与民意息息相通。有学者因此认为,最高法院与总统、国会一样,也是民主机构,它们的行为都具有同样的民意基础,都同样尊重选民的意愿。{7}
按照这种理解,如果说总统、国会是宪政制约下的民主机构,最高法院则是尊重民主的宪政组织;美国的三权分立是民主与宪政的相互补充与融合;宪政民主与民主宪政,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最高法院的民主性虽然不如总统与国会,但其突出的宪政功能,却能防止民主的短期性与盲目性,保障美国的民主体制不会偏离航向。
如果说民主是一条汪洋恣意的大河,既可以肥沃土地、灌溉庄稼,也会冲毁房屋、淹没家园,那么,宪政则是这条河的堤岸,可以规训民主这条大河,发挥其灌溉作用,防止其泛滥。
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中,负责维护宪政岸堤的主要是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正因为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成为最有权势的法院,才能够抵挡汹涌的民主波涛,确保民主这条大河平稳流淌。没有宪政之堤的阻挡,民主之河就会泛滥成灾;相反,如果民主之河干涸,宪政之堤也就毫无意义。这是民主与宪政相互依存的一面。
民主与宪政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正如河水会不断冲刷提岸,希望自由奔流,民主也会持续冲击宪政,期望不受任何内容与程序限制的民意。为了坚固宪政之堤,抵挡民主之河日积月累的冲刷,美国人制定了成文宪法,规划了民主之河的大致流向。
水往低处流,民主也是一个向下看齐、力求满足大多数人最大愿望的进程;宪政之堤只能沿河而筑,
如果强行改变民主之河的流向,或是人为引河上山,无异于忽视民意,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之上,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堤毁岸消,河水肆虐,民众遭殃。
因此,宪政之堤也要适应民主之河的流向,美国最高法院以各种路径解释宪法,就是在修补宪政之堤,适应民主之河。当然,民主之河有时候也会改道,比如美国内战,宪政之堤也要随之改建,比如内战后的三条(第十四、十五、十六条)重建宪法修正案。
美国这条民主之河,之所以能够奔流两百余年,除了一次改道外,很少泛滥,根本原因就在于最高法院能够不时修补宪政之堤,在顺应潮流的基础上,遏制过于汹涌的浪涛。
修补宪政之堤,首先必须尊重民主之河的流向。美国最高法院解释宪法,也往往能契合长期民意。这其中,有制度上的根源。众所周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职,除非行为不端,可以老死任上。大法官并非民选,而是由民选代表(总统、参议员)推选任命,虽然民主性不足,但也称得上是民众的间接代表。所以,当其行为不端、不能胜任职务时,民选代表(议员)可以启动弹劾程序,使其去职,然后加以审判。其次,大法官的数量和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范围,都掌握在民选代表手中,他们可以增减大法官人数,收缩限制最高法院的管辖范围,从政治上控制最高法院。最后,民众与民选代表还可以增修宪法,从法律上推翻背离民意的判决,比如内战后的重建宪法修正案就明确推翻了臭名昭著的“斯科特案”判决。
但是,最高法院毕竟只是民众的间接代表,无论是弹劾程序、政治途径还是法律手段,民众或民意对最高法院的影响,都是间接的、非常规的。因此,最高法院在拥有巨大权势的同时,还享有极高的独立性,不但可以进行司法审查,甚至具有司法主权(judicial sovereignty)。
这样的主权与独立性,使最高法院可以不受短期冲动性民意的冲击和动摇,专注于维护个人基本权利和民主的核心价值,这也是美国式自由与民主得以长期存续的一个重要保障。
对于个人基本权利,《权利法案》有明确列举,但最初只针对联邦政府,州政府并无义务遵循。但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通过最高法院的不断解释,表达自由、宗教自由、排除非法证据、获得律师帮助等权利,都逐渐全国化,同时可以约束各州政府。《权利法案》的全国化,彻底阻挡了民选机构(包括州议会)侵犯个人基本权利,这是最高法院深孚民意的最坚实根基。
在民主核心价值方面,美国宪法也顺应民意,步步推进,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在内战后将公民权扩大到所有黑人;20世纪初,参议员改为直接选举(第十七修正案),妇女获得选举权(第十九条修正案);取消选举权的税收要求(第二十四条修正案)。而最高法院则依据宪法与修正案的精神,将选举权落到实处,尽量保障一人一票,每票平等。沃伦法院时期的重划选区案就是例证。在维护民主的核心价值和程序上,最高法院勇闯“政治棘丛”,赢得了选民的尊重,也突破民主自身的局限性,为美国民主提供了外在的修复功能,保证了美国民主制度的长期性与稳定性。
四、民主与“明主”
不管美国最高法院到底是不是民主机构,能否代表或反映民意,有一点不可否认,它在争取充当美国人的“明主”,尽量理解和尊重民意。而且,与国会政治的多元化与地区化相比,最高法院似乎更能体会全体民众的普遍意愿,更能代表美国政治中坚群体的看法。
正如美国学者杰弗里·罗森(Jeffrey Rosen)所言,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一系列问题上,最高法院中温和的多数,都比国会中两极化的政党领袖,更准确地代表了多数美国人的看法。法官实际上比影响乃至控制国会政治的利益团体更准确地体现出全国多数民众的宪法态度。{8}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的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开始,政治学家就认为,最高法院在历史上一直是倾向于跟随,而不是挑战全国民意。达尔在1957年写道,最高法院并没有保护少数群体不受多数暴政压迫,“主导法院的政策观,从没有长久背离主导美国立法多数的政策观”.{9}杰出的政治学家罗伯特·麦克洛斯基(Robert McCloskey)也承认,尽管法院的判决会轻轻地将这个国家拐向某个方向,或是温和地踩一下朝另一个方向的刹车,法院总会留意来自总统与国会的持续的政治抨击,并最终受制于民意。麦克洛斯基写道,“公众的赞同为司法决策设置了一个外部的边界;……最高法院也很少长时间地抵制并无错误的公众情绪”.{10}
在麦克洛斯基看来,美国宪法是“人民主权”与“基本法”思想的二元对立统一,前者意味着多数统治,后者则强调基本法的限制。这两种思想共同融入美国宪法,使“美国人的政治心灵分成了民众意志和法律主治”.反映在政体设计上,则是立法机关负责提出计划、制定政策,回应选票表达出来的公共利益,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法院则“几乎是预先就注定为基本法的守护神”,体现着美国的法治精神。{11}不过,法院解释宪法不能仅仅注意法律的逻辑,更要注意民众的容忍度。法院必须在尊重民意与维护法治之间寻求平衡。
最高法院之所以尊重民意,充当“明主”,也是为了长久地维持自身的有效性与正当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最高法院才能充分维持自身的有效性与正当性呢?罗森认为,在美国历史上,当法官的行为符合所谓的民主宪政论(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时,换句话说,当他们遵从全体国民的宪政观时,他们就在实际上维护了自己的民主正当性。反之,当法院奉行司法单边论(judicial unilateralism)时,其判决最容易受到抨击,并长期遭到抵制。所谓的司法单边论,指的是,法院判决联邦或州法律违宪时所依据的宪法原则,受到美国多数民众的积极与强烈抗议。{12}罗森因此大胆地提出,当最高法院奉行民主宪政论时,最高法院就成为了美国最民主的部门。
罗森将一向被认为缺乏民主性的最高法院称为最民主的部门,虽然有些标新立异,但却不无道理。在国会利益集团化、总统两极政党化的美国民主制中,只有最高法院超然独立,似乎可以成为“明主”,捍卫美国民众的基本权利,维护民主的核心价值。罗森所谓的最民主的部门,不就是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的“明主”吗?
由此可见,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倒像是民主与“明主”的结合。当然,只有遵循民主宪政论,最高法院(以及大法官)才堪称“明主”,才能成为最有权势的法院。
【作者简介】
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
【注释】
[1]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载埃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理性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4页。
[2]1913年4月批准的宪法第十七修正案将参议员的间接选举修改为直接选举。
[3]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4]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5]约翰·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朱中一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第102页。
[6]Thomas M. Keck, The Most Activist Supreme Court In History: The Road to Modern Judicial Conservat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pp.40-41.
[7]Jeffrey Rosen, The Most Democratic Branch: How the Courts Serve America,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4.本书中译本已经纳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美国法律文库”,即将出版。
[8]Jeffrey Rosen, The Most Democratic Branch: How the Courts Serve America, pp.3-5.
[9]Jeffrey Rosen,The Most Democratic Branch: How the Courts Serve America, p.6,
[10]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
[11]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2]Jeffrey Rosen, The Most Democratic Branch: How the Courts Serve America,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