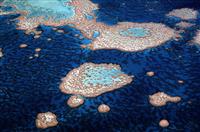
【摘要】 宪法总纲条款占据了我国宪法的近四分之一,并成为历次修宪的主要对象。宪法总纲条款的最大特征是具有纲领性,即规定了一种国家未来要实现的目标,在德国法上被称为国家目标规定。国家目标规定不同于基本权利,它高度依赖立法的中介与形成。同时,它保护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但是,国家目标规定仍然对于国家机关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立法机关来说,国家目标规定赋予其一种立法义务去规定实现国家目标的方式。对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国家目标规定主要提供了一种解释标准。国家目标规定的规范性体现为两方面,一是作为具体规范的标准和界限,二是作为立法者的行为要求。前者表现为针对立法作为的合宪性审查(即立法违反了国家目标规定),后者表现为针对立法不作为的合宪性审查(即立法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平等地履行国家目标规定所课予的立法作为义务)。
【中文关键词】 宪法总纲条款;国家目标规定;基本权利;原则;立法不作为
2018年3月11日,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了第五次修正,修正后的《宪法》共143条,其中第一章“总纲”有32条,占到全部宪法条文的22%。宪法总纲条款不仅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军事等各项基本制度,而且成为我国历次修宪的主要对象(在宪法序言和正文的四章之中,针对宪法总纲部分的修改是最多的)。[1]但是,过去宪法学对总纲条款的研究不多,主要观点认为总纲条款具有纲领性。[2]根据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的说法,纲领性就是指宪法指明了目标。周恩来在1958年谈到我国法制建设时认为,宪法的纲领性在于指出今后发展的方向。[3]栗战书指出,我国宪法同一些国外宪法相比,一大特色就是明确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奋斗目标。[4]我国台湾学者将这种纲领性条款称为“基本国策”,[5]即宪法中的政策性条款。[6]我国对基本国策的称呼,主要包括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改革开放、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7]这些基本国策绝大多数都位于宪法总纲部分。那么,如何认识宪法总纲条款的性质?宪法总纲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具有,这种效力以何种形式呈现?本文拟在借鉴德国宪法学上国家目标规定(Staatszielbestimmung)理论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探讨。
国家目标规定首见于1919年的魏玛宪法,[8]当时,它设计了一些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以社会为导向的规定,比如确保每个德国人拥有健康住房以及保障通过工作来维持生计的可能性(第155条第1款和第163条第2款)。但是在魏玛时期,这些条款被称为方针条款(Programms?tze),亦即只是一种政治宣告,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虽然魏玛宪法的传统影响了一些先于基本法制定的州宪法,但是基本法却有意避免写入魏玛宪法中的方针条款,因为制宪者认为基本法应当抵制纳粹时期的国家恣意和政治压制,所以不过分强调国家权力的宪法政策问题,而是转向国家权力的组织和界限。[9]基本法时代最早使用国家目标规定概念的是学者伊普森(Hans Peter Ipsen),他在1949年11月17日发表的有关德国基本法的演讲中将基本法第20、28条规定的社会法治国条款视为国家目标规定。[10]根据伊普森的说法,这是为了应对战后德国的社会现实而采用的一种不完全的规范和形式。[11]
1983年德国联邦内政部和司法部的“国家目标规定与立法委托”专家委员会针对国家目标规定给出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规范,它要求国家持续地关注或者履行特定的任务——即事实上已经确定的目标。[12]该定义被多数学者所接受。[13]学者佐默曼(Karl-Peter Sommermann)将国家目标规定定义为国家权力在法律上有义务追求的一种确定的目标,但公民对此并不享有主观权利(subjektive Rechte)。[14]因此,国家目标规定具有三个特征:(1)开放性,即国家目标规定需要具体化和形成,这主要是立法者的任务;(2)缺乏主观权利性。这一特性导致国家目标规定被违反后无法直接通过主观诉讼程序得到保护,由此宪法监督机构通过客观诉讼程序来审查立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3)最终性。这意味着国家目标是动态的、随着社会发展的,并引导国家的行为。在社会条件和国家目标的实现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关系,国家要选择实施方式和实施手段来最大程度地实现目标。[15]
(1)国家目标(Staatsziel)和国家目的(Staatszweck)。国家目的是高度抽象的,它是对国家存在的正当性证明,是实证法的来源,而国家目标规定是有效的法律规定。?瑏瑠国家目的是用来证立、正当化国家行为,并且为国家行为划定界限。国家及其制度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瑏瑡?国家目的是更一般的,例如安全、公共福祉,而国家目标是中间层面的,通过目标的说明将国家目的具体化,它强调的是某个方面或者是对目标实现的方式和手段的说明,[16]例如社会正义的建立是公共福祉的具体化。除了上述抽象-具体的区别之外,国家目标是宪法上规定的目标,它是直接有效的,从而区别于国家目的,后者不依赖于宪法并且先于国家和宪法存在。国家目标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以零散的、无体系的方式对国家任务的政治性列举。在此意义上,国家目标是宪法所确定的或者所采纳的国家目的。
(2)国家目标规定与国家结构性原则(Staatsstrukturprinzipien)。国家结构性原则(民主国、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共和国、联邦国)赋予国家特定的组织形式,是宪法的形式原则,而国家目标规定是决定国家行为内容的实质原则。比如实质法治国(国家的法治国属性在于保护人的尊严和促进人的自由)和形式法治国(国家行为应受到形式程序的约束,比如行政的合法性、审判独立或者法安定性),前者是国家目标,后者是国家结构原则。[17]
(3)国家目标规定与立法委托(Gesetzgebungsauftr?gen)。国家目标规定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但主要是约束立法权,[18]因为立法是贯彻国家目标的首要工具。所以国家目标规定和立法委托具有类似的结构,它们都敦促国家的积极作为。但是区别在于,立法委托只针对立法者,而国家目标规定还针对行政和司法。同时,立法委托对立法者比国家目标规定有更少的活动空间。也就是说,对于立法委托,立法者在是否立法上是没有活动空间的,而国家目标规定只是要求立法者注意或者最终履行它们的任务,至于是否立法以及如何立法都委托给立法者决定。[19]
(4)国家目标规定与制度性保障(Einrichtungsgarantien)。制度性保障的本质特征是指禁止国家废弃或者挖空要保护的制度,[20]但是内涵的形成或修改是允许的,只有制度的核心领域受保护。[21]所以,制度性保障与国家目标规定的区别在于,制度性保障是要求国家不作为,它保护的是已经存在的制度,而国家目标规定是要求国家作为,它预先规定了要实现的目标,该目标是不作为无法实现的。[22]此外,制度性保障是维护一种既定的规范和现实状态,而国家目标规定则是指出一种变化的趋势。[23]
(5)国家目标规定和国家任务(Staatsaufgaben)。国家任务比国家目标还具体,[24]它是指具体的活动领域,比如刑事侦查、司法、技术安全、养老保险、医疗服务。[25]如同国家目标是国家目的的实现手段一样,国家任务也是国家目标的实现手段。履行国家任务也是在直接实现国家目标或国家目的。国家任务是建立在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关的行为义务基础上的,它是宪法或法律明确规定或者从中推导出来的。所以任务的概念是基于行为,目标的概念是基于期望的行为结果,目的的概念是基于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26]
谈论国家目标规定的性质首先要从国家目标规定与基本权利的区别谈起。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家目标规定是一种纯粹的客观法规范,也就是说,从其中无法得出个人的主观权利。而基本权利虽然也具有客观法效力,但它首先是一种主观权利。[27]除此之外,基本权利主要是公民针对国家的防御权,而国家目标规定保护的不是公民针对国家的自由空间,而是共同体和政治体的价值决断以及公民要求国家进行给付或者参与国家。[28]同时,基本权利是保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国家目标规定是针对未来,去寻求达到一种目前还不存在的状态或者法益。
区分基本权利和国家目标规定是宪法理论和宪法教义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早期,基本权利首先通过立法者去实现,由此它不是对所有的国家权力产生直接效力,而是通过立法来约束行政,即行政的合法性原则。所以,基本权利的效力就取决于立法机关的民主化程度。基本权利的主观化肇始于1849年的保罗教堂宪法,该法第126条允许德国公民针对侵犯他受帝国宪法保护的权利向帝国法院提起诉讼,但是该宪法没有生效。将主观权利从客观法中提取出来的是当时的国家法实证主义。格贝尔(Carl Friedrich Wilhelm von Gerber)在1852年《论公权利》一书中提出,真正的权利只能是臣民在公法上享有的、法律明确承认的、针对君主和公职人员并且具有起诉可能性的法律地位。从而自由权不再是作为消极的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即客观的、抽象的法律规定,而是主观的权利。[29]此后,主观公权利经过萨维尼、耶利内克、比勒等人的发展,成为后来主流的保护规范理论。[30]进入到魏玛共和国之后,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区分又起波折。由于魏玛宪法在经典的自由权外还加入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这使得宪法规定的规范性变得复杂化了。学者们认为,这些新权利不能取得与经典的自由权同样的规范维度,尤其是它们不能取得主观权利的内涵。进入基本法时代后,虽然基本法第1条第3款肯定了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属性,但是基本法也规定了一些国家目标规定,[31]这种规定不像基本权利能够被直接适用,而是间接作为一种要完成的立法。联邦宪法法院在1967年的判决中承认社会国是国家目标。它指出,基本法第20条第1款仅仅确定了目标,但是关于如何实现该目标,路径是开放的。[32]
由此,国家目标规定与基本权利成为一种对立的关系。[33]如果某个规定中可以推导出主观权利的内涵,就是基本权利;反之,就是国家目标规定。因为基本权利保护的是个人利益,而国家目标规定保护公共利益,对于前者,主要通过主观诉讼来救济(因为是个人利益,个人可以放弃,所以是主观的),而对于后者只能通过客观诉讼,比如违宪审查来救济。对于客观诉讼,必须由法定主体基于法定的条件而提起,个人并无诉讼权能,更遑论放弃,所以是客观的。另外,佐默曼还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区分两者。假设一个规范的内容是,任何公民都有权获得合适的住宅。另一个规范规定,国家应关心公民获得合适的住宅。此时这两个规范是否都属于国家目标规定呢?佐默曼认为,第一个规范并非主观权利,而是规定了国家的措施义务。因为这种有约束力的给付义务需要立法的具体化和程序。[34]所以是否具有直接的效力或者是否需要通过立法的中介成为区分国家目标规定和基本权利的关键。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已经出现了区分国家目标规定和基本权利的“萌芽”,比如在“陶国强、祝树标等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赔偿纠纷案”中,[35]法院认为,陶国强等四人请求确认东莞国土局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杰违反我国《宪法》27条第2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规定,但该项请求并不属我国《行政诉讼法》2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形,原审法院认为该项诉求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无不当。
经典的规范结构是事实构成和法律后果,但是这并不足以应对高度复杂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的国家任务。基于所涉利益和关系的复杂性,除了跟事实构成相关的行为规范外,还出现了跟目标相关的指导原则,比如国家目标规定。卢曼区分了两种规范:条件程式(Konditionalprogramm)和目标程式(Zweckprogramm)或最终程式(Finalprogramm)。[36]条件程式是“如果……那么”模式,即如果满足事实构成,那么就出现相应的法律后果。条件程式的适用方式是涵摄。目标程式仅仅预设了目标,而如何实现目标则留给了解释者。所以它通过最优化(Optimierung)来适用,即在一个价值序列中比较不同的观点。在此意义上,国家目标规定就是一种目标程式。它放弃了行为方式的预设,而代之以目标。
卢曼区分条件程式和目标程式最初是针对行政法,尤其是规划法,用来处理动态背景下的复杂问题以及国家对社会和环境的形成功能。[37]如果说条件程式是自由法治国下行政行为的方式,那么目标程式就是社会和生态法治国下国家行为的进路。[38]条件程式主要用于侵害行政,而目标规定用于规划行政。国家目标规定反映了以危险防御为主要方向的自由法治国向以预防风险为目的的社会和生态法治国的转变。
这种区分类似于英美法上的规则和原则之别。根据德沃金的观点,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生效,当两个规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能其中一个生效。原则并不会产生一个确定的法律后果,而是为某个决定提供理由。两个原则发生冲突,必须通过比较具体情形中的权重来解决。但是,德沃金又认为,原则和政策不同。政策规定了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一般是关于社会的某些经济、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的改善。而原则不在于将促进或者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形势,而在于它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39]但是,德沃金区分原则与政策只是内容上的,而非适用方式上的。因此他才在大多数情况下,概括地使用原则这个词汇来指代规则之外的其他准则的总体。[40]德沃金之后对原则和规则进行区分的是亚历克西(Robert Alexy),他认为原则是一种最优诫命(Optimierungsgebote),它要求在法律和现实的可能性上寻找一种最可能实现的高标准。[41]而规则是要么履行要么不履行,当规则生效的时候,它要求精确地去完成它的要求,不多也不少。因此,规则代表的是事实和法律上的确定。[42]根据亚历克西的标准,国家目标规定属于原则模式,[43]即国家动用最有效的手段去尽可能地实现目标,目标冲突和原则冲突一样要通过权衡来解决。
最先对国家目标规定的法效力进行研究的是学者朔伊纳(Ulrich Scheuner),他将国家目标规定视为宪法原则的子集,是一种以普遍或者有限的形式出现的为国家活动设定的准则和方针。它在特定的方向上通过命令和指令来赋予方向和任务。[44]按照朔伊纳的观点,国家目标规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暗示了未来有待形成的社会问题,并且对国家的行动施加了较少的限制。[45]目前,德国学界的通说认为,国家目标规定具有法效力,国家权力有法律上的义务去追求特定的目标。这种效力并非限定目标实现的路径或手段,而是允许主管机关,尤其是立法者享有选择权。这种效力限于对目标的追求,即国家不能放弃该目标。
(一)对立法机关
国家目标规定赋予立法者具体化的任务。当然,这里的具体化主要是具体化目标本身。因为目标越抽象,立法者具体化的任务就越大。如果立法者对行为的要求视而不见,就会导致立法不作为的违宪。立法者的形成优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立法者选择合适的手段来实现目标,比如到底是将社会给付设置为一种纯粹的客观法还是个人的一种要求公权力或第三人给付的请求权,立法者享有评估特权;另一方面,立法机关并不需要马上立法。立法机关能够根据现存的手段或者法律状态来决定立法的时机。[46]但是,立法者的形成空间并非绝对。大多数目标设定并不限于国家有义务实现目标,而且包含了实现目标的方式,通常就是要保质保量地实现国家目标规定。这种质量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层次,从而要求在不同的规范层次上获得实现:[47]一种是实质上的,即内容的实现,比如我国《宪法》14条第2款,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第19条第1款,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第二种是形式上的,即实现的行为方式,通常以禁止某种行为方式的形式体现出来,比如我国《宪法》9条第2款,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15条第3款,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三种是程序上的,即实现的过程。比如我国宪法第16条第2款,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第17条第2款,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二)对行政机关
对于立法机关已经具体化了的国家目标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在适用法律的时候注意该规定。这时,国家目标规定是作为一种解释标准而发挥作用,即在解释法律的概括性条款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时候,要进行基于宪法(国家目标规定)的解释。对于立法机关没有具体化的国家目标,国家目标规定发挥裁量指导的功能。[48]行政机关在选择多个法律后果的时候,它的裁量权的行使受到国家目标规定的约束。尤其在所谓的规划裁量领域,比如空间规划、行业规划和发展规划,国家目标规定是作为规划形成的指导。[49]比如行政机关在做土地规划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宪法》10条第5款“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的要求。
(三)对司法机关
法院必须把国家目标规定作为合宪秩序的一部分予以考虑。出于法律保留的原因,司法机关不能随意地进行目标实现。基于分工,法院不能像立法者那样去独自进行国家目标的形成。只有当法官去填补法律漏洞的时候,才能直接适用国家目标规定。国家目标规定对于司法机关而言,跟对行政机关一样,主要是一种解释标准。比如在“咸阳中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咸阳市农业机械总公司等企业承债兼并合同案”中,[50]法院认为,农机公司系国有公司,根据《宪法》16条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形式,实行民主管理……本案农机公司虽对公司改制及对职工的安置办法召集公司职工代表进行了讨论,但会议并未形成正式的职工代表会议决议,农机公司上报的《职工代表会议决议》未经职工代表签名确认,因此,该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在“黄志荣与广州交通集团南沙巴士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中,[51]法院认为,《宪法》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原审法院的处理是符合宪法相关规定的。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被上诉人作为国企有义务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劳动者生育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隐私,涉及国企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主张劳动者应当如实向用人单位报告是合理的。同时,国家目标规定越具体、立法者对于目标具体化和实现的评估特权越窄,法院对立法和行政的审查密度就越大。相反,目标设定越抽象、目标实现的条件越少,法院就越要尊重立法机关的形成自由。[52]
(一)冲突解决
国家目标规定的适用首先要解决两个层面的冲突:一个是国家目标规定与基本权利的冲突,另一个是国家目标规定之间的冲突。[53]
我国台湾学者林明昕将基本国策与基本权利的交互作用分为三种:(1)基本国策对于基本权利的制约作用。(2)基本国策对基本权利的填充作用。(3)基本权利对基本国策的回馈作用。[54]其中,后两种情形都反映了基本国策(国家目标规定)与基本权利之间的互补。[55]冲突主要发生在第一种情形。此时,基本国策代表一种公共利益对基本权利的行使构成了限制。比如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由此,如果有人发表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言论,该条就构成限制其言论自由的理由。当然,这种限制能否成立,还需要在“维护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国家目标与言论自由之间进行比例原则的检验。国家目标规定与基本权利的冲突更容易发生在那些宪法没有规定对其进行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身上,因为有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主要由立法去规定,而那些没有规定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意味着对于这些权利的干预只能基于宪法提供的理由,这被称为“宪法固有限制(verfassungsimmantente Schranken)。[56]国家目标规定就属于宪法固有限制的一种。
国家目标规定之间的冲突,比如环境保护的目标与社会国目标,按照德沃金和亚历克西的理论,应当通过权衡来解决。这首先意味着,既然国家目标规定要求最大程度地实现,那么在目标冲突的时候就不能过分重视某个目标而忽视其他的目标。其次意味着,国家目标规定之间存在一个有条件的优先关系。不同于规则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反对另一个的实施,目标冲突只能在个案中确定,即在一种情况下A目标优先于B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的情况下A目标也优于B目标。所以,国家目标冲突并没有绝对的优先关系。佐默曼总结的衡量标准包括:特殊的国家目标优于一般的国家目标、抽象的国家目标优于具体的国家目标(因为抽象的目标更接近核心目标)。[57]当然,这些权重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而变化。
(二)审查标准
国家目标规定的规范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具体规范的标准和界限,二是作为立法者的行为要求。第一种情况表现为立法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即立法违反了国家目标规定),第二种情况表现为立法不作为的合宪性审查(即立法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很好地履行国家目标规定所课予的立法作为义务)。
1.国家目标规定作为立法作为的合宪性审查标准。合宪性审查是审查立法是否与宪法的形式和实质规范相一致。国家目标规定一般只是其核心领域对立法者具有约束力,因为目标范围的具体化是立法者的评估特权。同时,宪法对目标实现的路径也没有特别的预设。由于立法机关享有评估特权,
所以宪法监督机构的审查是有限的。只有当立法明显违反了国家目标、并且没有其他重要的宪法目标对其进行正当化的时候,宪法监督机构才能宣布有问题的规范是违宪的。[58]
2.国家目标规定作为立法不作为的合宪性审查标准。一般来说,立法者的评估特权也包含选择实现目标的时间点。前提是,立法者关注目标实现的问题,并且在与其他目标的权衡中确定了实现目标的“成本收益”。如同立法作为违宪一样,立法不作为违宪也必须是在明显违反国家目标规定的情况下。[59]一个目标的实现是否将损害其他目标的实现或者对国家的财政给付能力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这在判断立法不作为,是否构成明显违宪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又取决于每个目标在宪法的目标结构中的地位以及重要性的程度。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还区分了真正的或者绝对的立法不作为和非真正的或者相对的立法不作为。前者是绝对的立法不作为,是指立法者未在适当期间内履行其宪法委托,进行相应的立法行为。后者是指立法者以违反平等原则的方式赋予特定一群人利益,而将特定另一群人排除在外,从而赋予另一群人请求立法者作为的权利。[60]国家目标规定也可以作为相对立法不作为的基础,国家的促进义务不仅要求积极的立法,也要求考虑所有相关的人群。
结语
过去对我国宪法总纲条款的批评主要在于,宪法总纲条款的修改过于频繁,从而影响了宪法的稳定性。[61]从现行宪法的修改来看,确实有40%的宪法修正案是针对宪法总纲条款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国家目标规定的功能恰恰就在于保持宪法的动态性。一方面,宪法向未来开放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国家目标的成文化也意味着国家行为的确定化。宪法中国家目标的结构越紧密,对政治过程的规制就越严格。同时,国家目标越具体,立法者在实现目标中的作用就越有限,从而对未来不可预见的发展无法做出适当反应的风险就越大。[62]可以说,国家目标规定这种纲领性条款在宪法中的出现,是法的安定性因应现代社会高度复杂性的必然结果。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宪法总纲条款的规范属性与实施机制研究》(12CFX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锴(1978-),男,陕西汉中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
刘犇昊(1985-),男,辽宁开原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
[1]据统计,1982年《宪法》的52条修正案中,针对宪法序言的修正案有9条、针对宪法总纲的修正案有21条,针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修正案有2条,针对国家机构的修正案有19条,针对国家象征的修正案有1条。
[2]参见胡锦光:《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30页。
[3]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172页。
[4]参见《栗战书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人大网,2018年4月20日访问。
[5]李惠宗:《宪法要义》,元照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660页;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523页。
[6]陈春生:《宪法要义》,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67页;郑贤君:《论国家政策入宪与总纲的法律属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编《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创刊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24页。学者陈新民更是将之列为除国家机关和人权规定之外的宪法的第三种结构,参见陈新民:《宪法学导论》,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431页。
[7]《新中国基本国策知多少》,载《海南人大》2009年第10期。当然也有不同说法,比如田平对法律、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计划纲要、政府白皮书梳理后,认为我国共颁布过九项基本国策,还包括长治久安、一国两制、水土保持。参见田平:《我国基本国策的内容及渊源》,载《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8期。而苏庄和杨文庄认为我国共有七项基本国策,还包括水土保持。参见苏庄、杨文庄:《对我国基本国策若干问题的分析和建议》,载《北方经济》2008年第2期。
[8]学者林克(Thomas Rincke)认为,国家目标规定首见于1793年法国宪法规定的保护工作、公共救助和教育的权利。Vgl. Thomas Rincke,Staatszielbestimmungen der 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Sachsen, Peter Lang, Frankfurt am Main/Berlin/Bern/New York/Paris/Wien, 1997,S.10.
[9]参见Der Bundesminister des Innern/Der Bundesminister der Justiz (Hrsg.),Staatszielbestimmungen - Gesetzgebungsauftr?ge, Bericht derSachverst?ndigenkommission, 1983,S.22.
[10]参见Hans Peter Ipsen, ber das Grundgesetz: gesammelte Beitr?ge seit 1949,Mohr, Tübingen, 1988,S.1,8.
[11]参见Hans Peter Ipsen, ber das Grundgesetz: gesammelte Beitr?ge seit 1949,Mohr,Tübingen, 1988,S.455.
[12]参见Der Bundesminister des Innern/Der Bundesminister der Justiz (Hrsg.),Staatszielbestimmungen - Gesetzgebungsauftr?ge, Bericht derSachverst?ndigenkommission, 1983,S.21.
[13]参见Hartmut Maurer, Staatsrecht I: Grundlagen, Verfassungsorgane, Staatsfunktionen, 6. Aufl.,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0,S.166.
[14]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326.
[15]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427.瑏瑠?参见Daniel Hahn, Staatszielbestimmungen im integrierten Bundesstaat: Normative Bedeutung und Divergenzen,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2010,S.80-81.瑏瑡参见Heinz-Christoph Link, Staatszwecke im Verfassungsstaat-nach 40 Jahren Grundgesetz, VVDStRL 48(1990),S.17f.
[16]参见Georg Ress, Staatszwecke im Verfassungsstaat-nach 40 Jahren Grundgesetz, VVDStRL 48(1990),S.62.
[17]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373.
[18]参见J?rg Lücke, Soziale Grundrechte als Staatszielbestimmungen und Gesetzgebungsauftr?ge, A?R 1982,S.23.
[19]参见Nicolai Müller-Bromley, Staatszielbestimmung Umweltshutz im Grundgesetz?: Rechtsfragen der Staatszielbestimmung als Regelungsform derStaatsaufgabe Umweltschutz, Erich Schmidt Verlag, Berlin, 1990,S.38f.
[20]BVerfGE 20,351,355;24,367,389;58,300,339.
[21]BVerfGE 6,55,72;76,1,49;87,1,35;24,367,389.
[22]参见J?rg Lücke, Soziale Grundrechte als Staatszielbestimmungen und Gesetzgebungsauftr?ge, A?R 1982,S.29.
[23]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371.
[24]参见Hans Peter Bull, Die Staatsaufgaben nach dem Grundgesetz, 2. Aufl.,Athen?um Verlag, Kronberg, 1977,S.44-45.
[25]参见Josef Isensee, Staatsaufgaben, in 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V,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6,Rn.115.
[26]参见Dietrich Murswiek, Umweltschutz als Staatszweck: Die ?kologischen Legitimit?tsgrundlagen des Staates, Economica Verlag, Bonn, 1995,S.11-12.
[27]参见Rico Faller, Staatszile? Tierschutz “: Vom parlamentarischen Gesetzgebungsstaat zum verfassungsgerichtlichen Jurisdiktionsstaat?,Duncker& Humblot, Berlin, 2005,
S.137.
[28]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Die Diskussion über die Normierung von Staatszielen, Der Staat 1993,S.440.
[29]参见Carl Friedrich Wilhelm von Gerber, ?ber ?ffentliche Rechte, Mohr, Tübingen, 1913,S.79.
[30]参见Hartmut Bauer, 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er Lehre vom subjektiven ?ffentlichen Recht,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86,S.22ff.
[31]目前德国基本法中的国家目标规定主要有:(1)社会领域的国家目标规定,包括基本法第20条第1款的社会国原则;(2)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国家目标规定,比如联邦宪法法院从基本法第5条第3款中推导出的文化国家的国家目标;(3)环保领域的国家目标规定,包括基本法第20a条规定的自然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4)经济和财政领域的国家目标规定,比如基本法第109条第2款规定的经济平衡;(5)外事和防务领域。比如基本法第23条第1款第1句规定的参与欧盟发展。Vgl. Daniel Hahn, Staatszielbestimmungen im integriertenBundesstaat: Normative Bedeutung und Divergenzen,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2010,S.114-117.
[32]BVerfGE 22,180,204.
[33]学者佐默曼认为,基于基本权利的客观法性质,基本权利和国家目标规定也具有同一性,即基本权利既是一种主观权利,同时也是一种国家目标规定。因为客观法性质的根源在于基本权利的原则特征,即基本权利作为一种最优诫命,从而如何让基本权利的效力和行使的可能性最大化就成为国家行为的目标。Vgl. 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420.
[34]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418.
[35](2016)粤19行终62号。
[36]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357.
[37]参见Dieter Grimm, Der Wandel der Staatsaufgaben und die Krise des Rechtsstaat, in: ders.(Hrsg.),Wachsende Staatsaufgaben - sinkendeSteuerungsf?higkeit des Rechts,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90,S.299f.
[38]参见Hermann Hill, Das fehlerhafte Verfahren und seine Folgen im Verwaltungsrecht, R. v. Decker’s Verlag, G. Schenck, Heidelberg, 1986,S.190.
[39]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40]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41]参见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1. 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85,S.75.
[42]参见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1. 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85,S.76.
[43]参见Jan-Reinard Sieckmann, Regelmodelle und Prinzipienmodelle des Rechtssystems, Nomos Verlagsgesellschat, Baden-Baden, 1990,S.141.
[44]参见Ulrich Scheuner, Staatszielbestimmungen, in: Roman Schnur (Hrsg.),Festschrift für Ernst Forsthoff, C. H. Beck?倕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72,S.335.
[45]参见Ulrich Scheuner, Staatszielbestimmungen, in: Roman Schnur (Hrsg.),Festschrift für Ernst Forsthoff, C. H. Beck?倕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72,S.325,336.
[46]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379f.
[47]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382.
[48]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 Umweltschutz “mit Gesetzesvorbehalt?,DVBL 1991,S.35.
[49]参见Thomas Rincke, Staatszielbestimmungen der 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Sachsen, Peter Lang, Frankfurt am Main/Berlin/Bern/New York/Paris/Wien, 1997,S.164f.
[50](2013)陕民二终字第00076号。
[51](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65号。
[52]参见Daniel Hahn, Staatszielbestimmungen im integrierten Bundesstaat: Normative Bedeutung und Divergenzen,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2010,S.94-95.
[53]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383.
[54]林明昕:《基本国策之规范效力及其对社会正义之影响》,载《台大法学论丛》2016年第45卷特刊。
[55]比如我国宪法第46条仅仅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如何受教育,该条并不明确。相对地,宪法第19条就规定的国家在教育领域的目标和任务,有助于填补并理解受教育权的内涵。
[56]BVerfGE 28,260f.
[57]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414.
[58]参见Der Bundesminister des Innern/Der Bundesminister der Justiz (Hrsg.),Staatszielbestimmungen - Gesetzgebungsauftr?ge, Bericht der Sachverst?ndigenkommission, 1983,S.50f.
[59]参见Helmut Simon, Die Aufnahme von Staatszielbestimmungen in die Verfassungen, in: Herta D?ubler - Gmelin (Hrsg.),Gegenrede: Aufkl?rung, Kritik, ?ffentlichkeit, Festschrift für Ernst Gottfried Mahrenholz,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94,S.451.
[60]参见王锴:《论立法不作为的违宪》,载《东吴法学》2007年春季卷。
[61]参见张义清:《基本国策的宪法效力研究》,载《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62]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374.
【期刊名称】《法学论坛》【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