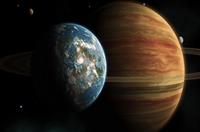
如果说,我国多年流行的劳动价值论仅仅承认劳动对商品价值的作用,因而是单一要素的价值论,那么,现在,我们应当综合考虑劳动和资产等客体因素与商品效用这个主体因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建构“系统价值论”。
一、既要肯定劳动的作用,又要承认资产的作用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各种商品之所以能够互相交换,互相表现为交换价值,“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1]所谓价值,就是各种商品之间的相对比价。这是完全正确的。它是我们分析商品价值的基础。
然而,马克思断言:“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具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于是,“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然后,“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这就是商品价值的实体[2]。于是,劳动就成为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
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逻辑上的跳跃:商品本来是由一定的劳动和相应的自然资源或物质资料(本文统称之为资产,即生产的物质条件)结合而成的,可是,为什么各种商品中“共同的东西”却只剩下了“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呢?完全舍弃掉自然资源或物质资料是合理的吗?有人可能会说,自然资源及其形成的使用价值,具有种种质的差别,无法相互比较,因而不属于各种商品中的“共同的东西”。可是,具体劳动不也同样具有种种质的区别吗?既然可以从具体劳动中分析出抽象劳动,它们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不是也可以从种种自然资源中抽象出“一般资源”吗?难道自然资源就是纯粹的“个别”,不存在“一般”吗?倘若真的如此,强调一般与个别统一的辩证法岂不是被推翻了吗!至于这个“一般资源”到底如何计量,其实与抽象劳动的计量一样,可以并且事实上也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可见,如果承认商品价值就是各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共同的东西”,那么,就必须合乎逻辑地承认,商品价值是抽象劳动和一般资源的统一,丢掉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是片面的。
传统劳动价值论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出发,导出一个重要论断:“机器等生产资料只能转移价值,而不能使价值增殖”。这已经被大量事实所证伪。例如,农民在不同的土地上耕作,虽然付出同样的劳动,但收获是不同的,而同样的农产品当然含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说,好地会带来更多的价值,其中,土地本身的增值作用不可否认。这个事例带有普遍性:一切物质生产都离不开一定的劳动资料、生产工具,这些劳动资料同农民土地具有相似的地位和作用。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通常也会大大提高实物劳动生产率,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条件下,创造出更多的商品,而同样的商品在同一时期基本也是等价的,更多的商品意味着更多的价值。这也是人们愿意采用先进机器的原因。假如机器不能使价值增殖,谁还会劳而无功甚至甘冒风险地使用先进机器。许多劳动工具特别是“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从笨重和简单的体力劳动到灵巧和复杂的脑力劳动),发挥着同劳动相似的作用,二者具有一定的等价性。为什么人的劳动可以创造价值,而代替人劳动的那些劳动资料就只能转移价值呢?实际上,市场只认商品这个最终成果,而不管它是由人还是由机器生产的。
由于资本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资本所有者所得到的回报,在一定范围内,应当看作是正当的和合理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过去把资本的一切回报都看作是剥削,是夸大了剥削量。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个人占有的财产会愈来愈多,在满足即期消费之余,人们必然会把一部分财产作为投资,享有它所带来的回报,这会成为愈来愈普遍的现象。如果认为一切投资回报都是剥削,那么,就会得出我国经济愈发展,剥削者和剥削现象也愈来愈多的荒唐结论。
关于自然资源没有价值的观点也是非科学的。从国际市场上看,人们对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决不能无偿获取,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有价值的。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有其必然的根据。一方面,由于这些资源的稀缺,所以,那些缺少但又需要它们的人,就必须耗费一定的劳动,才能生产出它们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与那些资源是等价的,这就使自然资源具有了相对的价值。而商品的价值量本来就是按照社会尺度衡量的,而不是按照个别情况确定的。所谓资源无价值,实际是资源十分充裕、因而可以任人索取的个别情况。另一方面,人们之所以愿意付出一定的价值(表现为货币)去购买商品,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具有使用价值。而且,使用价值越大,人们往往愿意付出的价值也越多。而自然资源显然是有使用价值的,其中不少资源的使用价值还很高,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会付出较高的价值去购买这些资源。这也使自然资源具有了价值。概言之,自然资源的“稀缺”和“有用”,而不论它们是否包含劳动,都使人们不能不承认它们是有价值的。而否认自然资源具有价值的观点,客观上只会助长人们对资源的随意损耗和浪费,社会效果是不好的。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极多。直到今天,我国还有不少由国家控制的资源性产品,仍然定价过低,造成了本来就很贫乏的宝贵资源损耗过多,加剧了资源短缺的矛盾。
总之,从商品价值的形成和增殖来看,劳动固然起着主导的和主要的作用,因为它是把资源转化为商品的推动力和控制力,但是,劳动创造价值离不开一定的生产条件,没有后者,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由于各个劳动者所拥有的生产条件特别是劳动资料是不同的,因此,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差异很大,其中,资产(包含生产资料等各种有形资产以及无形资产)的作用不容否定。
二、既要考虑客体因素(劳动和资产),又要考虑主体因素(商品效用)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究竟具有多少价值,不仅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和资源,而且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购买者的需要,或者说,取决于商品有多大的效用。
这是看待商品价值的理论框架的变化:商品对于使用者来说,仅仅是客体,如果认为商品价值只包含劳动的耗费,就是单纯从客体的角度看问题,这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还需要从主体角度来看商品的价值,看它对于主体有多大的效用。
这是在真实的市场上人们可以反复验证的事实:商品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绝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它消耗了多少劳动和材料,同时甚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对使用者有多大用处,从而促使人们愿意付多少货币来购买它。实际上,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很少考虑它包含着多少劳动,更多考虑的是它有多大的用处。这个“用处”是决定消费者愿意承受的价格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消费行为是注意商品的“质价比”,即商品质量的优劣与价格高低是否相互对应,它表明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直接与可接受的价格(价值是价格的抽象)有关。也许,有人在此又会提出,商品的效用不仅在各个商品是不同的,而且对于众多使用者也是差别很大的,怎么可能衡量它们呢?实际上,这又是一个“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各种商品的效用确实是各不相同的,这是个别,但同时,它们中又存在着一般即“有用性”。这是各种商品对于使用者的意义,是质的共同性。从这个角度看,各种商品同样只是具有量的差别,因而也可以互相比较。至于它们的实际计量,如同对于劳动价值的计量一样,也是由市场来实现的。
马克思可能也意识到了忽略社会需求是个重要缺陷,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界定了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人们通常称之为社会必要劳动Ⅰ)以后,在《资本论》第3卷中又补充说:“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3]这段话所表达的就是社会需求对于商品价值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相对于社会需求的社会必要劳动,人们称之为社会必要劳动Ⅱ。
恩格斯也表达过类似思想。1844年,他在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4]——《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还是由效用决定的争论,明确指出:“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争论的双方都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5]他在《反杜林论》中又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这里,恩格斯仍然把“效用”和“劳动”两种因素而不只是“劳动”看作是决定商品价值的东西,并且认为,这两种因素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不计量。“但是,”恩格斯接着说,“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6]后一点与事实不完全相符,本文上面已经作了说明。
所以,商品的价值,既取决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和资产,也取决于它对消费者的效用,是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的统一。前者构成了商品的生产成本,是生产者愿意出售价格的下限;而商品价格的上限,则是商品生产成本与一定的附加额之和,它们主要取决于商品的效用大小,是消费者认为它值不值、愿意付出多少货币的主要原因。这就是本文所说的“系统价值论”,列成公式即是:
这里的劳动、资产以及效用,均指社会平均值。正像个别劳动要折合成社会必要劳动一样,个别商品所包含的其他要素多少,也要按照社会平均值而不是个别情况来加以计量。
这个公式表明,商品价值是由客体因素(劳动和资产)与主体因素(商品效用)共同决定的,而不是由劳动这个单一的生产要素构成的。商品价值与这些要素的大小成正比。如果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相等,即所投入的劳动和资产相等,“那末”,正如恩格斯所说,“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倘若一种商品的效用很大,即使它的生产成本不高,也具有较高的价值。假如两种商品的效用相同,那么,社会平均生产成本愈高的产品其价值也愈大。毋庸多言,公式中的商品效用以及劳动和资产只能为正数,否则,就无所谓商品价值。
至于劳动、资产和商品效用这些不同质的东西如何互相比较,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到的,资产的价值通常用生产出其替代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衡量,即以劳动为本位。而商品效用可以看作是劳动和资产的系数,这也是公式中使用“×”(乘号)的原由。
“系统价值论”显然比只承认劳动作用的“单一要素价值论”更为合理。
三、既要尊重劳动和劳动者,也要重视资产和所有者,更要关注社会需求和消费者
科学理论不仅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解释世界”,而且要为人们的实践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思路,“改变世界”。系统价值论同样具有这种社会作用。
劳动的主体是劳动者,要充分发挥劳动的主导作用,毫无疑问,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简言之,尊重劳动者,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注意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产的主体是所有者,资产的有效利用同所有者的利益有直接关系。我们要促进资产的节约、更新和合理配置,就必须尊重所有者,保护所有者的合法权益,注意调动所有者的积极性。否则,资产的闲置、损失、浪费就不可避免,我国经济的发展就会因为“瘸腿”而步履蹒跚。在当代中国,明确界定所有权和产权,健全保护所有者权益的法律和法规,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在总结概括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反复强调“按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论。尽管这个论断中没有直接谈及商品价值理论,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分配的无疑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它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显然是以默认各种生产要素对商品价值都有一定贡献为前提的,而同只承认劳动是价值惟一源泉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假如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资本等物的要素,仅仅对使用价值的增加有贡献,而对价值的增殖无作用,那么,它们就没有资格要求分配,所谓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中的“贡献”也是用词不当了。事实决非如此。这种对资本等要素作用的新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且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体现了对商品价值源泉以及剥削等问题的新认识。
尤其应当看到,我国现在和将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严重过剩,而资产、资源、资本严重短缺。后者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假如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仍然像过去一样,只知一味地高扬劳动的作用而贬低资产的作用,那只会破坏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啻是亡党亡国的经济学。
还应指出,在当代中国,劳动者与所有者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交叉关系:几乎所有的劳动者都拥有或多或少的公有的以及个人的资产(社会越向前发展,劳动者拥有的资产也会越多),而绝大部分所有者都从事着一定形式的劳动(经营管理劳动、科学技术劳动直至直接操作劳动)。所以,我们在强调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同时,提出要重视资产、重视所有者,并非同劳动者利益相悖而是同其一致的。这不仅因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有利于劳动者,而且因为所谓所有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劳动者的另一重身份,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对劳动者利益的全面维护。当然,也不能把劳动者与所有者简单等同起来,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别和矛盾的,我们要注意依法协调他们的关系,兼顾二者的利益,尽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进一步说,劳动者和所有者并没有将社会经济主体概括无遗,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消费者,他也是重要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特别是买方市场的条件下,用户、顾客、消费者更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进入生产过程的一切所有者、劳动者及其结合而成的企业来说,谁的商品和服务受到消费者欢迎,谁拥有更多的消费者,谁就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谁就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谁就会有更为美好的未来。因此,在现代比较先进的企业中,“顾客就是上帝”、“用户满意是最高准则”等思想,正在成为生产经营的重要指导思想。1986年发端于美国的所谓CS(英文Customer Satisfaction的缩写,意即顾客满意度)战略,即以顾客满意度为最高指针的生产经营战略,正在全世界日益扩大其影响,就是一个证明。从更宏观的角度说,社会生产最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且是衡量生产结构是否合理的最终尺度。因此,在研究社会生产以及利益关系时,不能忽略社会需要及其承担者即消费者。
消费者同劳动者以及所有者是有差别的统一,但不是完全等同的。诚然,无论是劳动者,还是所有者,为了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是消费者。就此而言,他们是同一的。但是,在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自给自足的产品和服务微乎其微,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基本上都是由他人提供的,而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及服务也几乎全部用于他人的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消费者利益并不等于劳动者利益或所有者利益。这时,他们的统一表现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互相依存和互相换位:一方面,他们互相依存。没有劳动者以及所有者,就谈不到消费和消费者;而没有消费者,劳动者以及所有者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及其产品就毫无用处。他们彼此相依,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同一些人们在此时此地为劳动者或所有者,在彼时彼地又变为消费者,他们不断地转换自己的经济角色,从而构成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复杂多变、环环相扣、难解难分的链条和网络。总之,劳动者、所有者、消费者之间总体上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差别性统一。
以上,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区分,是根据他们是物质生产中劳动和资产两类要素的提供者作出的;而这两者与消费者的划分,则是按照他们分别代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确定的。这是根据不同标准提出的两种分类,各有其实际意义。这两种分类有一定交叉,但又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说,它们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既然社会经济主体区分为劳动者、所有者和消费者,他们又代表着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发展要求,我们要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既要注意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这是基本的),又要注意他们之间利益的差别。综合起来说,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应当克服所谓美英式“所有者的经济学”(马克思称之为“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的政治经济学” [7])、德日式“生产者的经济学”、计划经济中“劳动者的经济学”各自的片面性,实行以消费者利益为最终归宿的、以劳动者利益为中心的、兼顾所有者利益的“三者兼顾的经济学”。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页注。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页。
*此文原载于《求索》2005年第1期,略作修改后再发于《研究生教育》(内刊)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