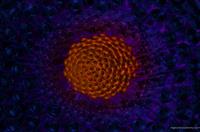
摘要:中国城市居民在储蓄、基金、保险、贷款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受排斥状况,即他们不能以恰当合理的方式获得这些金融服务。这种金融受排斥状况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基于2007年中国15城市居民投资行为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高都可以降低居民受到金融排斥的可能性,而居民在储蓄方面没有被排斥也可以降低他们在基金、保险、贷款等方面受到排斥的可能性。不同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也有着其他不同的影响因素。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维护和增进中国居民的福利需要解决他们的金融排斥问题,这需要有关机构采取措施来增加居民的家庭资产积累、改善居民在获得金融服务时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居民有一定的储蓄存款。
关键词:金融排斥,储蓄,基金,保险,贷款
一、引言
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表明,金融是其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的持续、收入分配的改善、贫困问题的解决、社会福利的增进都需要将有限的资源和相应的风险配置到那些最具生产效率和风险承担能力的使用者手中。为了实现资源和风险的最优配置,一个高效、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是至关重要的(Allen and Gale,2000;Demirgü??-Kunt and Levine,2009;Levine,2005,2008),它对居民福利应当发挥双向调节作用:当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时,它能够帮助居民分享经济发展红利;当经济处于衰退和危机阶段时,它能够帮助居民抵御经济下行风险。但是,传统金融理论建立在一个有待检验的关键假设基础之上:居民能够自由、充分、无障碍地获得其所需的金融服务,而不是被排斥在这些金融服务之外,即对这些居民而言不存在金融排斥。然而,金融排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现象(Demirgü??—Kunt et al.,2007)。Panigyrakis et al.(2002)指出,金融排斥的核心特征是某些人群不能以恰当合理的方式获得金融服务。这里的金融服务既包括储蓄等无风险金融产品,也包括投资于基金等风险性金融产品,还包括购买保险和获得信贷。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排斥的具体表现形式既可能是居民为获得某些金融服务进行了努力却最终无法成功的被动金融排斥;也可能是自我金融排斥,即居民认为寻求获得某些金融服务时会被拒绝而自己主动不去尝试获得那些金融服务。相反,当居民对某些金融服务没有需要时,尽管这也表现为金融排斥,但由于居民是自愿且无需要的,这实质上不是金融排斥。与金融排斥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居民的金融排斥状况?Kempson Whyley(1999a ,1999b )总结的渠道、条件、价格、营销、资源排斥等五种表现形式对应着金融排斥的五种成因,但它们是概括性的且相互交叉。文献中就居民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扩展分析。从金融排斥的涵义可以看出,居民的金融排斥是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金融机构对金融服务的供给无法恰当匹配造成的,因此影响因素包括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无法详细考察作为金融服务供给方的金融机构的特征对居民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而专注分析与作为金融服务需求方的居民相关的各种因素的作用。
首先,居民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会影响其金融排斥状况,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宗教信仰、种族、政治面貌等。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倾向(Jianakoplos and Bemasek ,1998)。
因此,金融机构在选择风险性金融产品和贷款的服务对象时会青睐男性,而在选择无风险金融产品和商业保险的服务对象时正好相反。当然,女性更强的风险规避倾向可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男女间不同的年龄、家庭规模、财富状况和收入水平等因素造成的(Christiansen et al.,2009),考虑了这些因素后,男女间风险态度可能没有显著差异,因而性别不会影响居民的金融排斥状况。标准的资产组合选择范式认为,能够解释与年龄相关的资产组合结构差异的唯一因素是不同的风险态度,随着年龄增加,居民会趋于厌恶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在选择风险性金融产品和贷款的服务对象时会青睐年轻人,而在选择无风险金融产品和商业保险的服务对象时正好相反。但是,这种推测建立在有待证实的个体风险容忍度随年龄递减假设之上。类似地,年龄对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可能反映了财富、收入、认知能力等因素的作用(Ameriks and Zeldes,2004),因此可能没有直接影响。家庭为居民提供了抵御外部社会风险的凭借,可能提高了居民承担风险的能力,因此,已婚居民是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性金融产品和贷款的首选对象,而在选择无风险金融产品和商业保险的服务对象时正好相反。但是,婚姻契约的维护可能降低了已婚居民的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得到完全相反的金融排斥预期。婚姻状况对居民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还可能是间接通过影响居民财富水平来实现的(Christiansen et al.,2009),而没有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使居民更容易理解并以更低成本来消费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Guisoetal.,2008),所以金融机构会把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作为首选客户。然而,受教育程度也可能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间接通过受教育程度所反映的学习和认知能力来影响金融排斥状况。健康状况越好的居民更愿意投资风险金融产品和进行借贷,而较少考虑无风险金融产品和商业保险,因此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会有相应的针对性。健康状况的这种影响并不是通过对风险态度、投资期限和健康保险来实现的(Rosen and Wu,2004),健康状况差异可能导致总体金融财富变化(Berkowitzand qiu ,2006)或居民其他方面不可观测差异(Smith and Love,2007),因而健康状况可能没有直接影响。家庭人口越多,用以购买金融产品和享受金融服务的资源越多(Hononhan,2006),可能越少受到金融排斥,但家庭人口增多也会增加居民家庭开支进而减少可用于购买金融产品和享受金融服务的资源,使其受到更严重的金融排斥(FSA ,2000)。家庭中更多的未成年人和老人既可能增加家庭开支进而减少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资源,也可能促使家庭积极进行储蓄和股票投资、购买商业保险、寻找贷款进而减轻居民的金融排斥。宗教信仰使信众更加认同勤奋工作与储蓄的信念,也更加坚信一些有利于市场发展的信念,如合作、信任政府与法制、竞争(Guiso et al.,2003)等,成为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的首选对象。同样,宗教信仰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可能反映了宗教对工资水平(Chiswick,1983)、受教育程度(Freeman ,1986)、健康状况(Ellison ,1991)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对金融排斥状况的间接作用。少数族裔居民可能会受到更多歧视,因而是金融排斥对象(Devlin,2005);但种族平等观念的强调和相应实践的推行可能推动金融机构向他们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减轻其金融排斥。作为共产党员的居民可能有更多途径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因此较少受到金融排斥;但党员身份可能通过提高个人和家庭收入来间接影响金融排斥(Liu ,2003)。
其次,居民的经济财富特征会影响其金融排斥状况,包括收入、家庭资产、家庭负债、信贷约束等。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家庭资产、更少的家庭负债都意味着居民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能力来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因而这些居民构成了金融机构的首选客户(Devlin,2005)。但是,收入水平和家庭资产分别对应着流量和存量性质的经济财富,金融机构在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时可能会有不同的倚重,所以收入水平和家庭资产对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可能会因不同的产品和服务而异。由于居民的家庭负债会影响其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和净资产水平,因此家庭负债对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可能不是直接的。居民的信贷约束制约着他们的可得资金数量,所以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会优先选择信贷约束程度较轻的居民(Buckland and Simpson,2008)。此外,我们还单独考察了居民是否拥有房产对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房产具有很强的不可分性,转换资产形式时交易成本很高,并且会减少居民赖以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资源(吴卫星、齐天翔,2007),因此金融机构会向有房居民提供较少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房产是居民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时最理想的抵押品之一,如果存在一个完善的房产抵押市场,那么有房居民的金融排斥状况会较轻(Cardak andWilkins ,2009)。因此,房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第三,居民的主观心态、态度和信念以及社会结构会影响其金融排斥状况,包括信任度、乐观度、风险态度、社会互动程度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普遍具有时间分离特征,即当前投资和未来回报的交换,这需要资金提供者对资金需求者的信任。在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和服务时,信任可以理解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居民对金融机构是否会尽其所能履行合同的主观判断。因此,居民信任度越高,金融机构越容易把他们作为服务对象(李涛,2006a )。乐观程度越高的居民对未来不确定的前景越充满希望,承担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和风险的意愿越强(Purland Robinson,2007),金融机构越愿意向他们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不愿承担在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时的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在选择无风险金融产品和商业保险的服务对象时会优先考虑厌恶风险的居民,而在选择风险性金融产品和贷款的服务对象时相反。但李涛、郭杰(2009)发现,中国人的风险感知程度会受其所在群体的影响,这使得风险态度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可能不显著,进而导致金融机构在选择客户时不再以其风险态度作为唯一参考,因此居民风险态度对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可能不显著。社会互动通过信息交流、感受共享、规范内化等内生互动机制和示范效应等情景互动机制推动了居民更加积极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李涛,2006b ),因此金融机构在选择客户时会青睐社会互动程度较高的居民。
已有研究对金融排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美国(Aizcorbe etal.,2003;Hogarth and O ‘Donnell ,1999;Jacobson,1995;Lee ,2002)
和欧盟国家(Devlin,2005;Kempsonetal 、2007),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的居民在基本银行账户、储蓄、信用卡服务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金融排斥,且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就中国而言,尽管大量研究探讨了中国金融系统的特征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却鲜有文章关注中国居民金融排斥状况。Demirgü??-Kunteta1.(2007)指出,减轻金融排斥对于提高各国居民社会福利水平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当然包括中国在内。减轻中国居民金融排斥的政府政策的制定需要依靠对这一问题的现状和成因的科学研究,这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二、数据样本和分析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2007年7—8月进行的“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项目。该调查访问了北京、上海、长沙、郑州、兰州、大连、重庆、西安、合肥、济南、烟台、沈阳、深圳、杭州、嘉善等15个城市的1355名居民,详细调查了他们的投资行为和心态。为保证样本质量,我们首先剔除了8名不满18周岁的受访者,然后又剔除了185名调查人员认为回答不可靠或很不可靠的受访者。最终有效样本包括1162名城市居民。
与FSA (2000)一致,我们从储蓄、贷款、保险等三类基本金融服务对样本居民的金融排斥状况进行考察。考虑到基金也是中国居民经常从基金公司那里获得的金融产品,
我们将基金也纳入样本居民的金融排斥范围。由于中国城市居民对以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更多地是基于家庭层面,因此我们在测度其金融排斥状况时依据的是居民家庭资产和负债的信息。具体而言:居民是否在储蓄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虚拟变量记作exclu-saving,当居民家庭没有银行存款时,赋值为1,反之为0;居民是否在基金投资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虚拟变量记作exclu_mutualfund,当居民家庭没有购买基金产品时,赋值为1,反之为0;居民是否在商业保险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虚拟变量记作exclu_insurance ,当居民家庭没有购买保险产品时,赋值为1,反之为0;居民是否在贷款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虚拟变量记作exclu_loan,当居民家庭没有购房、购车、做生意或教育等形式的贷款时,赋值为1,反之为0.以上四组虚拟变量赋值为1时,表示居民在该金融产品或服务方面受到了排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以上金融排斥定义不仅包括了上文提及的被动金融排斥和自我金融排斥,还包括了居民对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没有需要的情况,而后者并非金融排斥。因此,我们可能高估了样本居民的金融排斥状况。由于调查问卷中缺乏相应的居民家庭对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信息,我们只能采用以上金融排斥变量构造方法(o ,因此本文对中国城市居民金融排斥状况影响因素的分析可能高估了各种影响因素的实际作用,但这至少给出了上限估计,为今后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进行准确估计提供了参考。
居民性别记作female,男性赋值为0,女性赋值为1.居民年龄记作age ,考虑到居民年龄对其金融排斥状况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我们引入了居民年龄平方项age_sq.居民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已婚、离异和丧偶四种情形,分别记作single、married 、divorced、partnerdead ,对应相应婚姻状况时,该变量赋值为1,反之为0.居民受教育程度记作schooling_year,对应着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居民健康状况记作health,赋值为1到5的整数,分别对应居民认为自己健康状况非常差、较差、一般、较好或非常好。居民家庭结构包括家庭人口数、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口数、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等三组变量,分别记作family_size 、young_size、old_size.居民宗教信仰记作religious ,当居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时,赋值为0,反之为1.居民种族类型记作minority,少数民族赋值为1,汉族为0.居民政治面貌用党员身份来表示,记作ccp_member,共产党员赋值为1,反之为0.
居民收入水平用其家庭过去一年内全部家庭成员的平均月收入来衡量,单位是人民币万元,记作month_fam_income.考虑到居民收入水平对其金融排斥状况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我们引入了居民家庭平均月收入水平的平方项month_fam_income_sq.居民家庭总资产记作assets,家庭总负债记作debts ,单位都是人民币万元。居民信贷约束记作financial_constraint,赋值分别为1到5的整数,分别对应居民认为向别人或金融机构借钱非常容易、比较容易、一般、比较困难和非常困难。居民是否拥有房产用own_house 来表示,当居民家庭拥有自有房产时,赋值为1,反之为0.
居民信任度包括居民对社会上绝大部分人、政府监管部门、司法机构、财经媒体、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分别记作trust_social、trust_govreg、trust_legal、trust_media 、tmst_finins ,赋值为1到5的整数,分别对应居民非常不信任、不信任、一般信任、信任或非常信任的情形G )。居民乐观度包括居民对经济形势、收入水平、就业等的乐观程度,分别记作optimism_economy、optimism_income、optimism_employment.当居民对经济形势表示悲观时,optimism_economy赋值为1;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时赋值为2;乐观时赋值为3.当居民认为收入水平会减少时,optimism_income 赋值为1;不变时赋值为2;增加时赋值为3.当居民对就业表示悲观时,optimism_employment 赋值为1;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时赋值为2;乐观时赋值为3.居民风险态度用其风险规避程度来进行测度,记作risk_attitude,赋值越大,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如果赋值为正,表示居民是厌恶风险的;赋值为0,表示居民是风险中性的;赋值为负,表示居民是喜好风险的。居民社会互动程度变量分别用居民在进行储蓄、购买基金、购买保险时的社会互动程度来表示,相应的变量名称为si_saving 、si_mutualfund 、si_insurance,当居民周围的人现在大多采取同样行动时,相应变量赋值为1,反之为0.此外,在回归分析中我们还引入了居民所在城市的虚拟变量。
三、实证分析
我们在本节中分别汇报并讨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和相应的实证回归发现。
1.统计分析结果
表1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Harrison(1994)指出,居民拥有金融产品的决策呈现出从最初级的银行活期存款到其他更复杂的金融产品的层级结构,因此储蓄是居民获得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基础。Hogarth O ‘Donnell(2000)和Devlin(2005)证实了居民在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影响着他们在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相应地,依据居民是否面临着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我们把总样本细分为两个子样本。表1同时给出了基于总样本和两个子样本的均值统计结果。
样本居民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金融排斥状况,这表现为:分别有近80%、69%、89%的居民在基金、保险、贷款等方面受到了金融排斥;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近27%的居民在储蓄方面受到了金融排斥,尽管中国居民储蓄率位居世界第一。进一步地比较两个子样本的金融排斥状况,在储蓄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子样本中的居民在基金、保险、贷款等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更加严重。
样本居民中:40%是女性,平均年龄34岁;近38%未婚,平均接受了13年教育(即高中和大学之间),平均健康状况较差,平均家庭规模近4人,小孩和老人各1个,15%有宗教信仰,36%是少数民族,14%是共产党员,过去一年内家庭平均月收入是6925元,居民家庭总资产平均为近35万元,总负债平均为4.6万元,居民面对的信贷约束程度平均较强,感觉向别人或金融机构借钱的困难程度在一般和比较困难之间,43%的居民家庭有自有房产;居民对社会上绝大部分人、政府监管部门、司法机构、财经媒体、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平均较高,都介于一般信任和信任之间;居民对经济形势、收入水平、就业等的乐观程度平均较高,对经济形势和就业的看法介于中性和乐观之间,对收入水平的看法介于不变和增加之间;居民是风险规避的;超过38%、24%、13%的居民周围的人现在分别有存款或购买了基金或保险。
2.回归分析结果
针对居民在储蓄、基金、保险、贷款等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表2、3、4、5分别给出了相应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特别地,在考察基金、保险、贷款等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因素时,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与研究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因素相同的那些因素外,鉴于储蓄构成了居民享受这三种金融服务的可能门槛(Harrison,1994),我们额外引入了居民在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作为居民在基金、保险、贷款等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回归分析中用来解释居民金融排斥状况的一些解释变量可能是内生的,例如居民的经济财富特征、主观心态、态度、信念以及社会结构等,因此有关的回归结果可能揭示的是这些因素和居民金融排斥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但是,深入研究居民金融排斥状况与各种可能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须建立在首先识别出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的贡献正在于讨论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居民金融排斥状况的因素的具体效果,包括外生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和可能内生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可得性,进一步选择那些可能的内生变量、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探讨因果关系是今后研究需要关注的。鉴于被解释变量的虚拟变量性质,我们采用了probit回归模型。为了解释方便,回归结果没有汇报各种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而汇报了各解释变量的变化对居民金融排斥状况的边际概率影响,即边际效果。
表2汇报了居民在储蓄方面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因素的三组回归结果,分别对应除居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民族、党员身份、家庭结构、家庭房产、家庭收入水平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组合的不同选择。显著且稳健的发现包括:有宗教信仰、是少数民族、家庭中较少的未成年人数、有自家房产、较少的家庭资产、较多的家庭负债、对司法机构较低的信任度、对金融机构较低的信任度、在储蓄方面较低的社会互动程度都会增加居民在储蓄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可能性,而居民年龄对其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 型影响,转折点在40至42岁之间,但年龄上升的总体影响大致是负的。具体而言,其它因素不变:居民从无宗教信仰变为有宗教信仰、从汉族变为少数民族、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减少1个、从家庭没有房产变为有房产、家庭资产减少1万元、家庭负债增加1万元、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减少1个单位、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减少1个单位、从周围的人现在大多有储蓄变为大多没有储蓄,他们在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可能性会至少增加6.12%、8.73%、8.02%、6.12%、0.65%、0.25%、6.75%、5.32%、4.53%.
以上显著发现基本都可以对应引言中给出的理论预期:金融机构在选择储蓄客户时青睐年纪大的居民,特别是中年人,因为年纪大的居民更加厌恶风险,而老年人可能由于收入的减少在储蓄方面受到的忽视程度比中年人高一些;少数族裔的居民可能会受到金融机构更多的歧视;家庭中未成年人的增加促使居民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成为金融机构提供储蓄服务的优先客户;房产的高流动成本及其对资金的大量占用使得金融机构在储蓄方面更加青睐没有家庭房产的居民;金融机构会优先为那些拥有更多家庭资产或更少家庭负债进而更多金融资源的居民提供储蓄产品;对司法机构或金融机构信任度更高的居民越容易成为金融机构在储蓄方面的服务对象;居民在储蓄方面更高的社会互动程度降低了金融机构在提供储蓄产品时的成本,因而减轻了他们在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唯一例外的是,与文献预期不同,宗教信仰增加了居民在储蓄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概率。中国人普遍信仰的是儒家文化,而在变量构造中,我们把儒家文化归入了没有宗教信仰的一类。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儒家文化是最强调节俭与储蓄的,因此与一般的信仰儒家文化的中国人相比,信仰其他宗教的居民在储蓄方面更容易被金融机构所排斥。其他解释变量对居民在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可能性没有显著的解释力,这也可以从引言提及的理论预期中找到相应的解释。
与表2相似,表3汇报了居民在基金方面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因素的五组回归结果,分别对应除居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宗教信仰、种族、党员身份、家庭结构、家庭房产、家庭收入水平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组合的不同选择。与表2不同,我们在回归结果(1)和(4)基础上分别引入了居民在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得到了回归结果(2)和(5)。显著且稳健的发现包括:是少数民族、非共产党员、较少的家庭资产、对金融机构较低的信任度、在基金方面较低的社会互动程度、较强的信贷约束、对收入水平更加悲观的预期、在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都会增加居民在基金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可能性,
而居民年龄对其基金方面的金融排斥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 型影响,转折点在33至43岁之间。具体而言,其它因素不变:居民从汉族变为少数民族、从共产党员变为非共产党员、家庭资产减少1万元、对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减少1个单位、从周围的人现在大多有基金变为大多没有基金、信贷约束增加1个单位、对收入水平预期的悲观程度增加1个单位、从储蓄方面没有金融排斥变为受到金融排斥,他们在基金方面的金融排斥可能性会至少增加18.01%、8.43%、0.04%、1.65%、0.29%、6.67%、18.56%、8.98%.
与表2类似,表3的回归发现也都可以对应着引言中给出的理论预期:尽管年龄的增加会增加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但其风险容忍度可能随着财富的积累在中年时达到最大值,因此金融机构在选择基金客户时更偏好中年居民;少数民族居民可能会受到金融机构更多的歧视进而在基金产品方面更加严重的金融排斥;党员身份可能方便居民以更多的渠道和途径进行基金投资,降低了其基金方面的金融排斥概率;家庭资产越多的居民可能用于基金投资的资源越多,会成为金融机构的优先服务对象;对金融机构信任度更高的居民越容易和金融机构就基金投资进行合作;居民在基金方面更高的社会互动程度降低了金融机构在提供基金投资服务时的成本,因而在基金方面的金融排斥概率越低;金融机构倾向于回避那些面临着较强的信贷约束进而资金有限的居民;居民对未来收入水平越乐观,金融机构就越容易向他们销售基金产品;居民获得基金方面的金融服务需要以居民的银行存款为基础,因而金融机构更愿意把基金产品提供给那些在储蓄方面没有被排斥的居民。其他解释变量对居民在基金方面的金融排斥可能性没有显著的解释力,这也可以从引言提及的理论预期中找到相应解释。与表3相似,表4汇报了居民在保险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因素的五组回,归结果。显著且稳健的发现包括:年纪越小、离婚、较短的受教育年限、是少数民族、家庭中更少的未成年人数、家庭中更少的老年人数、没有家庭房产、较少的家庭资产、对政府监管较低的信任度、在保险方面较低的社会互动程度、较强的信贷约束、对经济形势更加乐观的态度、在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都会增加居民在保险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其它因素不变:居民的年龄减少1岁、婚姻状况从已婚变为离婚、受教育年限减少1年、从汉族变为少数民族、家庭中未成年人减少1个、家庭中老人减少1个、从有家庭房产变为没有家庭房产、家庭资产减少1万元、对政府监管的信任度减少1个单位、从周围的人现在大多有保险变为大多没有保险、信贷约束增加1个单位、对经济形势的乐观程度增加1个单位、从储蓄方面没有金融排斥变为受到金融排斥,他们在保险方面的金融排斥可能性会至少增加0.21%、19.03%、1.39%、11.23%、10.66%、6.48%、8.97%、0.02%、0.47%、17.11%、7.12%、5.80%、32.54%.
与表2和3类似,表4的回归发现也都可以对应着引言中给出的理论预期:年龄的增加会提高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因此金融机构提供保险产品时青睐年龄大的居民;离婚对居民家庭财富产生负面冲击,所以金融机构会尽量避免因离婚而导致购买保险资金缺乏的居民;金融机构倾向于忽视那些受教育程度低进而缺乏保险相关知识的居民;少数民族居民在保险产品方面可能受到更多的金融机构歧视;家庭中更少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可能降低了家庭购买保险的必要,因而金融机构提供给这种家庭的保险产品更少;金融机构会忽视那些缺乏房产进而缺乏资金实力和保险意愿的居民;家庭资产越多的居民可能越需要购买保险来提供保障,所以会成为金融机构的优先服务对象;对政府监管信任度更高的居民越容易和金融机构就保险销售进行合作;金融机构在提供保险产品时会选择那些在保险方面社会互动程度更高进而服务成本越低的居民;居民较强的信贷约束制约了他们可以购买保险产品的资金基础,因而金融机构会较少销售给这些居民保险产品;金融机构在销售给对经济形势持悲观看法进而对抵御悲观情形的保险需求更大的居民时更加容易;居民的银行存款构成了其获得保险服务的基础,所以金融机构倾向于向那些没有在储蓄方面出现金融排斥的居民提供保险产品。居民的宗教信仰降低了他们在保险方面的金融排斥可能性,这可能是宗教信仰关于未来和来世的看法增加了居民对于风险的防范意识,因而金融机构更加容易向他们提供保险产品,但有关发现并不稳健。其他解释变量对居民在保险方面的金融排斥可能性没有显著的解释力,这也可以从引言提及的理论预期中找到相应解释。
与表3和4相似,表5汇报了居民在贷款方面的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因素的五组回归结果。显著且稳健的发现包括:已婚、家庭中更少的未成年人数、没有家庭房产、较少的家庭资产、对司法机构较低的信任度、更强的风险规避程度、对经济形势更加悲观的态度、在储蓄方面的金融排斥都会增加居民在保险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可能性,而居民的家庭平均月收入对其贷款方面的金融排斥可能性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 型影响,转折点在15至19.3万元之间,但家庭平均月收入上升的总体影响大致是负的。具体而言,其它因素不变:居民的婚姻状况从单身变为已婚、家庭中未成年人数减少1个、从有家庭房产变为没有家庭房产、家庭资产减少1万元、对司法机构的信任程度减少1个单位、风险规避程度增加0.00010、对经济形势的悲观程度增加1个单位、从储蓄方面没有金融排斥变为受到金融排斥,他们在贷款方面的金融排斥可能性会至少增加54.65%、9.13%、8.43%、0.01%、6.08%、1.59%、6.43%、16.97%.
同样,这些回归发现也都可以对应着引言中给出的理论预期:婚姻契约的维护可能降低了已婚居民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金融机构在提供贷款服务时会优先考虑未婚居民;家庭中未成年人数的减少可能减少了家庭支出压力,而金融机构可能倾向于向家庭支出压力大的居民提供贷款;金融机构更愿意将贷款提供给有家庭房产可用于抵押的居民;更多的家庭资产意味着居民还贷能力越强,因而是首选的贷款客户;居民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越低,金融机构越难以和他们就贷款服务进行合作;金融机构很难将增加家庭经济风险的贷款产品提供给厌恶风险的居民;居民对经济形势越悲观,就越不愿意增加未来开支和承担更多风险,这样金融机构会减少贷款给他们;居民的银行存款构成了其获得贷款方面的金融服务的基础,所以金融机构倾向于向那些没有在储蓄方面出现金融排斥的居民提供贷款。与已婚居民相比,离婚居民在贷款方面更可能受到金融排斥,这可能反映了离婚对财富的负面冲击降低了金融机构提供给他们贷款的意愿,但有关发现并不稳健。其他解释变量对居民在贷款方面的金融排斥可能性没有显著的解释力,这也可以从引言提及的理论预期中找到相应解释。
为了检验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多种尝试。首先,我们分别使用了受访者被推测为户主的子样本(样本量为437)和剩余的子样本(样本量为725)进行了分析,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而且在总样本回归中我们还引入了区分两种子样本的虚拟变量与各解释变量的乘积,这些乘积变量并不显著,也不影响主要的回归结果。其次,考虑到住房信贷与其他信贷可能不同的成因,即大部分居民购买住房可能必须依靠按揭贷款,我们构造了去掉住房贷款信息后的新的贷款方面的金融排斥变量,回归结果没有显著变化。第三,我们构造了一个综合的金融排斥变量,当居民面临着储蓄、基金、保险或贷款方面任何一种金融排斥时赋值为1,反之为0.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显著影响保持一致。第四,我们采用了过去一年内居民平均月收入或居民家庭月结余来分别测量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平方项,采用了基于居民在投资时的乐观和悲观看法构造的居民乐观和悲观变量来测度居民的乐观程度,引入了以居民投资期限测度的规划期限、以参加无偿献血次数测度的社会资本水平以及以每周工作时间测度的闲暇时间作为其金融排斥状况的额外解释变量,还考虑了居民对储蓄、基金、保险的了解程度对其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这些尝试都没有显著改变前文汇报的回归结果。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李涛,王海港;中国农业大学,王志芳;中国人民大学,谭松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