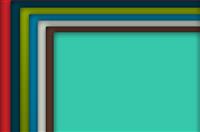
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了不起,20世纪70年代末率先搞土地承包,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时隔40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到底有何深意?近来多家媒体希望我作解读。研究三农问题多年,当然有自己的思考,就写出来与读者交流吧。
先提一个问题:中央为何30年前未提乡村振兴战略?而且10年前也未提?不知读者怎么看,我的看法,是那时候还不到振兴乡村的时机。众所周知,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三农”,然而解决三农问题却功夫在诗外,需要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8亿人口在农村,人均耕地不足1.5亩。试想,在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背景下,如果不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将部分农民转移进城市,农民怎可能致富呢?
经济发展既然有阶段,当然就要尊重发展阶段的规律。300多年前,威廉·配第在研究当时英国农民、工人与船员收入后发现:论从业收入,从事农业不如从事工业,从事工业不如从事商业。20世纪40年代克拉克对配第这一发现作了验证,并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说,由于第三产业收入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收入又高于第一产业,故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后来刘易斯提出“城乡二元经济模型”,也得出结论说:工业化初期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市。
中国近30年的经验,完全印证了上面的推断。据最新入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8亿。这是说,过去8亿农村人口中,已有2.2亿转移进了城市,而且这2.2亿人口都是青壮劳动力。我想问读者,当一个国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的时候,你觉得有可能振兴乡村吗?显然不可能。这样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之前中央为何不提“乡村振兴战略”了。
以前不提而为何现在可以提?我的解释,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中后期,农村劳动力流向已开始发生改变。何以作此判断?请读者注意2008年这个节点,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有2000万农民工下岗返乡。而据有关调研报告称,这2000万人后来大多留在农村就业创业,并没有再进城市。事实上,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频频出现招工难就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说我自己的观察。不久前我去贵州六盘水调研,看到有不少企业家到乡村投资。这些企业家之前其实也是农民,进城打工学到技术后自己办了企业。我不解的是,他们为何不留在城市而要回到乡村投资?我分别访问过其中几位,他们的回答不约而同,皆说现在投资工业已不如投资农业赚钱。这回答我相信是真话。随着工业投资密度不断加大,利润率肯定会下降。经济学所谓“投资收益递减规律”,说的就是这道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企业家到农村办企业会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从选择角度看,这无疑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比如过去农民种地年收入为5000元,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就是5000元。假定当地农民年收入增加到20000元,则机会成本就上升为20000元。再有,进城务工不仅背井离乡,而且生活费用也高,假定一年房租和孩子寄读费是20000元,这样务工收入若达不到40000元,进城务工就得不偿失。今天劳动力流动出现“刘易斯拐点”,原因即在于此。
另外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我看到的资料,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到70年代,欧洲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俄罗斯等国也相继出现这种趋势。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6%,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势而为,适逢其时。
以上说的是战略背景,下面再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究竟有何深意?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字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此,中央又提出了四大举措:即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村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或许有人说,以上举措在以前的中央文件中皆能找到,新话并不多。可我要提点的是,十九大提出的举措与之前的举措虽相同,但含义却不同。比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中央以前主要是对农民讲,是给农民吃定心丸;而中央今天重申,一方面是对农民讲,同时也是对城市的企业家讲,目的是鼓励企业家投资农业,大胆吸收农民承包地入股,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据此分析,我们便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深意。从近期看,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决胜全面小康当然需要振兴乡村。从长远看,则是引导、支持城市资本下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通过振兴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后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如果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中,后果会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