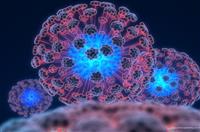核心提示:在近代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作为历史性的思维框架依然左右着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只是在西潮的冲击下,二者在近代的氛围中产生了历史的变异,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主义蜕变为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以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夷夏之辨异化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种族论。而在极端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又提供了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新天下主义生长的历史可能性,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和交叉镶嵌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
摘要:在近代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作为历史性的思维框架依然左右着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只是在西潮的冲击下,二者在近代的氛围中产生了历史的变异,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主义蜕变为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以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夷夏之辨异化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种族论。而在极端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又提供了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新天下主义生长的历史可能性,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和交叉镶嵌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天下主义;夷夏之辨;文明论;种族论
在讨论古代中国的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这样的悖论性现象:一方面,中国具有帝国的气魄和视野,以全人类的天下意识来包容异族、威慑四方;另一方面,中原民族又有华夏中心主义心态,傲视四周的“蛮夷狄戎”。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恰恰构成了古代中国自我认同的两面性,离开了任何一面都无法理解其真正的内涵。那么,到了近代社会,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是否从此销声匿迹了呢?本文将从这对中国传统的核心观念出发,着重研究它们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变异——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主义是如何蜕变为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而以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夷夏之辨又如何异化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种族论。而在极端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又如何为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新天下主义提供了生长的历史可能性。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和交叉镶嵌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怎么样的深刻影响。
一 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
何谓天下?在中国文化当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像。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①]。作为价值体的天下,乃是一组体现了自然、社会和人类至真至善至美之道的价值,体现在人间秩序,乃是一套文明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②]。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礼仪秩序,不仅适用于一朝一国,而且是永恒的、绝对的仁义价值与礼乐规范。天下之价值来自于超越的天道,而从西周开始,天就被认为是内在地具有德性的,天道与人道是相通,天意通过民意而表达,天下也就因此拥有了既是超越的、又是世俗的伦理价值。
天下的另一个含义是地理意义上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像。天下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第一个是内圈,是皇帝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区域;第二个是中圈,是中国的周边,是帝国通过朝贡和册封制度加以控制的番属;第三个是外圈,是中华文明无法企及的、陌生的蛮夷之地。严格说起来,所谓的天下,指的是第一和第二个圈,外圈乃是化外之地。正如甘怀真所分析的那样:“天下是由中国以及与中国有朝贡、册封关系的域外国家所建构的政治系统”,“而这个天下也是‘汉宇文化圈”’[③]。这个空间意义上的天下观念,始于西周,完成于隋唐,形成了以中原九州为中心、向东亚乃至世界呈同心圆辐射的结构。必须指出的是,古代中国的天下空间,不像现代的世界各国版图那样固定不变,内圈与外圈之间、化内之地与化外之地,经常处于弹性的变动之中,即所谓中心清晰,边缘模糊。在战国时代,天下只是方圆三千里的九州,而到了汉代,天下则成为包含“夷狄”在内、方圆万里的帝国辽阔的疆域了[④]。
价值意义上的天下与空间意义上的天下具有同一性,即表现出超越种族、宗族、地域和国家的普世文明特征,只要接受了发源于中原的中华文明的那套礼仪典章制度,就可以成为天下中的一个部分,只是中心与边缘的不同罢了,但服从的都是同一个文明尺度和价值,那就是天下主义。许悼云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表述:
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中国自以为是这一文明的首善之区,文明之所寄托。于是“天下”是一个无远弗界的同心圆,一层一层地开花,推向未开化,中国自诩为文明中心,遂建构了中国与四邻的朝贡制,以及与内部边区的赐封、羁縻、土司诸种制度。[⑤]
普天之下毕竞也有教化的阳光无法普照之处,于是与天下主义伴随而生的,乃是另一个概念:夷夏之辨。何为华夏、何为夷狄?在古代中国并非一种族性概念,乃是一文明性分野。夷夏之间,所区别的依然是与天下之价值相联系的文明之有无。宫崎市定如此区别华与夷的不同:
“武”的有无,不能决定。但“文”的有无,却可确定华与夷的区别。换句话说“文”只存在于“华”之中,同时,正是由于有“文”,“华’,才“得以成为“华”。[⑥]
中国历代一直有明确的夷夏之辨、胡华之别,华夏是“我者”,夷狄、胡人是“他者”,然而彼此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可变动和转换,夷入华则华之,华入夷则夷之。夷夏之间,虽然有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但最大的不同乃是是否有中华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华夏的骄做与自大,并非血缘性、种族性的,而是一种文明的做慢,而对夷狄的鄙视,也同样如此。晚清的郭嵩焘认为:“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而言及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戎狄”[⑦]。反之,如果胡人或者夷狄臣服于中原的礼乐政教,那就被接纳为天下中国之一员,哪怕成为统治者和皇帝,在历史中也并非个案。
天下是绝对的,但夷夏却是相对的,所需要辩认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己。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因此,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在中国历史中为常态,也是中华帝国文明扩张的使命所在。如果说华夏是“我者”,夷狄是“他者”的话,诚如许悼云先生所说: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⑧]”。“天下”有绝对的敌人,那就是没有或者拒绝接受中华文明教化的夷狄,因此需要夷夏之辨。但作为具体的夷夏,却都是相对的,可以教化,化“他者”为“我者’。“天下”是普世的、绝对的,而夷夏却是相对的、历史性的。
由于中原的华夏民族没有绝对的种族界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融合了周边的蛮夷,化夷为华。历史上夷夏之间、胡人与汉人之间有四次大的融合: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明代和清朝[⑨]。在这些民族大迁徙、大融合过程之中,不仅蛮夷被汉化,也有汉人被胡化的反向过程。汉人本身是农耕民族,而胡人多为草原民族,农耕中国和草原中国经过六朝、隋唐和元清的双向融合,华夏文化己经渗透进许多胡人的文化,比如佛教原来就是外来的宗教,汉族的血统里面也掺杂了众多蛮夷的成份。所谓的天下主义,乃是一个不断的以夏变夷、化夷为夏的过程。夷夏之间,既是绝对的(有无礼乐教化),又是相对的(相互的融合与内化),随着每一次中原文化对外的扩张,华夏民族融合了原来的胡人,使得他们成为新的一员。钱穆先生指出,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扩张是不同的,罗马帝国是以军事为后盾向外扩张,但中华帝国却是以文化为中心将四边向内凝聚“中国人常把民族消融在人类观念里面,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⑩]。
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是理解古代中国认同的核心,二者互相镶嵌和包容,不能抽离了一面来理解另一面,这就像一个角币的两面,具有双重的性格。这双重性格在不同时代侧重点是不同的。宋之前从孔子到汉唐,重心落在天下主义,不太强调夷夏之分。汉唐是气吞山河的大帝国,有强大的中心吸引力,不仅“以夏变夷”,用中原文明改造蛮夷,而且“以夷变夏”,用异族的文化丰富华夏文明本身,使之变得更多元、更辽阔。唐朝的胡人可以在长安当大官,可以成为封疆大吏。一个大帝国在真正强大崛起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不在乎夷夏之辨,更多表现出天下主义的胸怀。到了宋代,外患危机严峻,随时有亡国(王朝倾覆)的威胁,天下主义暂时行不通,遂突出夷夏之辨的另一面,更强调夷夏之间的不相容性与中原文化的主体性。从元到清,这条脉络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到王夫之那里产生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强烈认同。晚清以后,便接上了近代的种族民族主义。
但即使在宋代之后,夷夏之辨依然无法脱离天下主义而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夷夏之辨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存在。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内在渗透、相互镶嵌。天下主义是进攻利器,夷夏之辨乃防守之道。防守的终极目的,依然是要实现天下归仁的儒家天下理想。在古代中国,一个新的王朝是否合法,是否为汉族士大夫所认同,有两条标准:一条标准是夷夏之辨,另一条标准是天下主义。夷夏之辨是次要的标准,最重要的还是天下主义。非华夏的外族,既是绝对的敌人又是相对的敌人。之所以是绝对的敌人,乃是他们没有被文明教化过,代表了野蛮,是对中原文明的颠覆。之所以是相对的敌人,意味着只要蛮夷被中原文明所同化,就可以成为华夏天下的一员。即使是异族统治,汉族士大夫也可以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最终在意的不是亡国(汉人王朝),而是亡天下。
六朝隋唐之后,中国人不论从种族还是文化来说都不是纯粹的,且不说五胡乱华之后夷夏之间血缘混杂,即便是中原文明,也融合了外来文化。宋明理学就是被佛教夷化了的儒学,而佛教在中国也被汉化,从出世的佛陀变为在世的禅宗。中国的天下主义以中原文明为核心,把异端的、蛮夷的文化与种族包容进来,形成一个更大、更具开放性的华夏文明。这个华夏文明无法以种族、血脉、语言和历史的纯粹性来追溯。宋代虽然是一衰世,但中原民族的主体性也早己是多个民族和文化杂交后的主体性,夷夏之辨依然受到先秦而始的天下主义之规约。
古代中国的认同之所以博大,包容性强,中心清晰、边缘模糊,无法以近代的民族国家定位,乃是始终离不开天下意识。杜赞奇说:在中国历史中有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资源,一种是排他性的以汉族为中心的种族主义,另一种是包容性的以天下为价值的文化主义。这两套关于民族共同体的叙述,既互相分离又纠缠在一起[11]。天下主义是普世的,夷夏之辨是特殊的。对于古代中国而言,天下既是华夏的特殊主义,又是以华夏为中心的普世主义。普遍性(文化)与特殊性(华夏)融为一体,或者说普遍性的天下发端和存在于特殊性的华夏文化之中。只有到了近代之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华夏失去了普遍主义的位置,于是特殊的华夏与普遍的天下主义发生断裂,形成近代中国认同的深刻困境。
二 夷夏之辨向种族论的蜕变
在近代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作为历史性的思维框架依然左右着中国的思想家们,只是在西潮的冲击下,二者在近代的氛围中产生了历史的变异,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主义蜕变为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而以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夷夏之辨异化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种族论。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和交叉镶嵌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夷夏之辨在古代中国不仅是文化的、相对的,而且受到天下主义的绝对理想的制约,因此总是处于边缘性的位置。然而,到了晚清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一波又一波的西潮冲击之下,以儒家的礼教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发生了崩解,外来的西方列强携着枪炮的实力和文明的观念让古代的中国受尽屈辱,从此中国人失去了自信。于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抵抗性的民族主义意识油然产生,而它从古老的传统中所吸取的智慧,正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之防,由于其不再有天下主义的规约,古老的夷夏之辨化身为近代的族群民族主义,从边缘走向主流,成为从朝廷到士大夫的主流意识形态。
从夷夏之辨蜕变而来的族群民族主义有保守的、激进的两种不同的类型。所谓保守的民族主义,乃是晚清的传统士大夫,他们的敌人是西方的帝国列强和外来西学,在西方各种软硬实力压迫之下,强烈地守护中国本土传统,通过卫教试图保国。而激进的民族主义则表现为晚清革命党人的反满意识。这是一个通过族群动员推翻异族统治的政治策略,因为有夷夏之辨的历史记忆,族群动员威力无比,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最后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激进民族主义到1920年代之后转化为另一形式的排外性民族主义,即反帝的民族主义,新的蛮夷就是在中国与世界推行霸权的西方列强,激进的民族主义自此与保守的民族主义合流。
从夷夏之辨变异为族群民族主义,个中最关键的是种族意识的萌生。古代中国的种族意识一向很淡,真正具有强烈的汉族种族自觉的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但他的思想在清朝大部分时期都属于大逆不道的异端,对士林影响有限。姚大力指出:种族意识“其实它充其量不过是依附于王朝忠诚观念的一种‘伴生性的原民族’意识而己。一旦新的王朝巩固了它的统治秩序,这种‘伴生性的原民族’情绪很快就会大面积消退。”[12]而族群民族主义的真正出现,一定要等到晚清西方的种族观念引进中国并被普遍接受,方才‘可能成为风靡全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最早将西方的种族论引入中国的,根据松本真澄的研究,不是反满的革命派,而是将进化论介绍进来的严复[13]。严复在1895年的《原强》一文中,强调人类社会的竞争,最初是种与种竞争,然后为国与国竞争“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他认为世界上有4个种族:黄、白、褐、黑。中国的满、蒙、汉都是黄种,具有种族上的同一性和纯粹性,因为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是“文胜之国”,故“异族常受制于中国”,而非“异族制中国也”。然而,近代中国所遭遇的西洋民族,德智体皆胜于中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中国遂有了“亡国灭种”之虞[14]。
晚清影响最大的新思潮是严复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种族论正是伴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起来到中国,二者之间犹如孪生兄弟,有着内在的、无法切割的联系。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看来,人类社会竞争的基本单位就是种族,它赋予了种族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哪个民族在生存竞争中适合生存,是优胜者,它就是贵种,否则就是活该被淘汰的贱种。于是,晚清年间“种战”、“保种”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推动种族论传播最力的,仍属梁任公莫属。1898年,他在《清议报》创刊号上发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认为自大地初有生物,至于今日,数万年所相争的,一言而蔽之,争种族而己。种族之多,起初不可胜数,随着生存竞争,数目日渐减少,因为凭优胜劣败之公理,劣种之人,必为优种者所吞噬,直至灭种[15]。1902年,梁启超撰写《新史学》,将历史的基本单元看成是人种,所谓历史即是“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己”。在他看来,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有历史的,一种是没有历史的。世界上五大人种,黑种、红种和棕种皆是没有历史的,有历史的人种,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两种,最适合竞争[16],在此之前,梁启超对这一划分作了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解释:“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为之事,黄人无不能者。”[17]
纵观梁启超的种族言论,虽然也是一种新的夷夏之辨,但与传统的声音不同,他不再从文明的相对角度区分夷夏,而是转换为种族的绝对性。一部分人种是贱种,注定要在生存竞争中失败,而另一部分人种是贵种,将会最终赢得末来。文明可以转化夷夏,但种族却是天生的,命运不可改变。代替文明这一普遍性的,是另一种普遍性,乃是晚清所普遍认同的所谓公理:由进化论所带来的生存竞争。竞争面前种族平等,谁是通吃天下的赢家,谁被淘汰出局,似乎冥冥之中都有一个种族的宿命。
那么,作为黄种的中国前途如何呢?梁启超乐观地相信,在20世纪之中,“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其理由是因为中国具有四大优势:有自治传统、冒险独立、思想发达、人多地广[18]。纠缠在梁启超内心的,是一种在白种人面前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心结,一方面以白种人的生物学和文化学的标准即是否适合竞争这一普遍性来自我衡景,另一方面又相信黄种终将战胜白种统治全世界。这种于今看来属于“政治不正确”的种族优劣论,在晚清却不仅仅属于梁任公个人,而是弥漫在中国士大夫群体之中的普遍思潮,为各家各派所信奉[19]。比如革命派阵营的刘师培也将近代中国的亡国灭种危机归结为亚种劣而欧种优: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种族既殊,竞争自起,其争而独存者,必种之最良者也。中国当夷族入主之时,夷种劣而汉种优,故有亡国而无亡种。当西人东渐之后,亚种劣而欧优,故忧亡种。[20]
在晚清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大论战中,虽然双方意见分歧,但是背后都共享同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是否适合竞争这一新的普遍性来裁断一切;同时又都从种族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相信汉族是最适合进化的民族,区别只是在于如何看待满人:梁启超、杨度他们持的是大中华主义立场,更重视黄种和白种的“外竞”,将满汉视为同一个种族下的不同民族,而章太炎、刘师培、邹容等革命派承继明末王夫之的汉民族意识,将满汉视为汉贼不两立的不同种族。在晚清广泛流传的《革命军》一书中,邹容将亚细亚的黄种分为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两个不同的人种,中国人种以汉族为中心,包括朝鲜、日本、安南、西藏等族的“昆仑山系统”,而满人、蒙古人以及西部的土耳其人则属于另一个“西伯利亚系统”。邹容以极富煽动力的笔调控诉满人对“吾黄汉民族”的种族压迫:
汉种汉种,不过为满洲人恭顺忠义之臣民,汉种汉种,又由满洲人介绍为欧美各国人之奴隶,吾宁使汉种亡尽杀绝死尽,而不愿共享盛世,歌舞河山,优游于满洲人之胯下![21]
革命派排满的理由,除了君主专制之外,便是与汉族本非一族,且非同国之人,因此汉人建立的国家,当将满人排除在外。近代的族群民族主义还得到了中国传统中的家国天下观念的有力支持。刘师培如是说:
孟子言国之本在家,而西人言社会学者亦以家族为国家之起源,谓民族之起源,起于公同之特性,而公同之特性,起于血统之相同。则所谓民族者,乃合数家族而成者也,同一民族即同一国家。此家族所由为国家之起源也。[22]
由家族而民族直至国家,血缘性的家族扩大为单一、同质化的国族,革命派所想像的近代民族国家乃是日本式的单一民族共同体。因此相对应,立宪派对国族的想像乃是立足于清代以来的多民族并存的现实,通过立宪,融合汉、满、蒙、藏、回五族为一中华民族。晚清年间对此有系统论述的,乃是杨度。他在《金铁主义说》中力证中华并非一地名,也非血统之种名,而是一文化之族名。今日之中华民族,除蒙、回、藏文化不同,语言各异而外,满、汉在文化上己经是同一民族。他明确表明:“民主立宪党所欲成之民族的国家,命之曰中华民国,则是言文化而不言血统,欲合满汉而共组织一民族的国家可以推知”[23]。
多位学者指出,杨度为“五族共和”思想的始作俑者,虽然他最初提出的是“五族君宪”的方案[24]。细读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可以发现在他的视野之中,五族并非真正的平等,而是有进化程度的差别。杨度深受由严复介绍进来的甑克思的人类社会野蛮—宗法—军国三阶段普遍进化图式的影响,认为在中华民族内部,汉族是最进化的民族,己经进入未发达的军国社会,为汉族同化的满族次之,而蒙、藏、回三族尚停留在宗法社会[25]。因此,要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国族,首先是满、汉平等,其次是同化蒙、藏、回,即以汉、满为中心,同化蒙、藏、回三个落后的民族,合五族于一族[26]。于此可见,无论是革命派的排满性的汉族共和国,还是立宪派的合五族于一族的多民族君宪国,都是以汉族为中心,不管是排斥还是同化异族,皆相信汉族在血统上最优,最为进化,在国内诸民族之中最具有竞争能力。辛亥革命之后,杨度的“五族君宪”方案迅速为革命党人吸纳和改造,形成“五族共和”的全国性共识,个中之重要原因,乃是革命派与立宪派都共享一个基本的预设,所谓“五族共和”就是以汉族为中心,同化与融合其他未开化的民族。根据松本真澄的研究,民国初年孙中山在各种场合谈到“五族共和”的时候,态度有微妙的差别,对汉人演讲时强调汉族在种族、竞争和文化上的优越感,需要同化和融合其他民族;而在会见蒙古王公和回教领袖时则表明民族自治和民族平等,参加民国对他们有好处。按照他的理想,民族自治只是最初的一个阶段,最后乃是要融合和同化各个民族,达到统一的、同一的中华民族[27]。
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方案表明解决了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争论,但这只是汉族知识分子内部分歧的终点,并没有得到满、蒙、藏、回其他四族的真正认同,从外蒙古王公的策划建国、西藏长期事实上的独立、乃至满洲国的建立、西部回教地区的分离倾向,都表明以汉族同化和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为解决方案的国族打造,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路程。一个多民族的国族打造,要比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困难得多,其不在于主流民族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少数族群对这一国族的认同程度。姚大力指出:“从表面上看,族裔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两者的极端主张似乎是正相反对的,然而事实上,它们很可能就是一回事。历史反复提醒我们,掩盖在国家民族主义外衣之下的,经常就是一国之内主体人群的族裔民族主义”[28]。从晚清打造国族至今,汉族与中华民族常常被划上等号,黄帝被想像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国族民族主义的背后遮蔽着一张族群民族主义的真实面孔。这种以单一族群为基础的国族建构注定是脆弱的,一旦国家发生政治危机,其他被压抑的少数族群就会发生反弹,制造分离的麻烦。苏联帝国的解体就是一个近例,国族认同的真正内涵在于内外两面,一面是国家内部的各多元民族和族群是否认同新的民族共同体,整合为多元一体的国族,另一面是对于国族外部“他者”的态度。当夷夏之辨到近代蜕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下的种族论,而天下主义的价值规范又失去的时候,极端的盲目排外便以反帝、反西方、反洋教、反洋人、反欧洲中心主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越是国族打造遭遇困境,内部四分五裂,越是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以强化自我,这种自我被掏空了的、只是以他者的存在而存在的国族认同,在近代中国只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符号,无法落实为中华民族的自觉实体。
三 文明论:逆向的天下主义
如同古代的夷夏之辨有天下主义的制约一样,当晚清之后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天下主义解体之后,一种新的天下主义出现了,这就是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
天下主义的实质乃在于普世的价值和文化,相信各个民族可以有各自的历史,但最终都会百川归海,为更高级的文化和制度所征服。晚清之后,当西洋文明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优越性来到中国,显示其新的文明力量的时候,中国的确面临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士大夫内部发生了分化,保守主义者严守夷夏大防的传统立场,以各种方式抵御西方文明,保卫中华文明的礼教。另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则清醒地意识到时势的变化,
开始接受西洋新文明。
一种外来新文明进入原来的文明母体,首先需要的是要在原来文明中获得合法性。有意思的是,如果说抵抗西洋的力量来自于夷夏之辨传统的话,那么接受西洋文明的理由却出自于天下主义,这就是“古己有之”论。王尔敏先生的研究表明,自龚自珍、魏源之后,最初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士大夫,将西洋的学术政教,皆视为中国固有之物,所学于西洋者,实合于“礼失求诸野”的古训。“古已有之”论,有两种表现形态,一为西学得中国古意,一说西学源出自中国[29]。
“中国古已有之”论秉承天下主义的传统,并不认为西洋文明有异于中国,中华学术政教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天下主义的视野之中,华夷的区别就是文野之分,文明只有一个,但寄托于何者身上,有变易的可能“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其中的“进”,并非地理和身份意义上的进入中国,最重要的是承认和采纳中国的政教理想,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王韬如此批评晚清时人中狭隘的以种族为标准的夷夏之辨:“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薄人哉?”[30]
这是天下主义视野中的夷夏观,“古己有之”论亦如此看待西洋的文明,并不以为异端,乃是以普世的价值尺度大度接受夷人之学术政教,并视为己出。可以如此认为,古已有之论,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文明论,它为传统的天下主义转型为近代文明论搭建了过渡的桥梁。
在神州本体的士大夫,对西洋文明只是隔岸的想像,而真正有机会漂洋过海到西洋考察的,所见所闻乃是一种真正的心灵冲击。作为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发现,西洋立国一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以往的辽、金蛮夷,截然不同。物质繁华不论,既论制度之优,统治者品德之良,也在中国的三代之上:“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31]
最识洋务的郭嵩焘在这里己经意识到,西洋所出现的文明,已经非中国古人的理想所能包容,它代表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夷夏之间,可互相转变,文明之担当者,当有变易。王尔敏先生发现,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流传着一种运会学说,认为历史是循环的,易理之发展,穷毕必返;五德终始,天命常在不同的朝代变易之中。这种循环论的运回学说,到了晚清又再度流行,面对西洋文明的崛起,相信这是天命的转移,西力东渐是天机地气,运回使然[32]。于是能够以天下主义的大度,坦然接受新的文明。到了这一步,“古已有之”论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传统的天下主义开始转向另一种天下主义,以西洋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
这种近代文明论,可以说是一种逆向的天下主义,其价值尺度不再以中国、而是以西洋为标准,夷夏之间变换了位置。从天下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的文明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当儒家的三代乌托邦和礼乐教化不适时宜,不再能代表人类的普世理想的时候,那么就需要一个新的天下宏图,新天下既代表了人类的德性价值,也有更合理的典章制度。礼失求诸野,于是天命就转移到了西洋那里,运回循环,华夏变成了蛮夷,而过去的蛮夷成为了新华夏,他们代表了新天下的真谛,这就是文明。
晚清的文明论是一种公认的、新的价值尺度,它来自欧洲和日本两位对中国影响巨大的思想家,一个是英国的甑克思(Edward Jenks),另一个是日本的福泽谕吉。甑克思是英国的法学教授,他本人在欧洲并没有什么名气,《社会通诠》 (A History of Polities)也只是一本阐述社会发展的通俗著作。然而,当严复在1903年将它翻译成中文之后,却在中国引起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立宪派和革命派还围绕该书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33]。一本简明的社会发展史小册子之所以在晚清影响如此巨大,原因无它,乃是当传统的天下主义所提供的历史观式微之后,中国士大夫迫切需要一个同样是普世的、适合全人类的进化通则和历史发展图式,而《社会通诠》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就是从蛮夷社会到宗法社会再到国家(军国)社会的历史进化过程。这一历史观与晚清流行的公羊三世说在结构上是对应的,都是直线型的一元进化历史观。在这一普遍的人类进化图式面前,西方处于进化的顶端,而中国尚处于从宗法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转化过程之中。
福泽谕吉作为日本明治维新最著名的思想家,在他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提出了文明论思想,为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文明是从欧洲传到亚洲的一个概念,文明是一种历史观,也是解释人类演化的历史过程和终极目标。文明在福泽谕吉那里,获得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文明是精神性的现象,表现为人类在德智方面的进步,文明随着德智的进步而发展。同时文明从拉丁语ci-vitas演变而来,含有“国”的意思,因此文明也有良好的国家体制的意思。文明作为全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和制度,它具有终极性的意义,整个人类的发展是从野蛮社会进化到半开化社会最后到达文明社会。福泽谕吉由此判定,美国与欧洲是最上等的文明国,日本、中国、土耳其等亚洲国家是半开化之国,而非洲、澳洲则是尚末开化的野蛮之国[34]。在日本的梁启超读到此书,深受启发,过去他相信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公羊三世说,如今的文明三阶段说不仅与三世说匹配,而且更有世界性的普遍价值。他在《文野三界之别》一文中说:
泰西学说,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正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35]
从此,文明这个概念迅速在神州流行,成为与“大同”同等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价值尺度,如果说“大同”还只是中华文明的一家境界的话,文明却是属于全世界的,文明是毋庸置疑的公理,是全球公认的普世价值,而且有一套可量化、可模仿的典章制度。只是这一新的天下主义之主体已经易位,从中国变为西方,因此激励起开明士大夫强烈的赶超意识,试图朝着新天下的目标,尽快从半开化的宗法社会,进化到文明的国家社会。到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这种文明论便发展成更为激进的全盘西化论,传统的天下主义以一种文化主体颠倒的世界主义形态表现出来。
在整个近代中国,文明论与种族论始终屡屡不绝,相互冲突和对立,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以中西种族不同、汉贼不两立的姿态抗拒西方文明,以中华的特殊性抵抗文明的普遍性,而五四的启蒙者则以普世的文明论批判中国传统,反思中国的国民性,检讨中华民族的种族和文化上的缺憾,两个阵营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然而,种族论与文明论又非绝对的对立,它们之间有共享的逻辑预设,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种族论与文明论,都相信历史进化论,不同的种族之间,按照进化的程度分为优劣,而进化的标准则是生存的竞争能力,其集中体现在德智体文明发展的程度上。所谓的进化,就是文明的进化,而种族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文明的竞争。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严复、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人,既是一个种族论者,又是一个文明论者。如同古代的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样,近代中国特殊的种族论与普世的文明论也同样互相镶嵌,互为理解背景框架,至于何者居于支配性的位置,完全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从族群、民族、国族,到种族和世界,相互之间的界限都是相对的、模糊的,以何者为他者,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自我认同。于是,汉族认同、大中华认同、大亚洲认同乃至世界的认同,都有可能发生在同一个思想家身上,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李大钊、毛泽东,都是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同时赞同大亚洲主义,又有解放全人类的世界主义情怀。他们学习西方文明乃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的新生和再起,又将为亚细亚提供抵抗西方的典范,为世界展示新的东方文明。1917年,李大钊先后撰写《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篇文章,从亚细亚和世界的角度思考中华民族的问题。他说,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西洋文明乃掠夺之文明,而高举亚细亚的旗帜而与之抗拒,乃当然之反响。“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国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36]从世界的背景思考亚细亚的命运,又从亚细亚的命运中思考中华民族的重要位置,这种思维既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显然承继了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的双重传统。在近代中国的大思想家里面,很少有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或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总是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里面思考中国的问题,同时试图以中国文明的复兴去拯救全世界。
传统的夷夏之辨和天下主义发展到近代所出现的两种极端形态:种族论和文明论虽然影响巨大,但它们却无法回应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打造一个与全球文明接轨的民族国家,既保持中国自身的文化认同,又具有近代的文明价值和制度。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种族论虽然现成地用中国特殊的种族与历史建构国族的“我者”,但这样的“我者”却以排除“他者”的文明为前提,具有“自我幽闭症”性格。而以西方为典范的文明论尽管有可能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但在获得了“近代”的同时,却失去了“我者”的主体性,无法建立自身的国族认同。在古代中国,因为天下文明就是以华夏为中心的文明,普世的天下建立在特殊的华夏之中,因而即便政权是异族建立的,在文化上依然不会发生“我者”认同的困境。然而,到了近代中国,普世的文明与特殊的华夏发生了断裂,天下不再是“我者”的天下,而华夏也失去了文明的优越感,在这一困境下,天下与华夏、近代与中国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使得什么是近代中国的认同这个问题真正地凸显出来,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
于是,在种族论与文明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个极端之间,出现了两种温和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与新天下主义。
所谓温和的民族主义,就是类似德国赫尔德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其有着世界主义的背景,绝不排斥世界的主流文明,同时又追求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因为是文化的,而不是种族的,因而是开放的,也是和平的。在近代中国,这种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正是陈寅恪所倡导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37]。这是宋以后民族主体性意识的健康版传承,是夷夏之辨与天下主义互相镶嵌的历史传统,它从晚清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开始,有一条清晰的思想史脉络:杜亚泉、梁漱溟、学衡派和新儒家,也被张君劢这样的自由民族主义者引为同调。
所谓温和的世界主义,乃是一种新天下主义。它不以中西为沟壑、古今为壁垒,而是追求全人类的普世文明。世界主义看起来似乎是反民族主义的,但其背后又有一种最宽阔的民族主义胸怀,即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胡适先生说过:“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38]。盲目排外指的是刚性的、原教旨的种族主义,拥护本国固有文化民族文化不一定排外,但强调的是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体性。而民族国家的建构,乃是一种非民族的民族主义表现,试图用全人类的文明(也包括中国自身的文明)打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就是从五四以后出现的新天下主义。
在近代中国,种族论和文明论作为两个极端,总是发生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但文化民族主义与新天下主义之间却能够建立良好的互动,它们都有世界主义的胸怀,同时又有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意识,虽然一个强调中国本位,另一个突出普世文明,但都不以排除对方为自己的前提。它们继承了古代中国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的辩证传统,在普世的天下视野里面追求中国文化自身的定位和认同,在普遍与特殊的融合之中建构“我者”的主体性,同时不断地将“他者”文明的优秀成份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新天下主义追求的是“好的”文明,而文化民族主义拥抱的是“我们的”文化,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将他人“好的”文明转化为“我们的”文化,
成为民族主体性的一部分;而将“我们的”文化放在世界视野之中,上升为普世文明,让它从特殊走向普遍,成为全球普世之“好”?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提供了将普遍性融入特殊性、从本土文化上升为普世文明的智慧。而它们之间的断裂产生了近代中国西方文明论和狭隘种族论的两种极端的变异。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回新天下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中道之中,将“好的”文明落实在“我们的”文化之中,而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世界“好的”普世文明。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7BZSO44)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1JJD770021) 的中期成果。本文初稿承蒙杨国强、赵刚、黄兴涛、刘擎、任锋等先生阅读指教,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①][美]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
[③] 甘怀真:《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载甘怀真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第26—27页。
[④] 参见[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5页。
[⑤]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北京:三联书店,2010 年,第20页。
[⑥][日]宫崎市定:《中国文化的本质》,载《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04页。
[⑦] 《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 年,第202页。
[⑧]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0页。
[⑨] 详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2页。
[⑩] 同上书,第132页。
[11] 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74页。
[12] 黄晓峰:《姚大力谈民族关系和中国认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2月4日。
[13] 参见[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 1945 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
[14] 参见严复:《原强》,载刘梦溪主编:《严复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540—551页。
[15] 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51页。
[16]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41—746页。
[17] 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00页。
[18] 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259—262页。
[19] 关于近代中国种族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参见[荷]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载《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21] 邹容:《革命军》,载《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3页。
[22] 刘师培:《伦理教科书》,载《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23]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
[24] 参见[日]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 年第5期; 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北大法律评论》11 卷2辑,2010年。
[25]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258页。
[26]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301页。
[27] 参见[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 1945 年的“民族论”为中心》第2章第1节。
[28] 黄晓峰:《姚大力谈民族关系和中国认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2月4日。
[29] 参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3页;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6—59页。
[3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
[31] 参见并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13章《西方文明对郭嵩焘的影响》,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225、215页。
[32] 参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72页。
[33] 关于《社会通诠》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影响,参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4] 参见[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9—41 页,另参见[日]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陈玮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35页。
[35] 梁启超:《文野三界之别》,《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40页。
[36] 参见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载《李大钊全集》第2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493、662—663页。
[37] 陈寅恪:《审查报告三》,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页。
[38]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