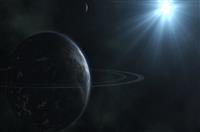(吴万伟 译)
早在1752年,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用两条雪松树枝制作了风筝,扔向黑压压的乌云要吸收闪电的火光。他后来写到,他在研究关于大自然的理论,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他也担心失败和大众的嘲笑,这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次放风筝只告诉了儿子,但是他并没有面对意识形态上的或者来自经济上的敌意和反对。比如蜡烛制造者,面对电灯泡时代到来肯定损失巨大的前景,并没有想方设法要破坏这个结果的信誉。相反,政治和文化环境奖励他的冒险精神,让他成为新生的国家里第一位科学名人。
相反,这些年,科学实验不管手头进行的是什么实验,大脑基因排列图,探索干细胞,或者研究极地冰盖的融化点等好像都处在一个几乎冷酷无情的争吵气候下。科学发现的前景好像让拥有根深蒂固偏见的党徒不是感到兴奋,而是感到担心。2006年的大众民主好像不是诚实的科学的恩惠,反而成为障碍。
热情信徒分为两大类别:简单地说,就是为理论家(The Ideologues)和大企业家群体(The Big-Money Crowd)。
热情信徒横跨从宗教右派到新左派的整个政治光谱。前者推动大学在生物学课堂上讲授伪科学“智慧设计”;后者拒绝支持生物学家严肃对待男女在数学和语言上的能力差异的观点。任何一方都应该遭到在电影《义海雄风》(A Few Good Men)中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扮演的海军上校(Marine Col. Jessep)在法庭上的痛斥。担任军事法庭律师的尼克尔森嘲弄地问年轻的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你想知道答案?”
“我要知道真相”。
“你承受不了真相”。
对于大企业家群体来说,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化石燃料行业任性地不愿意承认“让人为难的真相”—全球变暖—正如科学狂热者戈尔(Al Gore)在他的同名新电影中说的那样。和热情信徒不同,这些冷静理性的人能够对付真相,这是隐藏在寓言或者被歪曲下的底线。当然,真正的失败者是地球。
这种让人遗憾的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这真是说来话长啊。轨道开始于美国缔造者时期的启蒙时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随着美国的民主成熟而成熟,但是接着就开始遭受来自1960年后的文化战争和金钱推动的政治中日益庞大的企业利益连续不断的攻击。不过现代的专业研究者科学家们也决不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如今,科学家越来越成为热情信徒和自私自利的人,依赖政府拨款,大部分是居住在蓝色美国的居民。
尽管人们可能忍不住希望当今的冲突和争论还快就会过去,但是实际上恐怕正好相反。因为,首先,处在当今许多战场中心的生物技术革命本身正处于婴儿阶段,某些政治人物和法官拥护和支持这个观点,既政治中的金钱同样值得法律保护,因为言论能继续滋养这个或那个利益受到威胁的行业继续诋毁科学。
因此我们面临的争吵时代才刚刚开头,而处于危险的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更严重的是,过去曾经被认为建立在启蒙运动基础上,具有自由派传统(没有任何讽刺味道)的开放性社会,如今听起来却非常奇怪,让人匪夷所思。
社会批评家麦克斯•勒纳(Max Lerner)在1957年的著作《美国文明》(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中说“正是自由派智慧传统让美国的价值观典型地体现出来。”为了宣传其观点,这个布兰迪斯(Brandeis)大学教授像所有该传统的记录者做的那样,乞灵于比富兰克林更有成就的启蒙者大名人杰斐逊。他不仅是总统,还是个科学家,发明家,建筑师,音乐家,律师,语言学家,农夫,政治哲学家。杰斐逊说“地球属于活着的人”,强调了这个宏大的主题,勒纳写到,“自由主义因此得以出现。它的信条是追求进步,它的心态是乐观主义,它对人类本性的观点是理性主义者的,和容易变化的。”
勒纳解释说自由派传统不是碰巧建立在相信科学,使用理性工具(tools of reason)解决人类问题。虽然美国在关键的方面和旧世界,和欧洲分开了,但是在自由派传统上,代表了美国对欧洲最宝贵的遗产和礼物---启蒙运动的成功修改。这场启蒙运动出现于17世纪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
启蒙运动就是不仅在科学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不受妨碍的探索精神。这个时代的巨人如洛克,牛顿,伏尔泰都明白他们是共同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伏尔泰在1727年参加牛顿的葬礼上说“牛顿看到也让人们看到了真理,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设想当成真理。”
美国科学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在19世纪末到来,当时美国正进行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美国还欢迎不辞辛苦来到美国的移民,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为美国提供了聪明的后代。在这方面典型的人物是1904年出生于德国犹太人家庭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在全球范围内,科学家很快被作为新型的英雄被庆祝标志着承诺理性,繁荣,和社会英才统治(social meritocracy)时代的复兴。”作家凯•伯德(Kai Bird)和马丁•舍温(Martin J. Sherwin)在最近出版的奥本海默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的开头说。在美国,改革运动在挑战以往的秩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使用白宫的霸道讲坛提出好政府和科学一致,应用技术能够形成一个开明的新进步时代。
奥本海默上过哈佛大学,在欧洲学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后来又负责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他亲密地拥抱古典自由派传统作为自己的信条。1950年,他在年度“西屋奖学金”(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获奖者发表演讲。5年后作为他的书《开放的心灵》(The Open Mind)的一部分出版,题目是“科学的鼓舞”。奥本海默的谈话详细阐明了杰斐逊1799年写给询问科学研究的作用的年轻人的信。
杰斐逊的信用简短回忆学习代数的过程,然后转向主要的观点:科学是战胜专制政治和“封建野蛮”(feudal barbarisms)的工具,感谢苍天美国人的思想已经非常开放了,已经没有办法从对科学的承诺中退却了。”
从杰斐逊的观点谈起,奥本海默告诉学生“在科学中没有教条存在的空间。科学家能够自由地提出任何问题,怀疑任何假设,去寻找证据,去改正错误。我们自己的政治生活取决于开放性。”
但是光线已经开始暗淡下来了。奥本海默将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作为麦卡锡式的猎巫(witch-hunt)的结果,他的政府安全项目被撤消,他拥抱的美国缔造者的古典自由派精神传统遭受到围攻。
来自文化左派的攻击
1978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一个抗议者往哈佛世界著名的昆虫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的头上浇了一杯水。他的专业就是研究蚂蚁,该歹徒的同伙谴责威尔逊通过研究给予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种族屠杀提供了营养。
威尔逊的罪恶在于他创立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他定义是新达尔文主义延伸进入社会行为和动物社会的研究。“人类是这个分析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不仅是生物原则的外在表现而且是对生物原则的顺从。连续不断的细致入微的形式表现出政治不正确的观点的例子让左派大为光火。在他的书《论人性》(On Human Nature)中关于《性》一章中,威尔逊写到,人和多数动物物种一样,“让雄性更加具有进攻性,急躁,变化无常,不加区别,而在理论上“雌性腼腆害羞更有利,她要确保雄性拥有最好的基因才愿意就范。”
对于人类是否“天生具有进攻性”这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他说“答案是肯定的”。在《纽约书评》中威尔逊被攻击要恢复导致纳粹德国建立毒气室的优生学政策的理论基础。
左派对社会生物学的歇斯底里攻击---你可能注意到了毒气室没有在美国出现---是运动开头的缓解药。虽然偶尔退却了,但是往往以更强大的声势再次出现。就在去年,左派挥动手臂攻击启蒙堡垒的哈佛大学,其座右铭真理(Veritas拉丁文),愤怒的教授们要把校长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赶下台,部分原因就是他不适当的观点,数学水平可能与性别特征有关。
弗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和《生物学和哲学》杂志创办人迈克尔•鲁斯(Michael Ruse)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认为萨莫斯没有真的说什么哈佛生物系的多数人不相信的话。我们有来自右派的警察国家心态,同时也有来自左派的警察国家心态。”
考虑到生物学“没有达到确切结论,鲁斯提出了将来引起越发激烈的争论的可能性。比如,科学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中国人是否天生比我们聪明?”这确实听起来有挑衅的味道,但是随着科学家深入研究大脑,他们企图改变可能成为种族主义者饲料的清楚的研究结果是有道理的吗?对于坚定的种族主义者来说,从科学上得来的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饲料。如果大众的理性这么容易被改变的话,古典自由派的传统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尽管有左派的焦虑,事实上,前沿的生物学没有全部支持许多人认为的人类倒退的画面。对于性身份定位的科学研究的趋势似乎显示,正如同性恋权利团体主张的,同性恋有生物学的基础,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文化选择或者倾向。数学天才更多的可能是男性的研究同样也发现女性在语言上的天赋更大。
科学并不决定社会构造的方式,但是它可以提供建议,哪些方式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因此,虽然左派不想听这些,进入初级学校教育的人可能不得不承认女孩子一般比男孩更容易安静地坐着。谁想要更多休息时间呢?
来自文化右派的攻击
当然,不仅左派抓住现代生物学不放,偶尔让达尔文及其同代人处在攻击的靶子。右派,尤其是宗教上的右派攻击生物学更是个古老的行业,这至少可以追溯到1925年“猴子审判”(monkey trial)案件时期。当时一个高中教师约翰•斯克普斯(John T. Scopes)被控违反田纳西州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律。
尽管斯克普斯在审判中被判有罪,进化论仍然成为美国科学课程的支柱,因为科学家进行的数不清的实验确认了达尔文对于地球上生命进化包括人类生活是被竞争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基因选择的尝试错误(trial-and-error)的中心观点。因此,有一段时间好像斯克普斯风波代表了美国反对现代圣经地带者(Bible Belters)的最后一次喘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世俗为主导的左派在1960年代发动的针对宗教右派的文化战争反对起源于没有上帝的时代的让人恐惧的衰落。
这次,宗教理论家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试图让公立学校在科学课程上讲授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作为进化论的替代品。问题是“智慧设计不是科学”正如布什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约翰•琼斯(John E. Jones III),在去年12月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Harrisburg, Pa.)做出的裁决。琼斯在解释为什么多佛区学区委员会(Dover Area School Board)要求学生在9年级生物学课堂上讲授智慧设计是表现“让人惊讶的无知”,说“智慧设计违反了几百年来科学的基础,挑起和允许超自然的因果关系。”
琼斯根据作为“上帝造人说重新包装成为智慧设计破坏了宪法上教堂和国家分离的原则,因为它是宗教观点的产物,而排除了多佛区学区委员会的要求。他本来可以狭隘地判决,可他根据牛顿时代现代科学方法起源的个别辅导方式,准许提供个别辅导。他的裁决非常清楚说明智慧设计不是简单地表达对进化论的敌意,它们实际上是排斥科学的工作和自从达尔文在1859年《物种起源》以来科学家们提出的证据。为了试图把智慧设计包装成为科学,智慧设计的鼓吹者在抛弃科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高程度的智慧傲慢。
由于他的判决,琼斯被保守派宗教事业的长期积极支持者施拉芙莱(Phyllis Schlafly)指控与“无神论进化论者”沆瀣一气,
而且背叛在2000年投票支持布什的“千百万福音派教徒”,正是布什提名他成为联邦法官的。在他的裁决中,琼斯“用匕首刺进了和他跳舞的人脊背。”施拉芙莱在《科普利新闻》(Copley News Service)专栏上大肆攻击琼斯。
智慧设计运动或许不会因为琼斯的裁决而消失。但是努力要否认进化论的科学可靠性的努力肯定不会绝迹。智慧设计背后的力量正在重新聚集。当然,没有人被强迫接受进化论,或者在这点上像接受水在正常气压下100摄氏度沸腾的观点。但是,如施拉芙莱在专栏中暗示的,用大众民主来决定什么是可以信赖的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吗?
企业的攻击
当大烟草(Big Tobacco)遭遇大量科学证据确认吸烟危害的医学警告时,布朗威廉森公司(the Brown and Williamson Co.)开始搅混水,通过创造虚假的科学争议的表象。在1960年著名的公司内部记录里宣布说“怀疑是我们的产品”。
那个备忘录这些天大出风头,多亏化石燃料行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割游戏策略(stall-game tactics)的批评家所推动。正如一个批评家科学作家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注意到的,1990年代后期美国石油研究院准备了一个关于气候变暖的备忘录,说“当承认不确定性成为传统智慧的一部分时,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这样的游说努力可能有一天看起来就像当今烟草行业否认吸烟和癌症之间联系一样这么荒唐和厚颜无耻。长时间以来,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已经朝向让人担心的方向。“气候变暖现在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了”显然不是耸人听闻的杂志的《经济学家》去年晚些时候总结说,“虽然任何将来的温暖的严重性仍然是不清楚的,人类活动看来是最大可能的原因。”
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气候科学家的讨论会更加确定,最近报道说“人类活动要对地球最近的气候变暖负责。”在这点上前副总统戈尔(Gore)应该得分,他1992年出版的书《濒临失衡的地球》(Earth in the Balance)曾受到嘲弄,现在看来走在时间前面十年。作为天文学的长期爱好者,戈尔早在1960年上大学的时候就对气候变化感兴趣,他选修了哈佛大学该领域的前沿科学家罗杰•雷维尔(Roger Revelle)讲授的课程。
大烟草(Big Tobacco)的事业主要是区域性的,被来自种植烟草的地区的律师所推动。相反,在当今党派偏见严重的环境下,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的辩论成为两个政党最两极化的议题之一。《全国评论》(National Journal)报道4月份国会内部进行对111名议员的调查显示98%的民主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你认为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地球变暖是因为人为污染造成的吗?”但是共和党人中回答“是”的比例只有23%。剩下77%的人回答是否定的。双方学习的教材是不同的吗?
气候变化成为科学作家穆尼最近的畅销书《共和党绞杀科学的战争》(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的中心话题。该书有误导作用,好像暗示对科学的攻击来自一个方面,实际上它来自包括左派在内的混杂的整体。然而,共和党(the GOP)当然企图开发一个关于全球变暖的立场,这个立场本身好像有点不科学。
在2002年国会选举之前,舆论领袖弗兰克•伦兹(Frank Luntz)鼓励共和党候选人使用诸如“科学家可以从当今世界的数据中推断所有的事情,但是这并不说明明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与此同时,由能源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上与共和党保守派运动密切联系的华盛顿的智囊库则对全球变暖不确定性推波助澜。
这些在短期内或许是聪明和有效的政治策略。但是随着全球变暖的迹象不断增加,如果湖泊继续干涸,夏季继续延长,地球本身可能会嘲笑共和党人的睁着眼说瞎话。他们企图扭曲科学的尝试就像从克林顿的草稿箱中搞来的。从长期来看,正如吸烟导致癌症辩论所证明的,科学不是儿戏。科学的惩罚是无情的。
披上科学外衣的新自由派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同情受到各方攻击的科学家。科学家就像启蒙运动思想本身成为受害者,是的,多数顶尖科学家仍然是男人。
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可避免的情况是,科学家被拉下水,或者自己委身于围绕科学的政治辩论和价值观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另外的党派偏见分子。(虽然不是那么明显)
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宗教右派对进化论的攻击。达尔文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痛打,用真正科学的精神提出现成的回应。也就是他的科学观察中,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能够证明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但是那种不可知论者的谨慎在当今科学家的身上好像消失了。
在大西洋两岸的新达尔文派生物学家中间,一种对抗的好战腔调逐渐获得力量。最著名的进化论者比如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豪地声称他们的审美观念---甚至暗示相信上帝的人都是傻瓜。道金斯在谈到信仰上帝的时候说“如果你相信它,你当然会觉得满足的。但是谁愿意相信谎言呢?”
但是正是道金斯试图要从科学中找到科学本质上无法提供的东西看起来逊色。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阿伦•雷什纳(Alan I. Leshner)在采访中说“他是极端的无神论者,他在杀死我们。”
如果现代科学家是他们喜欢说的古典自由派,他们就不会集中在争论分歧的一边了。实际上,他们表现出了深蓝定位(deep-blue orientation)。美国皮尤研究中心(A 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进行了调查,发现87%的科学家/工程师(随机抽样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的成员)不赞同布什当总统的做法。在1997年秋天,相反,78%的科学家/工程师赞同比尔克林顿的表现。
究竟这么回事?答案部分是科学家有个长期的倾向相信有些社会问题---全球变暖是现在的例子---要求集体的自由放任的解决办法(laissez-faire)共和党人不愿意支持的。在1930年代,科学家普遍支持罗斯福的新政,一群研究者对斯大林的罪行不闻不问,是实际上的共产党同情者或者本身就是共产党员。
今天的披着科学外衣的自由派和杰斐逊式的古典自由派不同,他们是1960年代的产物。一流的研究科学家如国家科学院的成员普遍继承了越南战争抗议运动和民权斗争所极端化了的学术环境。虽然多数科学家回避新左派的身份政治焦点,即使接受政府拨款的科学界也倾向于采取反对体制的姿态,拥抱科学自身纯洁的假象。
“通过在越南的行动,我们的政府动摇了我们对其做出聪明人性的决定的能力的信心,”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美国环保科学家联合会”(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在1968年成立文件上宣称。别忘了,这些科学家精英,从事与政府有关的秘密项目的成员,外号“The Jasons)是为五角大楼提供关于越南战争策略建议的。
科学家这种对那些运用华盛顿政治权力的纵容者的据说不涉政治的关注仍然存在。在最近网络帖子上关于美国和伊朗可能出现的冲突问题上,“环保科学家联合会”宣称伊朗“并不代表对美国直接的,现实的威胁。”这是政策判断,不是科学结论。这个判断是让人怀疑的,考虑到伊朗明显的迹象,支持邻居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分子和黎巴嫩的真主党,确实让美国军队在中东的任务变得非常复杂。
布什政府作为整体,不光是它的军事政策,都处于坎布里奇整套攻击射程之内。该团体在2004年引用气候变暖,儿童铅中毒,生殖健康,滥用毒品等议题说“当科学知识被发现和政治目标冲突的时候,政府常常操纵这个过程,通过让科学进入决策之中。”签名者包括曾经被新左派点名批评的哈佛昆虫学家爱德华•威尔逊。
在采访中,“美国环保科学家联合会”主席及其创立宣言起草人,康乃尔大学物理学家科特•高特福莱德(Kurt Gottfried)否认该团体或者科学家群体有政党偏见。“我不相信77%或者87%的科学家一般投票支持民主党。”不过,可以得到的数据显示,正如科学家喜欢说的,正好相反。在15年的调查中,皮尤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迈克尔•戴莫克(Michael Dimock)说科学家“总是表现出民主党中的精英群体。”
科学家群体,即使有时候是不情愿的战士,本身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两极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美国的缔造者把科学家看作融合美国民主的黏合剂,现在他们可能有变成美国不断分裂的推动力量的危险。
科学和民主
这些听起来好像是抽象的关心。美国民主往往被说成受这个或者那个威胁的危机中,但是总证明是有弹性,能复原的。虽然如此,当今对于科学如何能够在政治文化中运行的焦虑来自美国制度本身的深处。
这些担心曾经被路易斯•伯兰斯卡姆(Louis M. Branscomb)等人表达过。即将80岁大寿的老人,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IBM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作为美孚(Mobil)董事会的成员20多年了,他是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国家标准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局长。他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主任。
在最近的访问中,伯兰斯卡姆总结了研究者在追求科学真理时面临的风险:各派别的理论家,在诸如前任石油公司主任承认的气候变化问题上“追求权力和金钱”的政府,所有这些让我们“远离独立和理性的思考”,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有责任。
他说,现在还没有达到反对科学的时代,但是“已经偏离了启蒙运动的理性哲学所保留的核心内容,这些是设计美国宪法的人信赖的基础。
伯兰斯卡姆帮助组织了美国环保科学家联合会的对布什政府对待科学的态度的猛烈抨击,但是,正如他的话所显示的,他不是任何人想象中的民主党分子。同行物理学家代表密执安州大急流市(Grand Rapids, Mich.)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弗农•埃勒斯(Vernon Ehlers)称他为“非常公平的一个好人。”
难怪有为科学危险的地位辩解的说法。科学界的许多人,华盛顿的有些人,呼吁投入更多的钱支持学校给孩子们讲授现代科学方法。前大学教授埃勒斯说需要找到一个办法让普通美国人知道真正的科学,“学习的乐趣”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它们只关心我们(科学家)是否为他们研制了更好的手机。” 埃勒斯哀叹到。他预测,19世纪的美国人对科学的崇尚比现在更强烈,因为有那么多人在农场工作,不得不自己对付大自然的很多奥秘。
好科学的大众支持者,以及好的科学所需要的批评形思考,应该可以被强化,通过一流科学家的广泛参与选举政治中来。但是不要指望这个事情会发生。埃勒斯作为国会中的自然科学家是很罕见的,他是第一个研究科学家。而除了杰斐逊以外,没有哪个专业科学家曾经当过总统。对于一个典型的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来说,埃勒斯承认转行从政一般被认为是走下坡路的行为,这和律师当今占据政界的情况不同。
无论如何,这个问题不能仅仅指责教育体系的缺陷,或者为社会解释科学的魅力十足的科学家的缺乏。今天的科学争论,大体上说不是“大众的无知的问题,”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和神经科学家阿伦•雷什纳说,他注意到,我们生活在“复杂性极强的时代,有些美国人觉得可以自由地忽略或者歪曲对他们不利的科学。”
他接着说在民主社会,“只有科学家被迫靠科学生活。”或者用另外的方式,表达这个思想,自由包括反对科学的权利,也就是拒绝开明思想,把理论交付证据检验的自由派传统的权利。自由可以是不自由的。
不管怎么想象,美国人还没有到反对科学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全体人类福利的程度。从1970年来,大概70%的美国公众总是对这个问题做肯定的回答。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科学研究的好处是否大于它带来的危害?”但是,正如雷什纳指出的,调查也显示许多人忽视科学,如果科学与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因此,47%的美国人说他们不同意“人类起源于早期的动物物种。”
一个激动人心的,然而有点吓人的社会实验正在进行。问题是民主是否自然地推动科学的发展,或者科学实际上的现代进步是否与政府的预示来临的形式关系不大,而是与现代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时期某个特定时刻孕育出来的成果关系更大,美国由于缔造者的努力从中获益多多。
杰斐逊这个对科学进步和民主手拉手的绝对的乐观主义者1826年去世。就在后来被称为杰克逊式美国时代(Jacksonian America)的黎明,由穿泥巴靴子的人民统治的喧闹时代。1831年到美国游历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也是美国最深刻的编年史记录者担心科学在这个新国家的前途。“没有什么比思考对科学的高贵文化或者更高贵的科学部门更需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民主社会的结构更不适合进行思考的了。”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中说到。
长时间以来,这个观点好像是很少被忽视的托克维尔思想的一个例外,但是当今时代好像证明他的话确实是对的。
译自:“Who turned out the enlightenment?”By Paul Starobin, National Journal
http://nationaljournal.com/about/njweekly/stories/2006/0728nj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