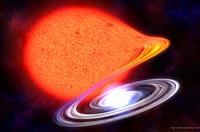
程老师10月28日晚遇害,在事发一小时之后,就有同学给我发短信,当时我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只知道他被人砍伤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有点麻木。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对暴力和血腥已经如此习惯,习惯得如每天的洗脸刷牙。
人的情感会有亲疏远近,这是天然的。好恶喜厌愛憎……,这些因事因人而发的情绪与情感,其强度与深度也都与先天禀赋、人际交往的疏密,还有后天的情感教育密切相关。
我认识程春明教授,至少不算陌生,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私交,也从无超过五分钟以上的两人单独相处。第一次与程老师的近距离接触还是在电话里,至少有六年以上了,是因为我写过一篇书评,关于舒国滢教授的一部文集,程老师看到以后,舒老师牵线,我们在电话里通了几句话,那时就感觉程老师是个热情的人,也是个谦逊的人。
后来,我去了法大,在我少数参加的几个会议上,我遇到程老师,这时候我们当然会聊几句,对他的感觉还是如初,他是个热情、善良和谦逊的人。再后来,有时候会在学校办公楼的楼道、电梯里遇到,这时也就是普通的相互问候。
一个多月以前的9月28日,我们在北航的一个案例研讨会上遇到,照例寒暄问候,他给我的印象还是那样,热情、善良、开朗、谦逊。最后一次遇到,则是上上周的10月22日下午,我们都在E段教学楼上课,在课间,我们一起站在教学楼外的天井里抽烟、聊天,上课铃响了,就各自回教室。
我和程老师的所有交往全都在这里了,我们没有很深密的友情。
知道程老师去世,是在事发之后两个小时,我从另外的同事那儿获知。我想,我对程老师的悲痛和惋惜,也是这样一点点开始的,我没有他的亲人好友那样的深悲剧痛,但是心理上一直处于莫名难受的状态。
这种状态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我和他是同事,我认识的人,但更重要的却不是这层关系,而是我们都是有血有肉,同样来自我们都不清楚的一个神秘之处的生命。
在最初的两天,这种心理状态甚至带来了一些生理反应,数日来,只要醒着,一个人的时候,我无时不想到那血腥的场景。当晚,从得知程老师去世之后,我就开始上火,脸上起包,第二天和第三天,肠胃不适、上吐下泻,没怎么敢多吃饭。我甚至怨恨媒体过于写实的报道——伤口的长度和深度,让我一直难受,说不出哪儿难受,可是哪儿都难受,一种莫名而焦虑的难受。
我自知,这种难受是源于我们都是人,都是有感情的,有喜怒哀乐的人。而现在这个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来不及打个招呼,来不及道个别,来不及一个相互致意的友善温和的表情,甚至连一个笑容都来不及给我、给他,他的生命就如烟而逝。现在,他还躺在那个冰冷的地方,带着致命的伤口,带着他的亲人友人们难以平息的深悲剧创,带着他对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眷念。虽然今天的太阳如此辉煌灿烂,可是程老师却再也看不见了,再也看不见了。
事发的第二天下午,是我的“中国宪政史”课,走进教室的时候,还有二十分钟才上课,我冲着同学们笑说了一句:“吓坏了吧都?”大家就笑了——空气里弥漫着过于诡异的紧张,我本能地想缓和一下,然而我立刻又觉得似乎是不妥的,我觉得自己整个的状态怎么会那么满拧。上课铃响了,我提议同学们全体起立,为程老师默哀一分钟。之后,我没有讲平时该讲的内容,那一堂课,我给大家讲“愛”,也让同学们讨论这个话题。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与现在的许多中小学教育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老师们无论水平如何,都很敬业,他们教给我们的善良、正直、理想主义,也总是在他们自己身上体现着。然而,就是在那样敬业的教育中,中国长期以来的仇恨教育、暴力教育,可是一样不缺,因为老师们也是愚民教育和暴力文化的受害者,正如现在的大量教师是愚民教育、暴力哲学、仇恨文化和全社会犬儒主义盛行的多重牺牲品。
那时候,我们缺乏的,最缺乏的情感教育——如现在一样匮乏,那时候,我不会愛,不懂得敬畏生命——仅仅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是远远不够的,十年的家庭善行培养,社会上一夜的恶行就足以摧毁它,人类堕落的能力和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现在的我,同样没有身不由己地去愛和敬畏生命的能力,虽然多年来,我在理性上不断地明示、暗示自己去努力地愛,去敬畏生命。但是,很遗憾,从生命本身和情感本身出发,如泉涌般的愛和对生命的敬畏,在这次事件中,让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那是没有的。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内心里有很柔软的一面,但也有很冷漠的一面。这冷漠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说与柔软的那一面同样本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听说程老师被如此血腥地砍伤之后,没能立刻反应过来的原因。我是一点点反应过来,随着当晚独自一人对事发现场无以控制的想象,一点点递增着这难受,这悲伤。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感受到的这一切,使得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既然我自知缺乏理想的愛和敬畏生命的能力,也自知缺乏在生命本源意义上反对暴力的能力,那么我至少要在理性层面上反对暴力、反对仇恨。无论在道德和在法律上,作为杀人嫌疑犯的付成励同学,他的暴力行为都是要强烈反对和谴责的,但他同样是暴力文化、仇恨哲学的受害者。
有些人因为此事件本身谴责学校,在案情大白天下之前,我想任何人没有资格就此事件本身谴责学校,因为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学校在其中有没有责任。
退一步讲,即使学校有责任,谴责学校这样的小环境,虽然不是毫无意义,也意义不大,它有更为深刻和普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原因,于学校而言,总体上说这是一起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学校也是受害者。在一个弥漫着如此暴力气息和仇恨毒雾的当代中国社会,人的生命似乎越来越像个侥幸的存在,谁也保不定自己哪天出了门就再回不了家——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在城管执法现场拍了几张照片,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对警察执法的方式表示不满,或者是因为你在被征地过程中不愿意失去家园……,既然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是如此侥幸地活着,我想我这个既怯懦又愛管闲事的人或许尤其没有理由例外。
我愿意用理性的声音替代我尚未炼成的敬畏生命的能力,告诉任何一位在我博客里或者在其心中诅咒我死的人们(我收到过不少这样的纸条,因为我反对死刑或者其它他们不喜欢的观点,他们发出过各种各样让我去死的诅咒),以及将来可能的所谓“执法”过程中杀害我的人,如果你真的对我拿起屠刀,将我杀死在路边、寓所,甚至我现在任教的讲台上,如果死之前我还能说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对不起,我没能帮你走出暴力的误区。”——如果那一刻我来不及说,或者我说出了本能反应的恶语,那就以现在的文字为准吧。
程春明老师已经被残忍地杀害,杀害他的不仅仅是付成励同学,更是这背后无处不在的暴力文化和仇恨哲学。师生两个都是受害者,但受害者远远不止于他们两位直接的当事人,还有各自的家人,程老师的父母、妻子还有未来的孩子,付成励同学的父母亲友(他的父母还要再背上罪犯家属的沉重心理负担,这是怎样的伤痛?),以及一切双方当事人认识的友好相识,还有容易被忽视的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们。有些伤害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一点点爆发出来,也许,这种心灵的康复对有些人甚至可能整整一生都未必能完成。
人死不能复生,悲伤也无法替代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如今付成励同学深陷囹圄、未来生死未卜,如果我们还没有能力如行云流水般地热愛生命、敬畏生命,至少可以做到理性上对此信念的认同,至少可以在理性上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悲悯作为生命中一员的付成励同学,鼓励他坚强地活着。在良法意义上,付成励同学固然应当承担自己戕残生命的恶果,亲友、学校、老师、同学、全社会包括我自己在内却也有义务关怀他、愛护他,帮助他早日获得灵魂的救赎与新生。
我相信,只有愛才能完成这些使命。我更相信,仇恨只能增加仇恨,暴力也只能助长暴力,只有愛才能最大程度地消融仇恨与暴力。
2008年11月3日於追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