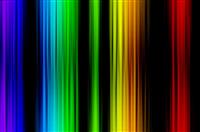这是一棵很大的银杏树。
在我养病的日子里,我天天围着它转几圈,啊,和我幼时看见的它相比,它衰老得多厉害呀!
瞧,它的大多数枝桠都是光秃秃的,兴许它同我一样得了严重的疾病吧?我弯腰拾起地上飘落的一片银杏叶,摊在掌心里翻来翻去地仔细看,犹如医生平时为我把脉诊病一般。
一位老先生凑过头来盯着我掌上的叶子说:“银杏是很长寿的树,这棵树少说也还该活几百年哪,可惜它却因为优伤快要死了。”
“什么?什么?忧伤?树也会优伤么?”我惊愕问。
“树当然有树的忧伤。”他缓缓地一字一顿地说。
我从老先生那饱经世事的眼神里,读出他能洞悉大自然的秘密,我赶快问:“那么,消除它的忧伤它会活下去?”老先生肯定地点点头。
“怎么消除呢?”我问。
老先生凑近我的耳朵,神秘地说:“你带上竹篮,到森林里去拾一篮鸟儿的歌声,银杏树就不会再忧伤了。”
老先生的耳语“嗖嗖”地穿过我的耳孔,直往我心里钻。
“哈,你不是开玩笑吧?鸟儿的歌声是能拾起的吗?这事只有童话里才有。”我是一个中年男人,可不是小娃娃,早过了幻想的年纪,一本正经地同我说这样的话,真是太不相宜了。
但老先生却很认真。他从他那宽松的茶色衣衫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木盒子,严肃地说:“喏,瞧这个。”他打开盒盖,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起一件物品,不知道是他过于珍爱手中的东西还是年龄大的缘故,递给我时,他的手索索发抖,“这副眼镜,你戴上,就会拾到鸟儿的歌了。”
天哪,这也叫眼镜?这是小孩随手用藤蔓挽成的两个圈儿,两个根本不圆的空框里谈不上装镜片,完全是小孩的玩艺儿,这老头返老还童,和我玩”过家家”的把戏逗乐子?兴许是老糊涂了。
刚才我还一直把他当成智慧老者请教,虔诚得近乎愚蠢,现在该怎么下台呢?
我尴尬地摆弄着手中的“眼镜”,老头几天真而又热切地盯着我说:“戴上试试。”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目光,从来没有什么目光能支配我做不乐意的事,我常常落得个“不随和”或是“不识时务”的名声,可今天,我猛然发现,面对一双天真而又热切的眼睛,你却没有抗拒它的力量。
我竟顺从地把“眼镜”架到脸上,尽管心里知道一个大男人这么做是多么愚蠢可笑。
确实,从空框里看出去,四周的高楼仍是高楼,脚下的水泥路仍支支岔岔地通向各幢楼房,被水泥路圈在中心的这棵银杏树还是孤零零地伸展着它残败的枝桠,像几根光骨节的手指想抓住空中的什么东西。
我暗中想侥幸看到点儿稀奇古怪的事,嗨,却什么都没发现,倒是发现老先生竟弃下我,转身向银杏树走去,把我像傻子似的扔在这里……
我竟被一个老头儿的恶作剧作弄了!老头也玩恶作剧?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我恨恨地盯着他的背影,气忿得竟忘了摘下“眼镜”。他那宽大的茶色衣裤在身后飘飘忽忽地摆动,似乎在嘲弄我说:“傻冒,拜拜了!”
忽然,我看见他径直走进银杏树的树干里,不,是树干分开两扇门,里面竟有一间“树屋”,老头儿跨进去,转身面向我喊出一句:“记住拾一篮鸟儿的歌来,拜托、拜托。”并行了一个极古老的拱手大礼,门便关闭了。
我三脚两步奔向银杏树,满树干摸着寻着想找那两扇门,但树干却严丝合缝,寻不到半点门的踪迹。
我摘下眼镜,再不把它看作儿戏了。
我想起几十年前,城市还没有扩展到这里,这儿除了这棵银杏树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杂树,我当时是个顽皮孩子,最喜欢在这林子里瞎钻,摘酸果、掏鸟窝、粘知了、捞毛柴……整个林子颠来倒去都有我的脚板印。
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在林中拾松塔,忽然,我们想玩新鲜的把戏,我扮教书先生,他们扮学生。
我把从我读过私塾的爷爷那里淘得的几个字写在这棵银杏树干上,心里窃笑着,谁读不出字来,我就用黄荆条狠狠打他的屁股,先生打学生,理所应当,爷爷当年读私塾就是这个规矩。
为了使自己更具有先生的权威,我从紧邻银杏树的青冈枝条上扭下一根垂着的葛藤,把葛藤挽两个圈儿做成眼镜架在鼻梁上,噢,那眼镜就同我现在手中的眼镜一模一样。
我不由得举起眼镜研究起它的质地来,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呀,这正是当年自己做的那副葛藤眼镜!虽然藤条已经干枯,但我认得出那藤条,当时由于柔韧的缘故,断头的地方总扭不断,我用牙连撕带咬,拉豁了好长一段皮,我虽然不满意这段豁皮藤条,不过只好将就用了。
那天玩完后,我把眼镜顺手扔在银杏树下,一副破眼镜,稀罕它干吗?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它竟真的成了稀罕之物——它是那片树林的唯一纪念啊!我突然像走进了银杏树那孤寂而无奈的心里,银杏树珍藏的仅仅是一副眼镜么?
我决定要到森林里为银杏树拾一篮鸟儿的歌声,不光是困在群楼中的银杏树,连我也有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见到过树林、没有听见过鸟鸣了。
我让妻为我准备一只竹篮,妻说:“这年月,谁还用竹篮呀?你想买菜,喏,用我的塑料兜兜买去。”
但我相信鸟儿的歌一定要用竹篮装才不会变调。
拖着病体,我跑遍城里大大小小的商店,这才发现本该放竹器的位置早已被光光鲜鲜的尼龙、塑料制品挤得满满当当,不知不觉中,往日平凡而熟悉的东西都在悄悄失去:树林、鸟鸣、竹器……往后还要失掉什么呢?该不是我自己吧?
经过鲜花店,我的眼睛一亮,插满花儿的花篮是竹编的哪!我像是寻到了宝贝,任花店老板“斩”了一大笔钱,却像是买椟还珠一样,在老板惊愕的注视下,将那满篮已按朵数算了钱的贵重洋种花儿全取下不要,提着个没算钱的空篮子欢天喜地地走了。
久违了,森林!当我踏进林间小路,嗅着潮润的绿色空气,旅途的劳顿一扫而光,连病体也忽然像注进了神奇的药物,猛地振奋了一下,病顿时好了一大半!
鸟鸣声此起彼伏地,我分辨着黄鹏、画眉子、斑鸠、杜鹃的歌声。啊,熟悉的鸟鸣使我回到了童年,我立刻掏出眼镜,像幼时那么顽皮地往鼻梁上一架,满林子乱钻起来。
啊,山板栗树上,两只相思鸟儿正在二重唱,只见一些晶亮、晶亮的东西从树的缝隙间弯弯曲曲地滴落下来,这不就是鸟儿的歌么?我仰着头双手捧着接那晶亮、晶亮的歌,一会儿工夫竟堆满了双手。我赶快把歌声放进竹篮,接着在麻柳树下接了一串画眉子的歌,在贞楠树下接了一嘟噜白头翁的歌,在松枝下接了一捧山雀的歌……
现在,我的篮子里装满了鸟儿们晶莹闪亮的歌声,它们像彩灯下的玻璃丝,颤动着绮丽的色彩。
提着篮子兴冲冲回到城里,满街的人都诧异地盯着我,我这才发现自己忘了取掉眼镜,幸喜没有碰见熟人,否则,大家看见我这副尊容,一定会说我疯了。
来到银杏树下,我高兴地大喊:“瞧,鸟儿的歌来啦!”
我举起篮子,突然看见篮里空空如也,呀,歌哪儿去了?漏掉了么?看见花篮编得稀稀的满是孔眼,咳,我这个冒失鬼,干吗没想到歌会漏掉呢?我急出一身冷汗,伸手到空篮子里摸摸,却碰到满满的一堆东西。
噢,原来我没戴眼镜,看不见鸟儿的歌。
我重新把眼镜架到脸上,立刻看见满篮子的歌都在蹦蹦跳跳,似乎它们认识老银杏树,似乎老银杏树在召唤它们。
我使出童年爬树的本领,把篮子里那弯弯曲曲的歌缠在银杏树的枝桠上,说也奇怪,只要沾上歌的枝枝杈杈,立刻冒出一簇簇新叶,银杏树像是急切地伸出满身绿色的耳朵来听鸟儿的歌。
跳下树来,我立刻听见满树百鸟争鸣,下班高峰,过往的人们都停下,团团围住银杏树,仰着头寻觅着:“鸟在哪儿?鸟在哪儿?”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神清气爽,纠缠我多年的疾病竟不治而愈,生命突然变得年轻起来。
推开门,迎着朝辉,我步履轻快地加入晨跑的人群。忽然,人们放慢脚步惊讶地叫道:“啊,树苗!路上长出树苗来了!”
可不是,在银杏树四周那环形的水泥路上,一夜之间冒出了一棵棵树苗,把坚硬的路面顶得破破碎碎。这时,一阵阵扑啦啦翅膀拍动,无数鸟儿飞到树苗及银杏树上,鸟儿们放开歌喉此起彼伏地歌唱,树苗在鸟儿的歌声中刷刷往上长。
只一会儿工夫,这里便成了一片小树林,待人们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置身在树林中了。从前我熟悉的那些树又在眼前,银杏树亦如当年那么生机勃勃。人们惊叹着:“高楼群中竟然冒出这么一片天然树林!”
我突然想戴上眼镜再拾一篮鸟儿们美丽的歌。我匆匆跑回家,书架上却不见了那藤条眼镜的身影。我东翻西找,猛然看见妻提着的垃圾桶里躺着碎成几段的眼镜。原来勤快的妻把它当废物打扫了。
我心痛地拾起碎块,把它拼粘成原来眼镜的模样,可它再也没有以前那样奇异的本领,我又用各种枝蔓挽了无数的眼镜,但全部是白费劲,啊,我多么想戴上“眼镜”再去拾几篮鸟儿的歌,把它分送给世间所有忧伤的树呀!
周围的人看见我爱戴藤条“眼镜”,都禁不住笑我:一个男子汉,怎么有个这么孩子气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