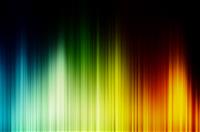
小时候,夏季,回到乡下去,随太爷爷生活了一段时间。
那时,刚认得铅笔,顿觉新奇,平日里多用它来玩乐作画,几乎多离了一分钟便手痒痒的。那次,恰巧望见干净的大木门,便总想着要在上面勾勒些什么,而猛地忆起抽屉里有支小铅笔,就兴冲冲地跑上楼去,翻来那只笔,又兴致勃勃地在门上画起个小娃娃来。阳光照在门上,像是抹金黄的颜料,染得一片灿烂。而那门上也映出些斑驳的影子,那影子欢乐地跃着,不知是鸟,还是我的心。
忽地,太爷爷挑着担菜,回来了。他望见我这副模样,先是一愣,接着大笑起来,放下肩边的菜担,轻轻走到我身旁,微微弯下腰来。我虽专心致志地画着,可这“娃娃”却像不听话似的,非惹出一副“四不像”的模样来。我哭了起来,放下笔,两只手抹着泪。太爷爷赶紧伸出那只粗糙的手,拍着我的背,压低了声音安慰我。他把笔轻轻摆在门前,又指着那“娃娃”说:“看这娃娃,多可爱啊。你不要急,一会儿再给你画个更漂亮的。”他为了逗我开心,还做了个鬼脸,那铁钉一样的面庞上泛起红锈,杂着哄与急。
我还哭着,直把头埋进太爷爷的
布衣里,还不甘心,在门上又多踹来几脚。那门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真像在哭,连声音也是颤巍巍的。
太爷爷急了,赶忙把手印在门上,随手拿起笔来描了一遍。我侧着头,看着这手印,逐渐停下了哭泣。
他回头望了望我,笑了,嘴角漾起涟漪,道道皱纹也鲜活起来。
他把我从臂弯间松开,递给我笔,仔细教我画“手”。他讲着讲着,不时咳嗽几声,趁着我练习的空当儿,背过腰去,猛咳几声,待我画好又转过身来,对我竖起大拇指,用着沙哑的声音夸我。我们祖孙俩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下午,他也向我打开了那扇尘封已久的心灵的木门,向我传赠童年难有的欢乐。
走的那天,我仍旧扒着木门不放手,生怕别离了。他那花白的头发在风中轻轻扬起,脸上挂着笑,催我快去,但眼眶却已然浑浊,模糊了起来……
再后来啊,那屋的主人走了,那快乐的孩童也不见了,空留一扇用铅笔画满稚拙的木门,在年月里“咯吱咯吱”地随风响着,凭生些蛛网青苔。
不知铅笔丢了否。
不知斑驳的影子流失了否。
只是那木门里的旧时光,再也回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