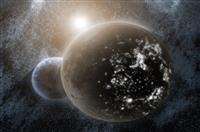我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不耐烦地环顾着我从未久待的厨房。外婆倚着一把枯青藤椅,莹白的米从她粗糙土黄的双指间滚入清亮的水中,微漾。一粒粒米如同稚小的娃娃,白白胖胖,满足地躺在渐染浊白的水中,不复当初的干枯。我吸了吸鼻子,心不觉安了下来……
外婆小心地盖上锈黑的锅盖,“咕噜咕噜——”粥水翻滚,像二月的泉水吃力地闷响。蓦地,我瞥见了那米水相融,耳畔边回响着的犹如湍急的水流,锅盖一下下被还冒着白汽的粥水,调皮地踢弄着。我
竟心急地前倾着身子。外婆已迈着蹒跚的步子走来,我不由得好笑地站直了身,没想到我第一次在厨房心急守候的,偏偏是我原以为最平淡无味的米粥。
外婆拾一块润湿的抹布,小心地握住滚烫的锅盖,缓缓微侧,瞬时,白腾腾的粥欢快地蹿了出来,氤氲在潮湿的灶边,温暖仿佛从指间溢了出来。我不可思议的腾起身,轻嗅粥香,竟是这样陌生。迫不及待地细细抿一口酥酥颤着的米粥,滚烫而粗糙的甜蜜跃于舌尖,记忆蓦地涌了上来,是它温暖了岁月的日日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