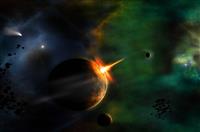江南的天总是有着灰白的色泽,连带夜晚的月,朦胧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我还是喜欢幼时家乡的那抹月,正如她对我所描绘的:北方的朗月清风自皎白,可比秀丽江南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小家碧月爽朗多了。
她是我儿时的启蒙老师,颇为精神的一个小老太,偏爱诗词。至于她姓名什么的,都因时光荏苒而模糊了。最近听说我自小生活的那一带动土拆迁,我才蓦然想起那谁也不曾窥得的“故乡明月”。
月夜幽静,蝉声低啜,蛙声呜咽。徐徐缓缓,仿若风过林海;起起伏伏,宛如月映澄江。白日里安稳学习的孩子们,在黝黑黝黑如蜗壳的夜晚永远闲不住。迎着白花花的银月就撒开脚丫子满地跑,不知疲倦,仿佛这般便能跑过天上的星河皓月、地下的山川河流。
我家在幼儿园的不远处,幼儿园的后庭是一块闲置的土田。不过自从她来到了这办起一所幼儿园,便被种满了时令蔬果。而这一方天地,每逢炎炎夏日便长满了绿生生的植物——黄瓜。刚上幼儿园的第一年,我对离开温暖自由的小家来到这个名为“幼儿园”的破烂地方感到不满,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地溜进这个像是园长秘密基地的菜园。我仰起脑袋踮着脚尖,头顶是满架子的青碧黄瓜,清香四溢,被风一吹还时不时拍着我的脑袋。我甩甩脑袋,一个歹念猛地蹿进我自认为聪明异常的脑袋瓜中:把她种的大黄瓜吃光,叫她无瓜可吃!我便蹲在一旁的磐石上,喂饱了蚊子也把自己撑坏了。恰在此时,视线中的月亮越发朦胧,弯弯的月牙似乎也交叠生成一轮新的满月,比我吃撑
的肚皮还要圆润。
这把我的家人急坏了,到处找不着我,还请左邻右舍一起找寻。她也是我的邻居,自然也在其中。似乎是在午夜时分她才扒开菜园子找到满腿是包的我。我迷迷糊糊的,掀起眼皮又睡过去。她大概是有些恼了,向来和蔼的面容染上怒色,但瞧见我一副昏昏沉沉的模样又蹙起的眉头终于忍不住舒展开。我感受到有一双瘦削却有力的臂膀抱起我,在茫茫月色中深一步浅一步地蹒跚前行。“月色穿沙碧净,人家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你个小兔崽子倒跑来这好不快乐地抱着黄瓜啃,我这把老骨头瞧着都腻味得很……”那时我什么都未曾听懂,只晓得那夜我黄瓜吃得着实不少,以至于此后某一阵子看见黄瓜就觉得饱。
她从不曾教予我什么,就连她总爱挂在嘴边的各种诗词,我也只会几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类的。她从不会过分苛求一个尚在懵懂的孩子,只会拍着她的脑袋,文绉绉地说:“‘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黄瓜也挺好,与众不同,不必与泯然众人的与什么牡丹、萼梅争奇斗艳。”
我还曾记得,她鬓角总有几缕掩不住的银丝,像灰墙胚里的白粉尘。她却颇为骄傲地反驳我,说她这是年轻时在南方城里教与我们一样的小崽子们时粉笔灰给染的。对了,她的家乡在富庶的江南,却偏偏跑来北方生活。
她给予我的实在不多,却偏用一种另类的方式保存了我心中的那片澄澈净土。故乡的月不再清朗明冽,却永远定格在那片早已不复存在的菜园上空,安安静静的,一如往日般的光风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