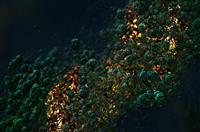
我的爷爷,是一个工人,之前总是在外面干工匠活,但如今也不得不服老,改行看管工地。
由于老爷子常在外地,见面机会不多,一年也只能见那么几次,他最不能让我忘记的是他的手。
他身为南方人,常年与北方的凜冽抗争,他的手常常被冻得裂开来,裂出一道道小口子,不仅仅是口子,工伤大大小小也有十几处。尤其是大拇指上一道口子,深可见骨,两边的肉向外侧翻,加上爷爷并不算爱干净,每次洗手只是流星一般稍纵即逝,伤口中慢慢囤积起黑泥,长年累月,黑泥不断地的堆积、提炼、升华,总之越练越纯净。仿佛真的可以提炼出某种东西来。黑泥几乎与皮肤齐平,仿佛黑泥便是他手的一部分,如同天然的纹路。他的指甲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中指上已了无指甲的痕迹,这是一次工伤留下的。整个手如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支离破碎。我常抚摸他的手,看起来像干柴,摸起来更像干柴,他的手,像一块沧桑的树皮。
爷爷在除夕夜里总会彻底洗一次手。他先把手放入热水中浸泡,泡得各个关节都放松,柔和。之后,我便会掏出牙刷仔细地清理这“黄土高原”,这个过程,大约得有半个钟头。最后细细打上香皂,冲洗。再拿些膏药涂抹在手上,促进一下伤口的愈合。爷爷常说,手没了这黑泥,干起事来不习惯。轻飘飘的不像话。但不过两天,爷爷的手马上打回原形。
而下一次这样的洗手仪式,则是在一年之后了。
虽然他的手面目全非,但我就是不讨厌,反倒十分喜欢。小时候,我常如游鱼般钻入他的被窝,求他给我挠背。他便会笑眯眯地用手在我背上来回摩挲,他手上的伤口结了疤,崎岖不平,扶在背上,滋滋……无法用语言形容,比什么“不求人”好多啦。这件小事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几件事之一。
小学时,家中需要盖间小屋,我目睹了他一个人从和泥到封顶完成这个浩大工程的整个过程。如何用他这双具有伟大神力的手,仅一个星期便完了工。我时常啃一个冻柿子,坐在门槛上,看爷爷如何和水泥:他抡起铁铲,将底部的水泥翻上来,在上百次的轮动后,水泥和黄砂搅在了一起密不可分。在这期间,他的手被染得灰白。几滴飞溅的水泥很快在他的手上冻牢;他的汗水滴在手上,与水泥搅成灰白色,但汗水很快被挥洒到地上……
爷爷的手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家道中落,他放弃了成为大学生的机会。转而自学泥瓦匠手艺。后来又为攒钱给儿子付大学学费,甚至去北漂,他的这双手有太多荣耀与辛酸。如果问他的经历,只需抬手,一看便知。他如今年过古稀。依然在外奋斗,不更是出于对家庭的责任?
至此停笔,凝望窗外,已是夕阳西下。相信他也一样在远方与我共赏这缕残阳,点点金光洒落在他的手上——世间最美丽的一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