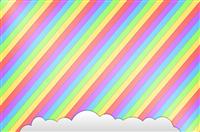
天空染上了夕阳的色泽,稻田里的蝉鸣渐渐荡的无声了。空气里,涌着寂静。面前这座石屋里曾住着一位老人,平和慈祥却充满力量,她是我的奶奶。
奶奶住在乡下,石屋里没什么物件。除去一张长炕,就是一口大锅——一口煮馄炖用的大锅。每次回乡下,一推门,准瞧见奶奶就站在大锅前。额间拂着几缕白发,皱纹爬上眼角,张开双臂,将我拥入怀中。如今这口大锅已经锈迹斑斑,却记刻着,奶奶亲手为我煮馄炖的往日时光。
奶奶包的馄炖,馅儿、皮儿都有讲究,一把大筛子,我抓着,底下一张板,奶奶倒面,我就使劲摇。也不清楚漏出去了多少,只是摇的开心。筛完,奶奶就在板子上揉面,三四斤的大面团,分出几十份,擀成圆饼,加上土生土长的山猪肉,一颗冰糖,一块猪油,不带丁点儿菜沫,就包平实下锅滚煮,待到沉睡在水里的馄炖游着水唱着歌,就是时候了。
捞出来,盛在大白瓷碗里,一口一个,鲜滑,喷香。我吃着,奶奶用手抚着我的脸,那手是那么的温暖,掌中划过我脸庞的纹,镌刻着岁月。奶奶望着我,目光里充满了慈爱。我每每问:“奶奶,你为什么不吃?”只听她答道:“人老了,不爱吃肉。单看你吃的
这么香,我也就饱了。”那个时候,我从未多想,只当一句随意的话语,从耳边飘去了。
当年的我,怎么也想不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吃奶奶亲手包的馄饨。那时,奶奶早已弱不禁风,炉前的身影瘦的如同一张纸片,她是顶着病,强撑着为我包的馄饨。而年少无知的我却未曾察觉,更未曾想这是最后一次。只是吃着吃着,心底,却不知为何涌过一丝悲凉。临走前,奶奶拖着身子追了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大包,在风中颤抖着说道:“再带些回去吧。”我还未做反应,母亲却已经接下了。那一瞬间,奶奶的眼里,似乎闪过了泪光。
一个月后,我便听得了奶奶重病不起的消息。石屋里,奶奶的四个儿女都到齐了。只记得奶奶最后再扫过屋子,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眼底闪过一道光,似乎,是疼爱却再也不能照顾了。自那以后,奶奶便再也认不得人了。
几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日升月落。我拖着行囊,又回到那个冷冷清清的石屋。如今的奶奶,已化作一只飞至天堂的白鸽,于我远去。只是耳边,还留着奶奶慈爱的叮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