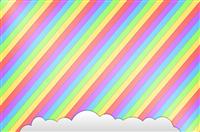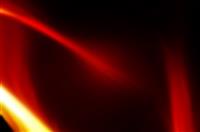
校园门前的过道,有五十米的距离,两侧摆满黄色的菊花,那是为迎接几日之前,为那个全国研讨会而布设的,今天是立冬的日子,她依然开的很艳。然而,除了刚刚摆布来之际为校园的师生瞩目,而且拟用宾客的目光试看她的美丽和粉饰之外,现在,很少再有人关注她了吧。
每次上班下班经过她的面前,我却总是要去看她一眼的,而且常常有搬走两盆放到办公室内独赏的冲动,莫非也有如我的过客,每天都会被她的娇艳所动心一下,颤动一下,而又终是匆匆的把她遗忘了?仿佛,她生来就在这里,不曾有过童年和乡土的美好梦想。
如若她真有灵,她还是会想念往年的梦和童年吧,往年在故土的风雨中,想到今秋的仿佛出嫁的荣光吧。她默默受用着厚实肥沃土壤里温存的叮嘱和慈爱,默默在暖的阳光下,在闪烁着金色的风中成长,出落的高些,有了秀的模样,娉婷的模样,又有了欲说还羞的花蕾,一团团在腰肢,在胸膛,在肩头,惊喜诧讶的鼓胀起来,也终于在一个早晨,在未霜降的早晨,次第开放,相互召唤着,一枚枚的开放。而当一辆辆来接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好奇的追问着自己的将去将在的地方吧!
是啊,她们的一生,就要在不知名的地方安步驻足,想来想到,被热闹的众目睽睽目光聚焦的一天两天之后,却这样落寞的在人往的路旁,群开而又孤独的注视着光的到来,光的灭去,那怕也常有我的目光和惊心,深情的把她们打量,直到一切时光渐渐枯萎,一切生息渐渐成尘。
善哉。善吗?这样的菊花,就是这样虽然是全国的年会,就是这般龚教授、江西、香港、新疆朋友们,菊花一现的,现已经不知道在何处的,也许已经故去,也去已经荒唐的,即使我当年的舞台和解说词,当年的四个主持人,我的专题片,我们的那些可亲的同事,并未流连在小小的魏都区的区志,即使那端鲜艳的菊,我的爱人,消逝了。在我去世的门前,淡淡的香,足矣,爱你,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