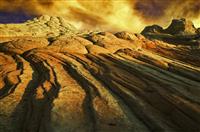
从医院出来,体检的结果赫然在目——偏胖,医生说无大碍,妻子也忙着说没有关系。我当然知道这没什么,可心情却未能释然。联想到这些日子晨练,小跑一阵竟然汗出如雨,气喘吁吁,而且极易疲倦,以前即使跑上好几里路也不过是蒙蒙小汗,稍事休息,便又精力无限。早几天腰部又开始容易酸痛,据此种种,慢慢地人生大概开始力不从心,还是衰老静悄悄地要来了?
妻子看见我蹙紧了眉头,知道我心头郁结,建议我去公园走走。上莲花山公园吧!那里视野开阔草木茂盛,空气洁净。
未睹其人,先闻其声。一阵虽不激烈但饱含激情的舞曲沿着山高树低荡漾过来,我以为有一群浪漫的年轻人在此开派对,歌舞升平。等我进得山门,沿坡路走上几步,却看到空旷的地面上数十位老前辈在翩然起舞,夜色未至,烈日犹存,怎么有这些老人家齐聚一地呢?看看他们轻盈体态和轻巧的舞步,只觉和白发,和脸上的沟壑极不相称,然而确是事实。
一位看上去很精干的老人家在自然形成的舞池之外,斜倚着一棵小树,眼光追随着翩跹的舞者,眼神有异,分明有着嫉妒和不满。是什么使老人家在乐酣舞浓的背景中,心事纷乱意难平?循着他的目光,一位矍铄清爽的老太太正轻松自如地踩着舞步,脸上挂满了欢乐,她的舞伴,一个高大挺拔的老头,年轻时必然风度翩翩。妻子笑着说:“原来老人家吃醋了!”再看看斜倚在树上的老人,果然一副醋意正浓的神情,大概在想这曲子怎么就这么长!
吃醋大抵是年轻人的事,但发生在年过六旬的老人身上,更让人对感情一事有了奢望。岁月摧毁了许多,消磨了更多,但终究有些屹立时间之流,无有损耗,例如这和年岁沧桑共存的爱情。
走得远了,垂钓的湖泊近在眼前。湖水清且涟漪,更妙的是林子里啁啾的鸟儿也跑来湖面上,高低起伏地飞翔、穿越。一些叫不出名儿的鸟大概飞翔得乏味了,羡慕起人类来,三三两两在湖沿水泥地面上步行起来。鸟和鸭子毕竟是近亲,走起台步来一模一样,屁股一扭一扭,一场跨物种的模仿秀。
这些鸟并不怕人,而人也不惊扰鸟类。即使和老人家同坐在长凳上,老人们也不意外,不驱赶,任其调皮捣蛋,仿佛对待家中突然出现的邻家娃娃。对于打太极的老人,无论是单鞭还是云手,鸟儿也无动于衷,一点也不妨碍它们在他周围轻言软语。电视上见到威尼斯广场中鸽子钻到游客怀中抢食不免惊诧,但鸽子素来性情温文,热爱和平。杜子美诗写“相亲相近水中鸥”,张孝祥词云“正为鸥盟留醉眼”,大概在江湖间鸥和人对峙久了,也惺惺相惜,有了友谊。
鸽子和鸥鹭与人的友爱自古已有,多半出于天性。我眼前这些鸟能和老人们不离不弃,无忧无惧又是为何?打量这些满头霜华的老者,我猜是年轻时候的霸气、杀气、戾气涤荡一尽,通体只有静穆之气,冲淡谦和,因此鸟类不但不敬而远之,反近而昵之。这副在瓦尔登湖也见不到的场景可算是“天人合一”的一个具体例子。看来,年龄增大,倒和自然更贴近,越发合乎天道了。
残阳如血!这个比喻总显得悲壮。就连残阳中的歌声都衬出几分苍凉,直到我见到这群引吭高歌者,这一感觉才消除。
又是一群老人,今天的莲花山是他们的舞榭歌台,连青春生活的少年郎也没有这样的情怀。草坪里聚拢的人不多,但分工合作,有条不紊,如一个乐团,笛声清远悠扬,二胡呜咽怨慕,手风琴轻快跳荡,还有认真专业的指挥,歌者更少,但是声振林木,豪迈激昂。唱歌的是老人,歌自然算是老歌,然而那豪情依然似当年甚至胜当年。《敖包相会》、《五指山和万泉河》、《乌苏里船歌》,一首连一首。最喜欢的是那位谢顶老人的《乌苏里船歌》。毕竟有了生活的积淀,有了世事沧桑的浸透,歌声苍劲,气势豪迈。一听这歌,仿佛就置身于松花江冰天雪地里,白皑皑一片河山,风卷起雪花四处飞扬。也许这想象和歌的意境不合,但是那种博大确是实实在在的。
一拨又一拨的人停留,然后走散,夕阳中的歌者和演奏者却沉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一曲续一曲,没有倦意,也毫不在意闲言碎语。孔夫子讲人过七十则“从心而不逾矩”,何必要设这样的年龄下限呢?只要豪情满怀,激情犹浓,大可学这群可爱的老人,无拘无束地放歌。
歌声似乎一直追随着我和妻子,下山的路就在脚下。已经遇上的老人们给了我太多喜悦,对生命和岁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今日种种美丽的点拨也许要宣告幕落了。且行且远,哪知还有一番热闹在前方。
原来有一卖毛笔的年轻人在即兴挥毫,墨迹淋漓,满纸云烟。一幅宋词条幅惹来众多围观者,许多赞叹和评议。
实然,一位相貌平平趿着拖鞋,衣衫不整的老头说:“这字写得漂亮,但是没到火候。”众人开始怂恿该老人露一手,他眯着眼睛望望天,说写就写,要写就写大字,露露腕力。然后从卖笔年轻人那里选了一枝最大的笔,巨笔如椽。老头不用墨,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纸可供他写,何况他笑着说要环保。
有人竟然拿桶提了一桶水来,老人将笔往桶里一放,各路人马纷纷退避,让出一块水泥地,老人双手握了笔杆,挥舞起来。顷刻间,四个大字写成——“气韵生动”,是一手老辣苍劲的碑体,果然不同凡响。众人连声叫好,卖笔的年轻人也是甘拜下风。老头挠挠脖子,眯了眼睛,对年轻人说:“小伙子也很好,不过字有韵而气不足,多临碑帖有好处。”
众人还要他再写几个,他抬腕看了看手表,一声哎呀,吧嗒吧嗒就小跑下山了,大家不禁都笑了起来。天真烂漫,童心未泯,他才可以这么潇洒,可以“老夫聊发少年狂”!
残阳褪尽,道路已经暗了下来,那位古怪艺术家滑稽的身影已在视线之外。来时的伤感,衰老惘惘的威胁,和这残阳一道,被我遗弃在山林湖泊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