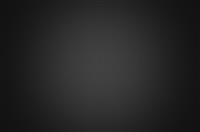二月二,龙抬头。这天也是土地神的生日。而明年的今天,却是敬奉土地神几十年如一日的我大爷的忌日。
2013年3月13日,农历二月二。这天上午,刚下深圳几天正在老乡彭国建的办公室网上投简历的我,接到妻子从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大爷没得了。还说大爷走得很安祥,没病没痛(痛可能有,只是我们不知道)的,他是在放水时在屋后阳沟不小心崴了一下,就瘫坐在地,被我的自信爷爷把他抱回家后,没多久就落气了。
少了病床上的折磨、孤凄与绝望,老人家若得这种走法,不能不说是一种福气,可能是上天对他一生忠厚老实的一种眷顾和恩赐吧。
事情如果要描述得更具体些,是这样的:与我爷爷同老太太的大爷就住在我屋坎下,他和我大婆两个人守着老屋和他屋坎下我二叔的屋。大叔在村里另屋别居,务农为生;二叔全家出门打工,过年前回来,过完年又走;四叔在邻县的王村做生意;五叔在县里工作。
村里还没通真正意义上(管理规范、供应正常)的自来水,长年以来大都是要靠背或挑水来解决生活用水。幸好在我们寨子后面的塘坝内坎有一个流量不大的水井,有人承头买了水管,将水接了出来,大家相互体谅着将就着用。
由于用的户数较多,这就需要人勤快些,瞄着别人不要时去放。相依为命的两位老人都已年逾八旬,要想把本来不够用的水接到自家的水池,必定会比别人艰难得多。对于大爷来说,像放水这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从来都是亲力亲为,不用大婆支使的。
沿路的塑料水管由于年代久或被牛踩而破漏的,水放下来后还得巡查。有时刚放没多久又被别人断去了,就得上门跟人家商量:我才放,等我放一些后再让给你,将就一下。总之,要放满一汗水池的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有些人永远无法体验到的艰辛。所以,除了看电视没有其他娱乐项目的大爷,就把放水提上了晚年生活的重要日程,放水甚至成了他多年来的生命内容。
性格内向的大爷不爱串门。再加上年纪大,耳朵有些背,有时跟别人讲话接不上砣。偶尔上别人家坐坐,大部分时间也只是当个听众。
2010年,我从吉首辞职回家后,在离村子两里远的地方建了栋3间的平房。去村子里就经常看到他拄着拐杖乐此不疲地看住在上面邻居的水池要不要接水,别人不需要的话他就抽空去放,去巡查。只要水池的水消下去几寸,他便城隍庙长草——荒(慌)了神,不用大婆催他,他便去放。有的人不解:“水又不能当饭吃,晓得要放那么多搞什么?!”
以前,我也对这句话深以为然。但是,这两天因为还没找到工作,住在国建的房间,一边要为稻梁谋而心急如焚,心乱如麻,如坐针毡,一边又想着十几天前还见过而今阴阳两隔音容宛在的大爷,想着他因患支气管炎而咳嗽着去放水的情景,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闪过。于是我又悟出了另外一种感觉:其实,守着空巢的大爷,放水不仅是他生存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可能更是他精神的需要,可能是他排遣内心空虚孤独的唯一方式。也许,只有在放水的路上来回行走,才能证明他生命的存在;听到水从细小的胶水管流到水池的声响,就是他的天籁,他很乐意享受这种声响;煮饭洗菜用上亲手放下来的水,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样一来,放水就成了他的瘾,他的乐趣。
大爷是个打掉牙齿往肚里咽的老实人。在我的印象中,他没跟乡邻吵过架。他青壮年时若村里有人办红白喜事,别人找他帮忙,其他不用做,他的主要任务是用背桶来运输水。像一只骆驼,嗯哼嗯哼地丈量从事主家到水井又从水井到事主家的距离。很负责,很卖力,让事主不用为这方面的事务操心。而大婆,在性格方面就比他强势些,家里家外都是她作主。每个家庭乃至每个单位都是这样的,要有埋头苦干的,也要有撑门面的。
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大爷一生敬畏土地神。在我还在读初中时,他就在屋后东南方去水井的路边用石头码了个土地台,供奉土地神,挂了红布,在台前摆一个装满火灰的罐头瓶,里面或斜或正的插了许多香。只要是过年、中秋、端午、清明等节气,他都会用碗盛上饭,上面放一块用五花肉做的煮熟的“神佛”,插上筷子,带上香蜡纸草,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地敬奉。若逢农历二月初二,土地神生日这天,他还会放两挂爆竹。每年杀年猪,他从不干帮忙摁猪接血这些事的,他的重要工作是拿事先叠好的3叠9张草纸,在屠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当口,一直在旁候着的他赶紧上前,伸手把纸蘸上猪血,与神佛一起敬土地神。
二月初二,龙抬头;二月初二,土地神生日;二月初二,大爷用他排遣空虚寂寞的方式和过程完成了他的宿命;二月初二,在群贤毕至的土地神生日宴上,大爷眼带忧郁,悲悯地打量着我们放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