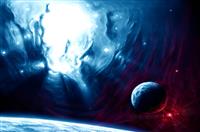原本是极喜欢看樱花飘落的。
和其他樱树一样,我家院落中一白一红两株樱树,如春的使者,最先告知春的到来。在春中飘落的樱花,像成片的蝶儿在空中蹁跹起舞,泼就一幅好春色,便早有写它的念头了。
那两株樱树,是前些年母亲栽的。它们总在春来的时候,分别开出重瓣和单瓣的樱花。粉红的、洁白的樱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间杂在一起,弥漫着淡淡的樱花香,衬托着不大的院落。每每那时,弄壶茶,闲坐它们其间,任朵朵樱花婆娑摇曳,看片片花瓣优雅舞动,有一份花醉,也添一些人醉,是极惬意的。
起始,我不太知道也不曾细究过母亲种樱花的缘由,只以为那是随意的事,也只以为她喜欢看樱花的白、樱花的红,感怀人生如花开花落般的匆匆、太匆匆而已。
刚种下樱树那会儿,母亲总喜欢徘徊它们的左右,然后嘱托我:“你若有孩子了,要告诉他,这樱树是他奶奶种下的,看见它,就像看见奶奶。”重病在身的母亲,有着她的担忧和希冀。
樱树慢慢抽枝长大,儿子也很快出生了。但逢冬去春来、樱花绽放时,母亲便牵着她的小孙子和外孙女散坐在樱树下,沐着和煦的阳光,赏着那盛开的SAKURA,教他们哼唱SAKURA的歌谣,絮叨着她的童年时光。我只在边上静静地看着、听着。
陪母亲赏樱的时候,总会恍然觉得,我被母亲牵着,去到了她曾经的故土,迈进了那深深的院落,尽管我从没去过那地方。在灿灿的樱花中,我好似看见了外公和母亲踱步花园、同赏樱花的模糊背影,其实我也只在照片上见过外公。又好像看见了母亲和舅舅们在樱树下摇头晃脑诵读“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样子来,即便我与舅舅也就一面之缘。
其实,我明白,那些都是母亲抹不去的思念。
花落时分,母亲更喜欢于樱树下,低低哼唱着“好花不长开、好景不常在”,神伤地看着樱花飘落、散去,也总要独立好久,才肯轻轻地将那樱花残骨拢聚在一起,轻轻地撒在樱树根下。后来才知道,花落是母亲从前的悲伤,她无可奈何看花落去,就像她匆匆而过的十四年的儿时人生,那有着外公和舅舅关爱的岁月。知道母亲病因的我,其实很清楚,花落也是母亲晚年的叹息,她万般留恋樱花的灿烂,她知足儿孙绕膝衣食无忧的晚年,但却心烦病魔缠身不知来年的日子。
樱花的来来去去,暗合着母亲的樱花情结。原来,那源于华夏、盛于东瀛的樱花,是最相思的,甚于那久被传颂的“南国红豆”。同样是春来发几枝或红或白、开得密密的樱花,如她极珍贵的相思,是她内心里的被长辈们宠爱有加的幸福童年的久久怀念、也是她对年少时便天涯各一方的外公和舅舅们的绵绵思念,更是她满心能给儿孙们带来安慰和庇护的希望。当然,与那樱花开落相随而不经意哼唱的“好花不长开、好景不常在”的词儿,则是她对失落的幸福童年的一种无以自拔的慰藉。
去年花开花落后,和母亲一起收拾着花园。看着枝杈交叠丛生的樱树,母亲对我说,“樱花是有灵性的,种了就要把它打理好,抽空找物业把樱树修剪一下,开春后会花会更艳,叶会更茂密的。”我漫不经心地应道:“现在这样更好,顺其自然吧。”母亲听罢不愿拂我意,轻轻叹了声:“弄好了,你们有得看了,我还不知能再看几次!随你罢。”
或许应验了母亲的话,不知今年上海春来晚的缘故,还是树没有整修的原因,本应在每年3月下旬开出的咱家樱花,迟迟不肯开出。那几日里,母亲有点诧异,也有些惶惶,总嘀咕着不会有啥不对吧。看惯了樱花的来来去去,我倒未在乎它的何时再来,只还惦记着如何写樱花。
樱花终究是开了。只不过,今次花开的时候,种花人已悄悄地离它而去,已然看不见它的再次绽放了。花儿再开,人已不醉,独剩一个“碎”了。
三月的最后一天,当我匆匆赶到医院,母亲已气若游丝,眼睛无神地望着天空,嘴角微微抖动,似乎想要说些啥,终于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便吐尽了最后一口气。
与病魔抗争了八年的母亲,带着好多牵挂和遗憾,去往另一个世界了。当我想轻轻合上她的双眼时,她的眼却总不肯合上,但见晶莹的泪珠在眼角挂着。我知道,她是不舍得离去的,因为有着太多牵挂。她牵挂着一手领大的孙儿们学业有成,她牵挂着客死异乡的外公遗骸归来,牵挂着与隔海相望的舅舅们的再聚首,她牵挂着樱花再开的样子······
木木地看着通往黄泉路的冰柜门缓缓打开,一股寒气扑面而至,将母亲单薄的身躯紧紧裹住,迅速地吞噬进去。在那冰冷漆黑的世界里,只有母亲孤独无声地躺着。我想,生性喜欢热闹的母亲,一定不喜欢容身在这清冷世界的,从来就爱有天有地感觉的母亲,也肯定不愿在这窄窄空间里呆着的,但我无助也无法改变它,只任由那冰冷无情的门,将我与母亲阴阳相隔。。。。。。就此“母别子,子别母”,默默的泪水换成撕心裂肺的哭喊,也唤不回朝夕相处四十八年的母亲离去。
一路泪水、一路恍惚,回到家里。无去处,踱步花园,习惯地看一眼樱树,白色的那株,竟然寂寂的开了,开得满满的,如白雪裹树,茫茫一片,淹没了门前那片天。看天看地看自己,周遭一片,皆是白白的,白的刺眼,直叫人不能看清天与云。
依偎在身边的儿子怯怯问我:“老爸,樱花为啥这么白?”我低低地回答:“它们想奶奶了。”“为啥想奶奶了?”“奶奶走了!”儿子又问:“奶奶去哪里了?”我指指云天说:“奶奶去天堂了。”儿子说:“为啥去那里?”我梗咽着告诉他:“奶奶想太公太婆了,去看他们了。”“为啥现在去呀,我还没长大呢!以后放学我就看不到奶奶了,再也没有人看着我了!”脆脆的话音刚落,我已经泪如雨下,无法再回答。
樱花是开了,开在了清明时节,只不过欲断魂的,不是路上的行人,而是我,纷纷的雨也不是苍天的,而是我和家人的泪。樱花是开了,依旧那样的白,而泪眼朦胧中,早已分辨不了哪是花,哪是天。“昨来风雨偏相厄,谁向人天诉此哀”,我无心盘桓其下,更不敢靠它太近。
也只在今年看花时,才知道,樱花原是有灵性的。
两株樱树,偏就那白的开了,开在母亲离开的那天,像是要让栽树的人再看一眼那樱花,想是告诉种花人,它的再来和它的哀思。而那红的直直不肯开出,大概是怕看花的人伤心,怕那花红得不合时宜。它们与我一样,也有泪,如我止不住的心碎,哀伤着种花的人离去。
看着满屋子的人给母亲忙做“头七”,总觉得一切都空落落的,也只好往树下呆坐着傻看。那白的花,竟很灵性地在中午时分,开始飘落了。那是母亲归去的时间。
阴沉的天色里,那一片一片惨白的樱花速速地凋落,想着母亲从前的点点滴滴,好像屋前屋后都有母亲的影子,幽幽地绕我左右。原以为花开花落是极平常的,花落才来花开,却不曾想过我的樱花从开到落,竟那么短、那么短,短得让人孤寂、无法接受。
想着曾经给母亲“明年我过五十,您过八十岁生日,我们一起好好庆贺一番”的许愿,默念着外甥女“我总想问外婆,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生日还没有到,您却已离开,一声‘再见’也不说,再也不看我一眼地离开。”的话,我很明白,一个多月前就急着要给外甥女过生日的母亲,已经扛不住重病的折魔了,不然不会走得这样急的。只不过短短二十多个小时的救治,母亲就再也回不了她喜欢和眷顾的家了,匆匆又匆匆地走完了她七十八载人生路。落一片樱花,掉一片泪,全然不顾路人的诧异,任泪水随意流淌,心中只有“真的好想你”的哭诉。
“樱花飘落”,是当初想写樱花时,脑中总蹦出的几个字,也只是想在花落的时候凑几段文字,发些岁月匆匆的随感而已。却未料,我的人生真的是樱花飘落。如今写它,一字一句都是泪水中化出来的,字字都如片片飘落的樱花,句句都像母亲根根花白的发丝,弄得我满是伤心、满是泪。
以前,一直喜欢静静地看樱花飘去坠落,一瓣一瓣地如雪花,迎风高低起舞,终又是落于地下,由白慢慢化成粉红粉红的,铺满一地,以为好看。
而今,一样是看着樱花的随风起舞,轻轻落下,星星点点地落满花园,慢慢烟化成粉粉的红,如啼过我血似的。才觉晓,飘落的是樱花,离去的是母亲。
低头俯看那殷殷的樱花,一片一片,映着残红。拾起那残花残梗,真像母亲离去时枯瘦的身躯,不忍将它随意丢弃,怕它伤心、怕它痛,只轻轻地将它放在泥土里,远远地看着,不想扰了它的梦。
樱花飘落,落于我耳旁,轻轻拍着我,像在对我的埋怨。是的,假如那时,让人打理一下那樱树,或许母亲早就可以看见樱花开了。假如在母亲走的那天,将那五瓣樱花铺就在母亲身下,或许她的一切都会重生。假如将她亲手栽的樱花,塞几朵在她手里带往天堂,送给她那里的亲人,或许她的神伤不会再有。可是已经没有那么多假如了······,只待以后年年清明,将倾注了母亲思念的樱花献于她的坟茔前,作为我的祭奠罢。
樱花飘落,滑落于地下,弃我而去,再添一份心碎。那幽幽的“好花不长开、好景不常在”成了她的绝唱,那“车开得慢一点,早点回家”的叮咛,成了我永久的期待。从此,没了娘亲,再也不见到她在小区路边等我回家吃饭的声影,只剩下残香孤烛与我顾影相怜,屋里再也听不见她轻轻的脚步声,只留下她往昔的笑语在我耳边萦绕。从此,我的世界不再完整。。。。。。
樱花飘去,它还会再开,那是肯定的。而种花人能否再来,我不知道,但我期许着她再来,期许着她再入我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