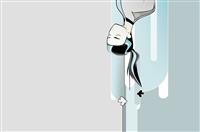我自谓是一个文人,我的手是拿笔的手。
我用右手拿笔。从小时候开始,我这只手拿过铅笔、圆珠笔、钢笔、毛笔、画笔,我写得一手好字(当然不可跟书法家相提并论),也曾经画过一段时间的画。我的食指和中指由于长时间夹笔,形成了硬而突出的老茧。就是现在我以电脑代笔了,我的这只手仍然是一只拿“笔”的手,当它在键盘上灵活地敲击着的时候,他仍然在履行“写字”的职责。
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有一个抛不开的情结:我很希望我的这只手能够拿一拿枪!而且有一段时间,我竟为此而着迷。
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弟兄四个,却没有一个当兵的?没有一个成为如宋祖英所唱的让人想死了的“兵哥哥”,没有一个成为如阎维文所唱的长在哨所旁的“小白杨”?每当在餐桌上,有人谈起谁当过兵,而且为此而自豪、为此而干杯的时候,我只能笑说当过“红小兵”。
我对当兵的崇拜,我对枪的神往,来自于从小所看的那些小人儿书,来自于那一部部战争题材的电影。记忆最深的是《小兵张嘎》,他从鬼子手里夺得一把手枪,藏在树上的喜鹊窝里,其智其勇,其危其险,让少年时的我崇拜不已。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只要有一个当兵的回来探亲,我都要追在后面听他讲故事,问他有没有打过枪,是手枪,步枪,还是冲锋枪?直到十七、八岁的年龄了,还一如孩提时代那样好奇。
为了过一过枪瘾,少年时的我曾经用木头做过枪。那时正是样板戏红火的年代,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排样板戏,而样板戏里有不少道具枪。只要有样板戏来村里演出,我就会摸到后台去看那一把把和真枪差不多的木头手枪,回来就依样画葫芦,找一块木板用锯子锯出枪的形状,然后再用凿子慢慢地刻削,成型后再用黑漆漆得乌黑油亮,再在枪把下面系上一根红绸子,这样一把木手枪就做好了。虽然粗糙一点,但往腰间一别,还颇像一回事似的,那分神气,让我的一颗少年好奇之心得到了多大的满足啊!更给我们乡村孩子单调乏味的童年生活注入了多大的乐趣啊!每天晚上,我常常都是枕着枪睡觉。
长大了,走上工作岗位了,成为一个成年人了,这些假枪的游戏不能再玩了,但心中仍然埋藏着一种想摸一摸真枪甚至想打一回真枪的渴望,以至于经常做梦,梦中我拿着一把枪追赶坏人,我一边追一边瞄准,可当我用力扣动扳机时,枪却不响,变成了木头枪,坏人回过头来拿刀凶狠地向我刺来,我被吓得从梦中惊醒过来……我知道这是我心底的枪情结在作祟。
因此我就想有机会能摸一摸真枪,能真正打一回枪。朋友知道后,说这有何难,民兵打靶或组织军训时带上你就可以圆你的打枪梦了。这样的机会还果真来了。那次,朋友打电话给我,叫我某时某日在哪儿上车跟他一起去农场打靶。然而也许我真的与枪无缘,朋友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参与一个文化考察团在千里之外进行着我的文化之旅呢!
最近看一个反腐打黑的电视剧,剧名叫《罪域》。那些黑社会的头子、爪牙,为了谋取他们的非法利益,动不动就枪杀无辜,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枪成为他们实施罪恶的“帮凶”。而公安机关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他们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对穷凶极恶、负隅顽抗的罪大恶极分子,毫不客气地予以当场击毙!枪成为伸张正义的“英雄”!枪啊枪,有了你就会有罪恶,有了你也会有平安。既恨有你,又不能没有你!既要消灭你,又想拥有你!
我不知道我心中的“枪情结”是不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暴力倾向”?
现在,我已经不再对枪迷恋了,我的这只拿笔的手我想让它一直拿笔了。我想,一生与枪无缘,未尝不是人生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