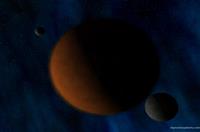
春天的早晨,阳光早早就开始敲打人们的窗户,俗话说:“一年之际在于春,一天之际在于晨”,那春天的早晨就更宝贵啦,但对于喜欢熬夜,不喜欢起早的叶晓文来说,哪个季节的早晨都是一样的。当晓文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又是差十分八点了,她虽然仍懵懵懂懂,却像受过训练一样,闭着眼睛都能把叠被、穿衣、刷牙、洗脸、梳头,这一系列每天早晨必做的功课,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完,并且达到优良的成绩。然后端起妈妈已经盛好的疙瘩汤,三下五下倒进嘴里,还不忘了梦呓般地抱怨一句“天天疙瘩汤,都吃恶心了”。妈妈接上说:“做别的你有空吃吗?就不能早起五分钟”。
晓文背起书包冲出家门时,是差四分八点,比平时晚了一两分钟,今天的点可是没怎么掐准,怕是要迟到。急行军到校门口,刚刚踩到上课的铃声。校门口到教室门口还有两分钟的距离,晓文还是迟到了。她小心翼翼地推开教室的门,里面乱哄哄一片,原来讲台上没人,老师还没来!晓文长出一口气,赶紧跑到座位上。同桌付建平说:“老师刚才来了,又出去了”。晓文得意地笑笑,拿出抹布擦干净桌面,然后把文具盒、课本、笔记、作业本一一拿出来,整齐地摆在桌面上,书包放进桌膛里,又把桌膛里的灰尘清理了一下。做完这些,她扭过头看看同桌,发现他穿了一件新衣裳,付建平对她说,他这件衣服是两面服。“什么叫两面服?”晓文还头一次听说,“就是里面也可以在外面穿。”晓文翻起付建平的衣襟,果然里面的样子和外面一样,只是颜色不同,也就是说,翻过来穿又是另一件新衣服,晓文夸赞说:“一件可以当两件穿,挺合适的。”付建平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常常会有新衣服穿。晓文是家里老三,穿的衣服大都是拣大姐、二姐穿小的,有时还穿妈妈年轻时的衣服或鞋,每年春节才能有件新衣,也是用给大姐、二姐做新衣剩下的边角余料凑合成的。不过晓文并不介意这些,看到别人穿新衣服也没什么感觉,好像拣剩理所当然。但晓文很在乎衣服的干净整洁,虽然没有多余的衣服可以经常换洗,但只要发现衣裤上有一个污点就要想办法擦掉,每天睡觉前一定要把衣服整整齐齐叠好,把裤子弄平整放在枕头底下压出裤线。
老师还没来,晓文拿出没做完的物理作业做起来。付建平做起美术作业,他画了擦,擦了画,一张画纸弄脏了撕掉换一张,还是擦来擦去的。晓文放下手中的作业,拿过付建平的图画本画起来。晓文的美术很好,每次作业都是优秀,付建平的美术可是他的弱项,几乎每次都要晓文帮忙改几笔,才能混个及格或良。这次的作业比较复杂,付建平没有一笔画对的,晓文无从改起,只好干脆自己替他做了。很快,一只像模像样的飞机跃然纸上,付建平说:“这回肯定能得优。”晓文说:“如果老师看出来不是你画的,那就不及格了。”
第一节课是化学,过去半堂了,班主任来了,说化学老师临时有事这节课上自习。下面有欢呼声,是那些不想上课,又被逼着必须来学校的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班主任说:“不上课怎么把你们乐成这样!不想上课就别来吗!”一个学生接了一句:“不敢不来呀。”得,把班主任的训话勾出来了。自从这位班主任接手语文课,晓文就开始自学语文了。在晓文的记忆里,班主任几乎没上过一节完整的语文课,在她的课堂上,只要有人惹了她,她就放下课本,开始训话,一旦训起来少则二十分钟,多则一节课,有时甚至压堂。总有那不怕死的、嘴欠的学生,于是语文课就堂堂上成了政训课。晓文很怀念刚入学时教他们语文课的那位老师,一位和她同姓、上了年纪的老头。晓文入学的第一篇作文,被这位老师作为范文在第一节语文课上讲评。那天晓文病了没上学,放学后,几乎全班女生一起到晓文家探望,并告诉她这件事。第二天晓文上学后,语文课前,那位语文老师来到晓文跟前说:“做我的语文科代表吧?”别的科代表都是后来班主任指派的,唯有晓文的科代表是本课老师亲点的,这说明晓文是名符其实的,晓文为此着实骄傲了一阵。在这位老师的语文课上,晓文全神贯注,听得极认真,老师提问,她总是第一个举手,课后收作业,从没有拖延交作业的时间,科代表当得称职、积极。换了班主任教语文之后,没课可听,没言可发,没作业可收,晓文这个科代表成了空衔,闲置一边了。不过又有了另一个身份,成了班级的秘书,运动会写宣传稿、某同学做代表发言、写倡议书,……凡是班级有需要动笔写的事,班主任都会派到晓文的头上。
晓文很头疼班主任的喋喋不休,不愿听那些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做别的又做不下去。这节自习课,晓文本打算把没做完的作业赶出来,回家就不用做了,可是班主任又唠叨上了,像噪音在耳边嗡嗡地响,响得头直晕,脑筋根本转不起来了。晓文不得不听,拿支笔在一张草纸上乱画。这回班主任唠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二十五分钟,差五分下课的时候总算停了下来。班主任草草总结了一下这次期中考试语文科的考试情况,便把批完的语文试卷发了下来,这是最后一科试卷了,其它科的试卷早发了,晓文和付建平就等着这张试卷好合分。他们俩不管是大考还是小考,每次考完试卷子发下来,两个人就开始各合各的分,然后比较谁分高,谁分高谁就是班级第一名,因为他们俩是班级学习最好的,没有谁能超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只要他们俩人比较出高低,班级的第一名就产生了。下课了,两人谁都没动,一张卷子一张卷子地加分。付建平的总分出来了,等着晓文,晓文的总分也加出来了,比付建平低了5分。付建平说:“我再帮你加一遍”,加出的结果还是晓文比付建平低了5分,这次付建平胜出。晓文有点沮丧,心里埋怨自己,数学那道5分题不该错,马虎了,要是那道题没扣分,起码打个平手。
午后自习课上,班主任突然把付建平叫了出去,在教室外谈了半天,回来后付建平一声不吭地收拾东西。班主任又马上把晓文叫了出去,原来是谈换座位的事,晓文问:“就我们俩换吗?”班主任说:“是。你们俩是班级学习最好的两名同学,分开坐,带一带别的同学。”晓文想起上午物理课上做作业时,物理老师停在她和付建平的座位前看着他们,晓文抬起头,物理老师笑笑说:“你们两个学习最好的同学怎么坐在一起?”一定是她对班主任说了什么,晓文虽然对物理老师印象很好,但心里还是不满她多事。班主任说:“付建平不愿意,刚才做了他半天工作,你呢?”晓文也不愿意,但还是说:“行吧。”晓文心里明白,说是让他们帮别的同学,其实就是怕他们俩好起来。晓文心想,真是多虑了,她是好学生,怎会像那些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搞对象的女生一样呢!晓文是不会虚度年华的,她一定会好好学习,让自己有真才实学,为理想而奋斗,当然理想具体是什么晓文并不清楚,但父亲常常这样教诲他们,晓文铭刻在心。不过晓文不善言辞,不爱多说话,她心里怎么想的老师们自然不清楚,当然即使清楚了,恐怕也不会完全相信,也要防患于未然吧。不管怎么说,老师是为他们好,晓文没有反对的道理,况且和谁同桌晓文也并不十分在意,只不过是熟不熟的问题,不换当然好,换了也就换了。晓文的座位没有动,付建平换到了晓文的后排,和一个很丑又最老实的女生同桌,晓文的同桌也换来一个很丑、在男生中也最老实的同学,外号叫“老蔫”。付建平同晓文斜对着,晓文几次回头想同他说话,付建平却总是低头看书,没看见一样。晓文想,他是不是怪她答应得太痛快,没有同老师争取,以为她愿意换座,起码是无所谓。晓文的确是有点无所谓,但她肯定是愿意同他,而不愿意同眼前这个“老蔫”做同桌啊。付建平从此不再理睬晓文,只一排之隔,却像隔了道鸿沟,两人一下就生分起来。他也从不搭理他的新同桌,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他在男生中也没有朋友,换座之后,付建平从早到晚几乎不说一句话,几乎只做一件事,就是低头看书。晓文试了几次之后,也不再想同他说话。后来因为付建平个子越来越高,又被换到后边去了。渐渐的,付建平在晓文的眼中只是靠着窗户站成一排的男生中的一个了,这时他要是主动同晓文说话,晓文都不知说什么,都会觉得不自在。
晓文对新同桌“老蔫”,没像付建平做得那么绝。开始她也不理他,还在两人课桌中间放一只长尺,警告他不要过界。偶尔“老蔫”的书本过了“界”,晓文就不高兴地怼回去,然后警告他,要是再“过界”就没收。晓文和付建平同桌时,两人常把暂时不用的书本摆放在两人的课桌中间,不分彼此。晓文是打定主意不理“老蔫”的,可是,一次数学课上,晓文忘了带圆规,问前后桌的人借,不是没有,就是没带,看看付建平,还是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晓文犹豫一下,只好破例问老蔫有没有圆规,老蔫没回应,像没听见一样,没说有,也没说没有,晓文心想,真够“蔫”的,一板子也打不出一句话来,晓文又问:“听见没有?”还是没有回应。晓文想,看来是报复我不理他,也不理我,不理就不理,晓文不再问,试着自己画圆。正费力地画着,一只文具盒慢慢爬到晓文的课桌上,晓文抬起头,看到老蔫正把自己的文具盒一点一点地推过来,晓文笑了,把推到眼前的文具盒打开,拿出了里面的圆规。这件事让晓文觉得老蔫人挺好,不该与他为敌,晓文撤走了“界尺”,也不再计较老蔫书本的稍稍“过界”,也打消了不理老蔫的决心。不过老蔫也实在没什么可“理”的,不管晓文说什么,老蔫只是用动作回应,就是不说话,晓文和他同桌一场,竟不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样,晓文有时甚至怀疑,他是不愿说话,还是不会说话?因为老蔫的不说话,两人虽然能和平共处,却总是不如同付建平那样融洽、默契,这让晓文偶尔会怀念和付建平同桌的日子,那些日子让晓文有一种暖暖的感觉。
这个北方小城的春天还是蛮漂亮的。街道两旁的树全绿了,浓浓的绿连成一片,使路变成了绿色长廊;黄色的迎春花开了,粉色的“胭粉豆”也开了,红色的鸡冠花像两条彩练伸展在路的两旁。城市由黑白变成了彩色。晓文尤其喜欢柳树刚绿时的颜色,那种嫩绿好娇艳、好鲜亮,把城市衬得年轻美丽。不过晓文知道这种鲜嫩的绿色好景不长,很快就会变老,然后没入所有树中,成为清一色的老绿。这时晓文每次路过柳树旁都会多看几眼,说不定下次路过就看不到这种绿色了。晓文还很喜欢小时候春天路边的槐树,树上的花絮到处飘着,像似放大的雪花,飘到路人的脸上、脖子里很痒,晓文常常看到路人一边从脖领里往外掏出钻进去的花絮,一边骂着“讨厌!”晓文却觉得很好玩儿,常常和其它小孩子们去抓飘在空中的花絮。当花絮飘尽,槐树花开了时,满街都弥漫着扑鼻的花香。现在却很少看到槐树了,晓文想可能是因为那些飘得到处都是的毛毛,人们不喜欢,卫生也不好打扫,所以种的就越来越少了。
晓文每天中午午休时间都会约上同学去市图书馆看书。今天在图书馆竟看到了同班的程光和冯力。晓文心想,这两个家伙平时课都不好好上,怎么到这来了,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晓文借出刚看了几页的那本小说接着看,没看多一会,头就晕晕的睏起来,晓文晃晃头、揉揉眼睛坚持住。她是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在图书馆睡觉的,否则,不但牺牲午睡时间失去意义,还会让人觉得是来装样子,今天尤其不能睡,有那两家伙在呀。晓文不断地晃头揉眼睛,总算挺住了没有睡,但头仍晕晕乎乎的,虽然眼睛盯着书,却没走几个字,其实每天中午都是这样,看书的效果很差。但晓文就是舍不得把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用在睡觉上,她相信“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晓文觉得中午看书虽然效果不好,但总是在学习呀,看得再少也是收获,时间过得也是有意义的,如果睡觉就是浪费时间、虚度光阴,晚上已经睡了,中午再睡这么长时间,生命和青春岂不是都在睡觉中度过了!晓文解决下午精神的办法,就是在午后第一节课上睡一会,少则5分钟、多则10分钟,午后就精神的很了。用10分左右的时间,换回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晓文觉得太合适了。
午后第一节是班主任的语文课,这是晓文最不好过的午后第一节,因为那宝贵的5到10分钟的觉不敢睡了。还好一周只有这么一天午后第一节是班主任的课,晓文怎样都能熬过去。今天的课一开始老师还讲了几句课文,晓文正庆幸,一个嘴欠的学生又说了句足以让老师训上一堂的话,得,又改上政训课了,晓文叹口气,很气那个嘴欠的学生。沉闷的教室里,班主任的独角戏自顾自地唱着,这个单调的声音杀伤力实在太大,下面的同学接二连三地倒下了,一会,同桌也倒下了,晓文扫一下旁边和后面的同学,喔,倒下一片了!班主任没看见一样,依然自顾自地讲着,连点间歇都没有。晓文看着站在前面,对着睡倒了一片的学生独自讲着的老师,心中竟莫名地生出一丝同情。晓文告诫自己不要睡,要坚持住,她是这科的科代表呀,谁睡她也不应该睡,她得支持她的任课老师,即便实在坚持不住了,她起码得做到最后一个倒下。晓文又开始晃头揉眼,还不断揉着太阳穴,强忍着这个催眠术般的声音对她的考验。可是,当她实在坚持不住了只想趴在桌上稍稍休息一下时,竟睡着了!睡梦中晓文好像听到唱歌声,是做梦吗?声音越来越大,好像不是,晓文一下坐起来,懵懵地四下看,所有同学都坐直了在唱歌,包括同桌,当然除了她之外。晓文彻底清醒之后,很不好意思,很气自己没坚持到最后倒下也就罢了,怎能成了最后一个醒来,她这个科代表带了个什么头啊!晓文皱着眉头,小声埋怨同桌说:“怎么不叫醒我!”晓文看一眼班主任,班主任正在看她,晓文赶紧避开了。
放学大扫除,班长检查扫过的地方,对正在扫讲台的晓文喊道:“叶晓文,你负责的这趟怎么扫的?重新扫!”如果是平时晓文会听,会照他说的去做。晓文也是班委会成员,干部开会时,班主任常告诫他们要团结,要互相支持,不能互相拆台。可是今天晓文翻脸了,她把扫把往讲桌上一放,横眉冷对地说:“你别只说不做,你不会扫地吗?你重新扫一遍吧,这样你的小红旗又会多一个!”前几天,班级的墙上贴了一张评比表,所有同学的名字都写在上面,然后根据表现往上贴小红旗,当然谁得的小红旗最多,谁就是最好了。这件事班长负责,他给自己贴的小红旗最多,遥遥领先,而晓文名字上边的红旗却只寥寥几个。晓文为这事早已对班长憋了一肚子不满,看在是班级工作的份上才忍了下来,她忍了他,他却来找她的茬!晓文想,那可怪不着我了。班长说:“这是你负责的,凭什么让我扫。”晓文说:“就凭你红旗最多,你最好啊!你既然红旗最多,你就应该多做。”班长说:“评比的事是老师定的,你有意见找老师提去!”晓文说:“别拿老师来压人,我就是有意见,凭什么我的红旗那么少?我哪儿做得不好了?”班长说:“你就是不好!”晓文说:“你才不好!你哪儿做得比我好了?凭什么得那么多红旗?自己使劲往自己脸上贴金,也好意思,这叫以权谋私!自己给自贴红旗谁不会,明天我也剪些小红旗给自己贴上。”大家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愣愣地看着他们两人吵,没人帮腔,也没人劝架。班长气得说不上话,扭头挤出了教室,有人冲晓文喊:“班长找老师去了。”晓文心里有点发虚,毕竟是她干扰了班长的工作,也影响了大扫除,转而一想,也没什么好怕的,自己也不是无理取闹,班长给他自己贴那么多小红旗就是不对。
第二天晓文上学,心里还是直打鼓,不知班主任会怎么处理她同班长吵架这件事。晓文走近教室,又听到里面闹哄哄的声音,每天老师来之前都是这样,但今天好像声音格外大,好像出了什么事情。晓文推门走进教室,一眼就看到墙上的评比表被撕掉一半,另一半也是这里少一条,那里捅个窟窿的。程光和冯力坐在评比表下面的桌子上,同一帮人兴奋地大声说笑着,见晓文进来,两人不约而同地看了晓文一眼,又继续嘻嘻哈哈。晓文猜想,一定是他们干的,程光带头,冯力帮手。除了程光,也真是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做了。程光是班里捣蛋学生的头,只要有违反纪律的事就绝对少不了他,他胆大妄为,像是天不怕地不怕,晓文觉得好像连厉害的班主任都惧他三分。至于冯力纯粹是程光的跟班,整天跟程光形影不离,是摇旗呐喊、为虎作伥的角色。程光高大,冯力瘦小,听同学私下里说,是冯力的妈妈出面找程光,希望程光帮助冯力,于是两人就成了看上去最好的朋友。谁都看得出来,冯力的妈妈是怕瘦小的冯力受欺负,实际上程光对冯力起到的是保护作用。这个作用的确非常明显,大家虽然对冯力很不屑,但由于惧怕程光也就都不敢欺负冯力,冯力在大家的眼中是名符其实的狐假虎威。晓文同他们绝对是两个阵营的,风马牛不相及,从没打过交道,甚至从没说过话,不知今天他们抽的什么疯,怎么帮起晓文来了。晓文知道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帮她出气,他们才不在乎什么红旗不红旗的,他们也不可能得红旗。但是,他们是帮了倒忙啊!晓文想,这下完了,老师要是看到评比表被撕了,还不得怎么气呢!虽然不是她撕的,但事情是由她引起的,肯定都得算到她的头上。晓文真想冲那俩家伙吼一声:“谁让你们撕的!”
语文课终于到了。班主任一走进教室,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几乎所有人都摒住呼吸,看着老师的脸色。大家知道,吵架、撕评比表要比平日那些捣蛋学生的接话、顶嘴严重得多,不知老师今天会是怎样的暴跳如雷。晓文没有看,她知道,今天老师肯定得训一堂,而挨训的主角,就是她这个从来只会被表扬的好学生。晓文低着头,等着“冰雹”砸到头上,此刻她的心情反倒平静了,能怎么样?天塌下来顶着呗!但是天却并没有塌!班主任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她只是脸色平和地问了句:“谁撕的?”,没有人回应,她也没有再问,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作文题,讲了讲要求,等大家开始写了,就把晓文叫出了教室。老师依然脸色平和地问晓文昨天是怎么回事,晓文如实地讲了一遍,然后说:“班长做事不公平,是假公济私。”老师说:“评比表的事是我让他弄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单独给他提,或者向我反映。”晓文想,向你反映不成了打小报告,她可不会那么做。老师又说:“总跟你们讲,要互相支持,不要拆台,尤其要支持班长的工作,在同学面前要维护班长和班干部的威信。你这样当众跟他吵,不是会降低他的威信吗?!他以后还怎么开展班级工作!”晓文心想,他本来就没什么威信。老师说:“你是班委、又是好学生,你都不支持他,那些差生不是更不听他的了!你写个检讨吧,下午班会上公开检讨?”晓文以为是命令,一抬头,看到老师征询的目光,赶紧点点头。晓文心想,干嘛还问她,难到她要是不同意,还可以不做检讨吗?!班主任始终没问晓文谁撕的评比表。
晓文的检讨写得很巧,不但检讨自己轻描淡写的,同时把对班长的谴责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晓文有点得意,她是谁,她是语文科代表,班级的笔杆子,在文字上做做文章可是她的长项。她可不能像别的同学那样在检讨里使劲批自己,就差骂自己了。她既要过检讨这一关,又不能太伤自尊,又要暗示出班长也有错。她本来就不服气,她觉得班长应该同她一起做检讨。晓文念完检讨坐下,心中暗自为检讨的巧妙窃喜,觉得这篇检讨实在称得上是高水准的作品。她看着老师,等着她的裁定,是通过,还是重写?这篇检讨显然不深刻,老师也肯定听出了其中的不满和不服气,也就是说,晓文虽然检讨了,但是她并没认错。晓文心想,要是老师不通过,让她重写,她还这么写!班主任看了一眼晓文,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却讲起了别的事情,没有对晓文的检讨做任何评说,也只字不再提吵架和评比表的事。老师的态度让大家明白,检讨通过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按照班主任平日的脾气和行事风格,这两件这么严重的事如此轻易的放过是绝对不可能的。晓文知道,若是别人干的,老师还不得讲上几节课呢,只因为是她叶晓文,老师才如此草草了事。晓文看着站在前面讲话的班主任,她这是明显的偏袒,谁都看得出来,可是她不怕学生说她一碗水端不平,她就这么做了!因为要偏袒她叶晓文,连程光他们都跟着借光不被追究了。晓文不由得心生感激。下课后,老师让人把剩在墙上的另一半破破烂烂的评比表全撕了下来,把那面墙壁清理干净了,晓文以为会重新贴上一张新的,但是没贴,后来一直都没有再贴,老师也不再提搞评比的事。晓文不确定这是好还是不好,不过有时在心里会责备自己,干嘛要吵架,把这件事破坏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