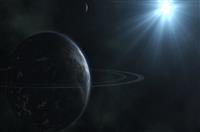十五
游手好闲了一阵子后,我重操旧业,认识了一个北京某服装品牌驻成都分公司的负责人,这个叫杨姐的女人,给了我两样东西,一是钱,二是梅裤子。
“这是小梅,以前在北京总公司当教官,现在来成都做我的助手。”杨姐介绍。
梅裤子西装笔挺地同我握手,脸上使用社交场合的常规笑容,说:“不好意思。”
我急忙也说:“不好意思。”
李姐就捂着嘴巴大笑,说:“有意思。”
身材高大的梅裤子略有些羞涩,斜着肩膀站在空调旁,不遗余力地保持着社交场合的标准姿态。
一来二往的大家很快就混的很熟了,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放在适应能力极强的梅裤子身上,一点也不为过。虽然我们也不大清楚自己到底是属朱呢还是属黑。
还记得第一次我带他去热舞会所玩,我瞅准了几个单身美女,喊他上去勾对,他宁死不从,说看看就满足了,一种憧憬未来的眼神在迪厅的闪烁彩光下时隐时现。无奈之下,我只好手把手的教他,在我和白言理论结合实践的共同指导下,梅裤子很快就脱颖而出,每天都朝着从一个外籍青年到本地操哥的目标中迈出坚实的一步。
梅裤子虽然不是成都人,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他对成都的热爱。你要知道,做为一个外来人口,要使同样的外来人口误以为他不是外来人口的话,首先满足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他必须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当地语言,梅裤子在清醒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后,开始勤奋的学习和使用成都话。
我们就经常会看见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场景……
在双楠的某个小饭馆里,梅裤子会大声的呼唤服务员:“小妹!掺茶!”
在青羊宫对面的公共厕所,梅裤子则低声的同把门的老太婆讨价还价:“能不能少点儿?好久涨的价哦?!”
在热舞喝酒的时候,梅裤子端着杯子微笑着搭讪:“美女,在喝酒哇?!”
在行进的出租车上,梅裤子跟司机套近乎:“师兄,最近油价涨得凶哦。”
最后,我们无一例外的目睹了使我们和梅裤子都失望到极点的结果,饭馆服务员和守厕所的老太婆以及酒吧的美女还有出租车司机都在不同的场所和不同的时间,针对梅裤子所提出的简单问题,在做出了较长时间的思索后,他们的答复是那样的如出一辙和不谋而和,他们会问梅裤子:“你说啥子呢?”
在梅裤子的眼里,这些人不仅对他缺乏足够的耐心,而且是如此的不善解人意。饱受打击的梅裤子把自己想象成钟子期,他斜着肩,盯着天空到处寻找他的伯牙,毫无疑问,除了满天的乌云,他根本看不见那个老伯牙的身影。
“老子再也不说成都话了,这帮孙子!”梅裤子说话的时候,成都的天空正飘着小雨,梅裤子的身影充满了孤独感和哀婉的悲剧效果,这是他的朋友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
对梅裤子身陷孤掌难鸣的尴尬境地,我们向他传递了同情和支持的的信息,然而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酒吧喝酒的时候,他仍然会使用他自以为擅长的成都话,仍然会端着杯子微笑着上去搭讪:“美女,在喝酒哇?!”
梅裤子在语言方面所存在的缺陷,虽然使他与他人沟通产生出许多的隔阂,但是一点儿都没影响到他在异地的短短数月内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交好手,这也是他与汉川的天壤之别。
梅裤子在女性圈子里快速聚集的人气,是我们这帮朋友有目共睹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中的细节观察到这种明朗的局势。
例如,老余在其后期人生失意前途未卜缺乏女人的时候,在嫉妒社交新星梅裤子崛起的同时,曾不止一次地同梅裤子进行协商,有时,甚至到了苦苦哀求的地步(注:刚刚不久,梅裤子在兵不血刃的前提下,易如反掌的接管了战友的女朋友,此女目前跻身于祖国的洗脚业,身材瘦小却手劲了得,下文中简称为:小洗)。
老余厚着脸皮说:“梅裤子,把小洗借给我搞一下,好吗?”
梅裤子对着老余翻一下白眼,说:“不行!”
老余哀求:“梅裤子,就搞一下,说话算话。”
梅裤子用藐视的眼神看着老余,说:“有你这样的吗?都饥不择食了!”
老余带着哭腔继续说:“你那么多,连一个都舍不得,真小气。”
梅裤子笑了,梅裤子说:“我靠,不就一女人嘛,有你这样的吗?!”
梅裤子的高风亮节让老余高兴极了,他于是闭上眼睛,开始遐想,嘴上还念念有词:“搞完了,再喊她给我洗个脚,嘿嘿。”
梅裤子一副心胸极其宽广的样子,笑着说:“孙子!”
再如,我们在慢摇吧玩的时候,老虫在扫视了一圈后,会充满忧虑的问我:“美女呢?”
梅裤子看我一眼,说声“靠!”就斜着肩膀到处乱转去了。
当我还在替他那引以自傲的成都话担心的时候,梅裤子已翩然而归,身后跟着两三个羞
答答的浓妆女孩,梅裤子指着我们,对她们说:“坐。”她们就很听梅裤子话的样子,按顺序坐下。我们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以饿虎扑食之势也按顺序坐下。梅裤子则在众人拍手称快的注视下,斜着肩膀傲然屹立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继续搜寻他的下一批猎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梅裤子同志做为一名社交好手的能力有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而且,我们对其未来的社交生涯,更是充满了无穷的信心。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小雪播送天气预报。
梅裤子到了,娘们还跑不得了吗?我们讲大灰狼的故事。
这年夏天的时候,雷虾子在成都呆不下去了,打算回老家新疆去帮父母种棉花。白言就给我打电话,说:“小B崽子真的要走了。”
雷虾子是在西门租的房子,小区环境不大好。我们仨兴冲冲的抬着两件绿叶啤酒上了二楼。
听见屋里传来雷虾子懒洋洋的声音:“谁呀?”
白言就大声喊:“你大爷我,快开门。”
“哪个瓜娃子,不想活了所?!”雷虾子全身只穿了条窑裤,看见我们手上抬着的啤酒,就瘦啦吧唧地笑了:“嘿嘿,我还以为是来收房租的。”
房间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只破沙发和几只凳子摆在那儿,就没有其他什么多余的东西了。
真他妈的热啊!梅裤子站在摇摇欲坠的电扇前面,解开衬杉的扣子,回过头问雷虾子:“你丫的半天不开门,准没干什么好事,是不是在打飞机呀?!”
雷虾子盘腿坐在破沙发上,说:“打球,老子在思考问题。”
白言就说:“就你那猴脑,最多想想娘们。”
雷虾子不乐意了:“你才猴脑呢,你才最多想想娘们呢。”
雷虾子一副很有思想的样子说:“我在想回去怎么发展,咋能把企业做大做强。”
梅裤子正在使用牙口接二连三地撬开绿叶啤酒的瓶盖,听见雷虾子陶醉在自己的高谈阔论中,就很不屑一顾地说:“你丫顶破天,最多从一个种棉花的上升到一个弹棉花的。”
“不许进行人身攻击。”“我岔开话题,说:“雷虾子,过来喝酒。”
雷虾子就过来了,雷虾子往喉咙里猛灌了一口酒,眯缝着眼睛看着我们,说:“你们就知道洗老子。”
我指责梅裤子:“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一个特奥会选手呢?”
白言答腔:“就是,别人雷虾子脑子不好使,你梅裤子脑子难道也不好使?”
梅裤子笑,看见梅裤子笑,雷虾子也跟着笑起来。我举起酒瓶,提议大家敬雷虾子一
杯酒,我说:“为了棉花。”白言说:“为了雷虾子。”梅裤子说:“为了棉花和雷虾子。”
雷虾子抽起酒瓶,朝喉咙里猛灌一口酒,然后严肃地对我们说:“挨球!”
二十四瓶啤酒很快就见底了,大家的兴致仍然很高,雷虾子就建议去酒吧耍耍。我说今晚就不要雷虾子掏钱了,我说我们仨AA制。
白言见我和梅裤子盯着他看,大言不惭地说:“我只有五十块钱,打的要二十,剩下三十全给你们。”
梅裤子鄙视地说:“靠!老白,你也太抠了。”
我也说:“每次都这样,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啥钱不钱的,说个JB!”白言从口袋数出三十块钱,扔在桌子上。
热舞会所位于顺城街某座大厦的地下室,我们进去的时候差不多快十一点了。
我们在服务员的引领下,穿越了一个个或瘦或肥或平或尖的屁股,摩擦了一块块有真材实料和没什么真材实料的没有胸毛和隐藏着胸毛的胸脯,昏头昏脑地来到了紧邻DJ台的一个小圆桌。
雷虾子表现得极其兴奋,手舞足蹈的到处东张西望。
“这才叫生活”。他对我大声叫嚷。
梅裤子用嘴巴“靠”了一下他,就端着杯子去吧台勾对单身美女去了。
雷虾子问我:“梅裤子干啥去了?”
我说:“梅裤子去问美女是不是在喝酒。”
雷虾子“哦”了一下后,再次问我:“他干啥去呢?”
我只好说:“他勾对美女去了。”
雷虾子就说:“我也去。”就扭着瘦瘦的屁股钻进了舞池。
梅裤子是在我抽完一支烟后回来的,他指着我,对尾随在他身后的两个姿色平平的美女说:“坐。”
跟着他介绍说,穿红衣服的叫娟娟,穿吊带的叫秀秀。
“一听,就是他妈的假名。”我对梅裤子说。
梅裤子说:“管她呢。”
这时候,雷虾子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搂着我和梅裤子的肩膀,好奇地问:“她们是谁啊?”我正想说一个叫娟娟一个叫秀秀,梅裤子就打断我,他抖掉雷虾子放在肩膀上的胳膀,
说:“娘们。”
雷虾子哈哈大笑起来,拿起桌上的啤酒,对着娟娟和秀秀摇着瓶子说:“卡妈,来吃狗!娘们。”
娟娟和秀秀马上站起来,对梅裤子说:“帅哥,那边还有朋友。等哈我们再过来。”
快融入人群的时候,那个叫秀秀的回过身,厌恶地扫了一眼雷虾子,嘀咕了句:“瓜娃子。”
我和梅裤子眼睁睁的看着两块可能到嘴的肥肉,就这么轻易的从身边溜走,不由地对雷虾子恨之入骨,
梅裤子骂:“你个狗日的,都怪你。”
我的心情也受到了影响,忙不迭地在一旁附和:“对,都怪你把人家吓跑了,多可惜呀。”雷虾子挨了我们一顿臭骂后,也觉得自己的泡妞思路有问题,于是就提出将功补过的请
求,一个人端着杯子往吧台去了。
我问梅裤子:“雷虾子到底行不行呀?”
梅裤子不屑一顾地说:“就他那熊样,能行吗?”
话音未落,雷虾子就一脸沮丧的回来了。
我问他:“你怎么跟别人美女说的呀?”
雷虾子告诉我他是依葫芦画瓢照梅裤子方式说的,他说:“我就过去问她,是不是在喝酒?”
我又问:“那那个女的怎么回话的?”
雷虾子没好气地说:“她说我废话。”
梅裤子惊奇地看着雷虾子:“那你就这样回来了?!”
雷虾子回答:“啊。“
梅裤子摇摇头,哈哈大笑。
雷虾子不无幽怨地自言自语:“今天真背,不适合泡马子,还不如打麻将去。“
在热舞会所的镭射灯光的扫描下,雷虾子一脸铁青,人生不得志的表情被我和梅裤子一览无余。
凌晨两点,我们带着满身的酒气和路人皆知的目的,被夏天的热风席卷着,脱离了这个充满欲望和几乎令人窒息的场所。
刘青龙说他要走了。
他散给我一支成都产的蓝骄烟,说他马上要去深圳毕业实习了。
我问:“神不知鬼不觉的你怎么都毕业了?!“
“都二十一世纪了,晓伟哥哥。“刘青龙提醒我。
我说你们怎么都走了。
刘青龙就问还有谁。
我说雷虾子你不认识,我说汉川你总认识吧。
刘青龙好奇:“汉川去哪?回武汉了吗?“
我说:“他去西昌了。“
刘青龙问:“去西昌干嘛?”
我说:“做装修工程。”
刘青龙笑:“各奔前程。”
我问:“钱非知道你走的事吗?”
他有些不满地说:“跟他说了,他说他忙得很。”
“对了,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呢?”刘青龙的好奇心又来了。
我说:“既没上学,也不上班,他每天就忙着睡懒觉和喝酒。”
刘青龙说:“你劝劝他呀,这样下去非废了不可。”
我说:“你搞错没有?!你让一个废人去劝说另外一个废人改过自新?!”
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打算尝试一下。
听说我要搬到他那儿住,钱非很高兴,他说:“太好了,又可以每天在一起喝酒了。”
我批评他,我说你除了喝酒,难道不试着畅想一下自己的未来。
钱非笑:“嘿嘿,伟哥,不会吧你?!”
我说:“你看看人家刘青龙,都马上本科毕业了。”
钱非还笑:“嘿嘿,伟哥,你说话的口气咋跟我爸一样。”
我说:“你还笑的出来?!我都有哭的心了。”
我看着钱非英俊少年的样子,想了想,说:“我看你还是找个班上吧。”
我把钱非介绍到杨姐公司的专卖店站柜台,说得好听点是导购人员,说得实在点就是个售货员。
“钱非工作表现不错,每天都站得很直。”梅裤子给我汇报情况。
我觉得奇怪,就问:“是站岗呢还是站柜台?”
梅裤子看我一眼,说:“靠!这是最起码的。”
老余不解:“要求那么高呀?”
梅裤子得意地说:“那是。”
老余当即表态:“我站得直!万一我下岗了,你请我去站。”
梅裤子笑说:“别呀,你去九眼桥站电线杆那来得多快呀,一次最少也得五十吧?!既满足了你站的愿望,又增加了个人收入,还繁荣了城市经济建设。”
老余就骂:“你个哈麻P,你才站九眼桥,你才站电线杆。”
觉得骂的还不过瘾,就继续骂:“你个卖勾子的。”
梅裤子哈哈大笑:“靠!急了,急了。”
我打断他们:“不准瞧不起战斗在第一线的阶级姐妹。”
……
没站几天,钱非开始叫苦连天。
“不信你去站站,太累了!”钱非抱怨。
我安慰他:“小不忍则乱大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
“生生死死。”钱非成语接龙。
我说:“该你了,老余。”
老余沉吟,说:“死去活来。”
我接:“来者不善。”
钱非接:“善者不来。”
老余汗流满面,说:“来者不善。”
我和钱非抗议,说不能重复。
老余汗滴禾下土,“来”了半天,说:“奶里奶气。”
我和钱非再次抗议,说不是成语。
老余蒙古大汗,悲痛欲绝地说:“奶大无脑。”
我和钱非拍案大笑。
老余不解:“你们笑什么?奶子大了是没脑子!”
我止住笑,说:“算是。”
老余如释重负,长出口气。
我往下接:“老羞成怒。”
钱非脱口而出:“怒火中烧。”
老余挠脑袋,重新出汗,在我和钱非催促下,吞吞吐吐地说:“骚球得很。”
我和钱非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余生气:“老子不来了,老子没你们有文化,老子喝酒。”
我们有个习惯,先随便找个地方喝酒,在家里或餐馆,喝的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兴致高还想继续的话,就转到酒吧再喝,喝的直到精疲力尽为止。
这个酒吧的生意不好,没有美女可以让我施展才华,我只好找客户经理喝酒。
客户经理塞给我一张名片,告诉我她姓殷。我看她那副模样,不由得联想起一个谐音字。
大多数男人在喝了酒后都会萌生欲望,我也概莫能外。
我问她有男朋友吗?
淫妇说有,不过才分了没多久。
我说那不是屁话吗?我说那我当你男朋友吧。
淫妇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笑:“好直接哦你,你都是这样泡妹妹的唆?”
我心说这还算直接呀?不是人多,早把你丫的给扒了。
我说我是认真的,我说你住哪儿呢?我说我送你回家吧。
淫妇说她没有家。“不得行,而且我今晚要值班哈。”她装得可怜兮兮地说。
淫妇看我一副失望的表情,就安慰我:“帅哥,改天嘛,以后有的是机会撒。”
我问她没有家是什么意思。
她告诉我,她才从老家上来没几天,原来是借住在朋友那儿,可是今天朋友的男朋友从外地过来了,她就不方便再住下去了。
“明天白天我还要去找房子,唉。”她叹口气。
“要不你搬到我那住嘛?!”我试探地说。如果她答应,我不仅救人于水火,而且也达到了霸占她的目的,不能不说是一箭双雕。
她竟然第二天真的就搬我那去了。
我和淫妇住一间,钱非和他一个北京籍的同学住一间。淫妇是晚出早归;钱非是不醉不归;我呢是早出晚归,有时候不归。哦,忘了告诉大家,当时我父母办理了退休手续后,在交大附近买了套房子,全家就彻底搬到了成都。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同时也为了追求自由,我只好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的,反正我也不嫌累,你就让我折腾吧。
我是个聪明人,不仅我自己这样认为,而且跟我打过交道的女孩也都这样评价我。
我一直怀疑淫妇是个淫妇。为了取证,我对淫妇说:“明天我回家住两天。”
她的回答让我很失望,她说:“随便你撒。”
我多希望听到的哪怕是句假话:“不嘛,不准你回去。”
次日凌晨两点左右,我摸黑潜入家中,径直走到床前,一个陌生男子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两个人睡得很香,丝毫没有察觉我的出现。
我先拍拍淫妇,然后拍拍奸夫。睡眼惺忪的他们一看见我,脸上立刻呈现出惊恐不安的表情。
我做了个让他们起来的手势,两个人一声不吭地起床穿衣。
淫妇几次想跟我解释些什么,却又欲言又止。我说:“爬!”
那男的低着头走了,淫妇还站着。我说:“爬!”
淫妇毫无愧疚地说:“现在你让我去哪儿哦?天亮了我再走。”
我怒不可遏:“爬!现在!”
赶走奸夫淫妇后,我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心想,狗日的胆子也太大了吧?!隔壁就睡着我哥们,竟然敢带个野男人回家。
晚上喝酒时,我问钱飞:“昨晚那个P婆娘带男的回家,你知道吗?”
钱飞说:“好象感觉到了。”
钱飞又说:“昨晚模模糊糊地听见你的声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说:“老子喊那个瓜婆娘爬了。”
结帐的时候,钱飞拿出一张一百的把单埋了。
我问他:“你发工资了?”
钱飞犹豫了下,说:“没呢。”
我问:“那你哪儿来的钱?”
钱飞笑:“伟哥,你就别管了。”
我之所以对钱飞的经济来源感到好奇,是因为他除了每月找家里要点生活费外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基本上都是我在埋单;还因为我最近经常发现自己钱包里的钱在莫名其妙的变少,而此前我一直怀疑是淫妇干的好事,我压根儿没把家贼着两个字跟我的兄弟联系到一块儿。
晚上睡觉前,我重新清点了钱包里的钱。明天不会又少了吧?!我心想。
第二天起床,我打开钱包数了数,少了一百。
兴许是钱飞的那个北京籍同学干的。我妄加猜测。
又到了晚上,我守株待兔地装睡,我想看看到底谁是这个家贼,然后在他作案的时候当场抓住。我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大半夜,也不见贼娃子现身,最后,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当我看到钱包里的钞票又少了一百时,我对自己嗜睡的恶习懊恼不已。
没办法,我只能采取突击审讯的手段。我走进隔壁房间,单刀直入地问北京:“你是不是拿了我的钱?!”
北京很憨厚的样子,回答:“没有。”
我恶狠狠地又问:“真的没有?!”
北京依旧很憨厚的样子,回答:“真的没有。”
我转而问钱飞:“那是不是你拿了我的钱?”
钱飞笑:“我没有啊。”
我说北京你出来一下,我说我有话跟你说。
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谁拿的?”
北京进行思想斗争。
我动之以情并晓之以理,说:“你是我表弟刘青龙的好朋友和同学,我相信你,我如果报案的话,后果会很严重。我只想知道是谁拿的,仅此而已。大胆地说出来吧。”
北京吞吞吐吐地交待说钱飞一大早拿出一百的一张买烟,至于钱飞是否偷我的钱,他没有亲眼所见,所以无法做证,但他可以保证的是他从没有做过这件不道德的事。
我说:“够了。”我假惺惺地拥抱了他,说:“辛苦了!”
我大踏步走进房间,对钱飞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吧。”
钱飞说他不承认。
我说:“北京已经交待了。”
钱飞冷笑。
我说:“大丈夫敢作敢当,你就承认了吧。”
钱飞嘲笑。
我火冒三丈:“你他妈的太让我伤心了。”
钱飞的所作所为深深地伤害了我,那个在我住院期间一把屎一把尿悉心照料我的钱飞到哪儿去呢?那个跟我有着共同爱好摇滚的钱飞到哪儿去呢?那个跟我朝夕相伴一起打架一起喝酒一起泡马子的钱飞到哪儿去呢?
“钱飞去北京了。”白言告诉我。
老余感叹:“没想到他会做这种事。”
梅裤子检举揭发:“闪了嗦?招呼都没打一个,到处找公司同事借钱,还把拿去维修的打印机给卖了。靠!”
我重重地叹口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