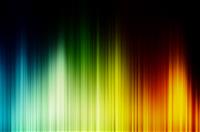一个星期后。
我走出柯华家的门。
2001年的3月依然冬天般寒冷。天是阴的,光秃秃的树枝没有发芽的迹象,伴着风声,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躯体在冰凉的世界中无声的哀鸣。
我慢慢而疲惫地走着。一辆出租车停下,我打开车门坐上去。
“去哪儿?”
“医院。”
“哪家医院?”
“哪家都行。”
医生说我已经不适合药物流产,必需要做手术,我面无表情的说:行。
走出医院的门,天已经开始下起了雨,中间夹杂着零星的雪。手术台上翻山倒海般的疼痛仍未消除,我的腹中像是被掏空了,只有血管在流淌着生命。我疲惫不堪,疼痛自腹中向周围扩散,我惨淡地对自己冷笑,迷蒙地看着前方说:对不起……
拖着沉重的身体走进营业厅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然后打开已关很久的手机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接电话的母亲,我很好,不用牵挂。
后来,又给柯华打电话,问她何时回来?而柯华却说她已回来了,现就在家里。
雨夹杂着的雪下得越来越密和急了,不觉间已完全变成了大雪。我的头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湿透,天也不知什么时候完全的黑了,路上的行人突然变得稀少,天地万物异常萧条。我孤影飘摇在雪中哭泣,痛苦不堪,那种折磨越来越深刻,我只希望能有鞭子在我身上狠狠地抽着,以减轻我无以复加的痛苦。
空气中微弱地传着我口中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你不该来这个世上,所以,我不能要你……
我对不起你,我把你的孩子杀死了……
口袋里手机铃声不停地响着,是柯华吗?她等我已等急了。但我的肢体已没有力气去拿任何东西。直到走到柯华的门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按着门铃,然后在柯华的惊叫声中栽倒在地上。
醒来时柯华坐在床边,正着急地看着我。看我睁开眼,她深吸一口气说:“天哪,你终于醒了!我刚刚在说你五分钟之内还不醒来的话,我就打120了。”
我闭上眼睛。听到她问:“你出事了?”
我没有回答,没有力气,也无言可答。腹中一阵阵的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咬牙承受着。我必需承受,那是扼杀的无辜生命后必需受到的惩罚。
“那天你找我,我就看你怪怪的。”柯华又说。
我微张开眼,下身不断流出的血液让我不得不挣扎着起来。一阵眩晕让身体摇晃,柯华慌忙扶住我,在她无意回头的一刹那,床单上浓浓的血迹让我听见她又一声的惊叫。
我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做任何的解释,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虽满脑子的疑问与担心,却也不再问我。
半个月后,我租到了一室一厅的小房子。然后我在周围所有的人中突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只知道我手机号码的柯华永远打不通我的电话。
房子里什么也没有,我每天坐在那张小床上孤独地思念着武兆磊。半夜醒来,穿上他的衣服在黑暗中绝望地哭泣,绝望地在房间里来回行走着,绝望地蜷缩在墙角呻吟。我颤抖着身体口中念着他的名字,我用刀片慢慢划伤着自己的皮肤……我不知该怎样摆脱这种痛苦,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我开始不停地吃东西,不停地吃。
后来,我在烦躁中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想死吗?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你要去工作。
一个半月后。
我到一家房地产公司面试,后很顺利的通过复试。最后总经理与我交谈的时候,在我的简历上盯了片刻后问我原来在哪家房地产公司。当他听完我的回答后脸上略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温和地笑着说:你的条件不错,我们再比较一下吧,这也是需要缘分。
两个月后。
我进了一家广州注册的保健产品公司。我应聘的是普通业务员,但个头不高的营销经理对我说我可以做业务经理。这种反逻辑之外的答案让我顺理成章的满腹疑问,但我还是留下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就是想工作吧。而仅一周的时间,就感觉出了某种地方的不对,或许是因为付总经理(老板娘)的蛮横挑剔,或许是因为总经理的古怪刻薄,亦或许是因为公司氛围的不健康……我懒得去想,我认为那些和我没关系,我只要有事做就行了。但很快我却意外的发现所谓在广州生产的治疗仪,不过是在本市某处破旧小院子里,一间三十多平米的房间中产出来的东西。而市场卖价五百多的治疗仪,让我无意中在电脑和别的途径中明白了其实际成本只有二三十元。我不禁思索,它是保健产品吗?能起到真的保健作用吗?我咬着牙问自己:我怎么进了这样的公司?!
那天,付总出门没车,扭头让下班正走向门口的我给她打一辆出租车。当出租车停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突然对我怒吼,嫌我给她打了辆破车不说,车型还太小。但不等她说完的时候,我更加暴怒的冲她喊:“嫌破自己打去!租辆车还有这么多的毛病!”说完不理她的反应竟自走了。
所以,公司把我辞退了,原因是我能力欠佳。我拿着比实际工资少了三分之二的薪水走进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秘书一个人,她的个头太过娇小,我不得不低下头和她说话。她瞪着三角型眼睛面对着我凶狠的质问,红着脸说着这样那样的原因。她当然不明白,看上去很是文静的我为何这样的泼辣无常。
一天,我从镜子里端详着已是胖了很多的自己,思索着自己暴躁的脾气和性格的变化,深深厌倦起自己来。我想,如果武兆磊知道了我现在的样子,该会有多么难过和瞧不起我……
于是,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不能再堕落下去了,否则,你真得不如死了的好!
于是,我开始和同学又有了联系,开始减肥。
但我依然陷在悲伤的记忆里无力自拔。如往常一样,甚至在路上看见与武兆磊一样的车都会让我痛苦不堪,思念的复加仍时而会让我对生活几乎没有了希望。
我擦干眼泪,咬着嘴唇对自己说:一切会过去,会的。
半年后。
我在一家合资的装饰公司做了业务员,并很快喜欢上了这个行业。在公司优良的文化氛围中,我慢慢找回了自己,同时对3D与ptotoshop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刻苦而努力的工作,空余时间全用在学习设计中。再就是饿了吃困了睡,我不给自己任何考虑工作以外事情的机会。
所以,一年后,刚进入公司半年的时间,出色的业绩便让我晋升为业务经理。但我并未因此而增加多少的快乐,我依如既往拼命的工作,仿佛生活中没有了工作便不能活。
我的朋友都有了变化。欣源可爱的女儿出生了,从寄过来的照片里看,长得既像吴彬又如欣源般清秀。雪莹和男友愿望实现开了一家小型超市,虽然只是在一个小区里,也算不上什么规模,但生意还算不错。郑晓兵有了漂亮的女朋友,是一名骨科医生。而柯华也准备和她的男友结婚了。但我除了工作不可能有别的变化,心与灵魂已牢牢地钉在武兆磊那里,没有丝毫的空间给其它人。
不过,我已慢慢不再那样陷在痛苦里无法自拔而时常绝望,不再那样刻骨铭心的思念武兆磊,只要眼前不会闪过任何关于他的影子。我不知他是否已结婚,只知道那个项目并没有进展。那块地面上的破旧楼体在拆除之后一直没有再动的迹象。
我为他祈祷,祈祷他一切都好。
一天,我意外的看到了冷氏集团董事长的消息,他被捕了,非法买卖土地。我不由想到了冷傲雪,担心武兆磊会不会有牵连。但担心只能是担心,我除了为他祈祷,帮不了他任何什么。
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忘记我,每次我梦见他的时候,他一定也是梦到了我。我在半夜醒来时的哭泣,他在远方清清楚楚的听见了,并且也如我一样,孤独地抱着枕头,如同抱在怀中的他……
但我和他除了思念,再也没有什么了,我已永远的离开了他的世界。他的世界离我已越来越遥远,没有再回去的路。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伤痛的心慢慢有了起色。我把所有关于他的东西陈封起来,装进行李箱里,并在心里划了一处方格,把那些伤痛的记忆拢在那个格子里,尽量不去碰。
所以,两年后,我注册自己的公司时,最终说服不了自己,把公司取名为“忆格”。
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和父亲为我汇来的五万块钱,公司启动还算顺利。我的公司开在家具城里,只有5个人,一名接待,一名设计,两名业务员和一身兼多职的我。我尊重并真诚的对待公司里几个和我一样大或者比我大的同事,而他们也真心诚意地帮助我,努力的工作。
上帝厚爱我,没多久我便接到了第一单。两家夫妇外地来做生意,挣了些钱买房准备在这里安定下来。可手中没有多少余钱,所以装修标准不高。其实他们本来就没打算装修,而是在买家具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转到我的公司门前随便看看,或是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后来,也许是因为我的真诚与热情,也许是因为我的专业素养,也许是因为我为了揽下业务而给他们承诺装修结束之后满意再结算……总之,他们当天就都签了单。
“你看上去很年轻?”女人对我说。
我眯起眼睛笑,职业而含蓄地点点头,“是啊,我很年轻。”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言行越来越像武兆磊。
“你没有三十岁吧?”
“是啊,我用不了几年就要三十岁了。”
“你挺厉害的!”
“是啊,我也觉得是。”
女的笑,男的也笑,我笑着和他们对视一会儿,“年轻或年老代表不了什么,我相信你们看不走眼我!”
送走他们,我咬着嘴唇无奈地想到,我的流动资金没那么充足。
回到家打开行李箱,拿出武兆磊给我的那张卡。我注视着它,然后轻轻地放在唇边亲吻着。那张卡里有多少钱我并不知道,但,是武兆磊送给我的,不管里边有多少钱对我来说都十分珍贵。我原是想着老了以后慢慢地去花掉,那样他就算是时常陪着我了。
但我没有想到,上面会有十万块钱。我知道那时武兆磊的手里并没有太多的钱,他当时的投资情况和收入来源我大体知道。
我不禁哭了,思念又把伤疤无情地撕裂开……
有些伤,一生的时间也不能去治疗。
我的工作态度是严谨的,思维方式缜密,每一处环节都没有丝毫的懈怠。效果图由我和设计一起完成,我相信自己富有个性的创意,并自信自己在设计方面的天赋。我对工程质量的要求近乎是苛刻,工程实施过程也严格,这并不是因为什么目的,确是我天生的一种性格。
装修完,两家人都非常的满意,而我因此也得到了更多的益处—他们朋友几家都是在一个小区中买的新房。所以,经他俩对公司和我的夸张式的赞美后,那几位朋友也相继成为我的客户。
我天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工作到凌晨很快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即便是工作到早上三、四点中,睡一会儿后,照样精神焕发的上班。这让公司中的每个人都很是佩服。但我知道自己没有理由让别人跟我一样的工作。对于工作的态度,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强求不来。对于职员考核标准我只有一个原则—数据说话。
我孜孜不倦的投入在工作中,无暇去想任何其它的事。上帝依然厚爱我,公司成立一年后,我的公司已在市场上站住脚,公司在人员上也翻番,已有二十个人。而公司制度也不断完善,我的公司已逐步正规化。
三年后。
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我开车去柯华的住处,接她一起去参加郑晓兵的婚礼。
之前的早上,我坐在床边呆坐一会儿后,终于打开尘封已久的箱子,找出那件我最喜欢的灰白色皮草开身毛衣,黑色暗方格裙子和深灰色暗格呢外套。穿好后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想着武兆磊在给我买这套衣服的时候,眼前一定闪过我穿上之后的样子。
柯华上车后我拿起身边的一个纸包给她,里边是她向我借的一万块钱。她再过两天就要去上海,一个人。她和男友在准备结婚的前一个月突然分手,我不知道原因,她不说,我也不问。只是后来她打电话借钱的时候,我意外的问:你手里一万块钱都没有吗?她停顿不久后说:阿雷你相信吗?我没有,我现在只有两千块钱。
柯华接过钱去放进包里,说:我会尽快得还你。
我笑笑,“到那边自己保重。”
她看我一眼,眼圈红了。
婚礼在酒店的二楼,新郎郑晓兵神清气爽,挽着漂亮的新娘幸福溢于言表。婚礼举行得庄重而不失热闹。
柯华肚子不舒服,坚持到宴席快结束时,起身去卫生间。她还如同学时的样子让我陪着她。我陪着她走出大厅,在卫生间的门口却发现上面竟然贴着:厕所暂停使用,请至一楼或者三楼。柯华嘟囔一句拽着我往楼梯口走去,而一楼卫生间前正站了几个等待上厕所的人,柯华皱着眉头说:“真够呛,星级酒店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我笑起来,同情地望着她,“今天人多。我先去那边坐会儿等你。”她心情已不太好,“你去吧。”
我在靠门边的沙发上坐下。一楼是零点餐厅,无意扫一眼人并不多。吃饭的点也已经过了。静坐一会儿,一只手习惯性地抚摸着手腕上的表。手表是三年前情人节时武兆磊送给我的,牌子和我当时送给他的手表一样。武兆磊的样子瞬间又闪现在眼前,轻轻叹口气低头打开包,拿出两份房间结构图纸和一份效果图用心的看着。
“祎文。”
我无意识的抬起头。
武兆磊正站在面前。
我的心猛地跳动一声,看着他慢慢站起来,而后竟忘记了和他分开的原因,几乎要扑进他的怀里。我咬着有些抖的嘴唇,看着他的双眼。他的眼中太多复杂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递过来,我没有勇气再看他。
“你好吗?”他问。
“还好,你呢?”我的鼻子发酸,眼中溢满了泪水。
他没有回答,接着问:“现在在做什么?”
“开了一家小公司。”
他微微笑笑,“我料到了。”
我的心依然猛烈地跳动着,皱皱眉头想把眼中的泪收回去。他的头向一边侧去,斜着眼睛盯着我。
我张开口想要跟他说什么,却看见柯华急急的向这边走来。我犹豫一下深深吸一口气,匆匆收起图纸从他身边走过,他抬起想要拦住我的手又止住了。
柯华看看我的脸色,又看一眼我身后的武兆磊,问:“你有事?”我苦笑,说没什么事。柯华又盯着我看两秒钟,然后说她哥哥来了,家里出了点事先回去。还不等我张口她又说:“你不用送我了,我打车回去。你跟郑晓兵说一声。后天走的时候给你电话。”说着急急忙忙地走了。
我回头寻找武兆磊,他正向大厅的一角走去,走到一扇门后,在那儿看着我。我走过去。
“你来干什么了?”
他的口气不好,刚才见到我时脸上的喜悦已被一种复杂的情绪代替了。但我习惯他的这种霸道,习惯他在我面前某些方面的强势。
“参加朋友的婚礼。”
他的嘴唇动一下,眼中闪着寒光和无奈,“你的婚礼举行了吗?”
“……没有。”我的脸无力的转向别处不敢看他。
“还没结婚吗?”
“没有。”说着,我鼓起勇气转过头看着他,看着他一秒钟都不离开我的眼睛,“你,你过得幸福吗?”
“幸福啊,挺幸福,一个人的生活最大的好处是自由。”他挑一下眉毛,“还有,可以随意让哪个女人来家里过夜!你说,我过得有多幸福。”
“是—吗,恭喜你又有那么多的女朋友,希望能有一个会永远留下来陪你。”我勉强地说,有些心酸,也有些生气,可能还有些醋意。
他冷笑,“可能是我命不好,我看上的,总是看不上我。我挖空心思地付出,却最终还是背弃我……”
“……对不起……”
他的眼中闪着泪光,盯了我一会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天我回到家突然人没了,已经是我生命中一部分的人消失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听着他的话,我不能控制悲伤的表情,脸抽动着,几乎哀求的说:“对不起,兆磊,你别这样……”
“你在惩罚谁?”
“……对不起……”
“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不能拖累你,我承受不了那样的负担……”
“拖累我什么?自以为是的女人!”
“……”
我的脑中很乱,咬着嘴唇想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想要知道他的生活。
“她呢?”
他皱起眉头,“谁?谁啊?!”
“她,你妻子。”我始终不愿提冷傲雪这个名字,他明明知道我问的是谁,却要为难我。
他的喘息变得粗重,目光中竟有了一种凶恶和陌生,声音像是从冰窖中传来,“我妻子?我老婆怀了我的孩子后突然失踪了,孩子也不知去了哪里,你能告诉我吗?她们去了哪里?”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像孩子一样痛哭着,委屈地看着他。他是这样恨我,我对他的伤害已经超过了最深的界限。
“对不起……求你……”
他看着我,目光终于慢慢缓和了下来。
不久,他轻轻地说:“我知道会再见到你的这一天……这几年过得好吗?”
我用力咬着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
“你比以前成熟了,也胖了些,但这套衣服穿在你身上还是一样的好看。”
我注视着他的脸,他看着我动动嘴唇露出一丝笑,目光中多了一份疼惜,“祎文……”
远处突然有人在喊着他的名字,他回过头去看看他们,又回过头来看着我。
楼上的婚宴已经结束,客人已逐渐走出来。
身后武兆磊的朋友又喊他,他们已吃完饭准备走,在那儿等他等不及。武兆磊表情复杂地看看我后向他们走去。
我看见了向我微笑的郑晓兵,擦掉眼泪走到他跟前。他看出了我的变化,也看见了站在大厅门口的武兆磊。他无言地笑笑,沉思一会儿安慰我说:“你没事的。”然后拍拍我的肩膀转身招呼其它要离去的客人。
武兆磊已走出去,我的脚不听使唤走到门口。他在车边站着,他的车旁边停着的是我的车。他看着我,不久后打开车门坐进车里。
我的脚停在了原地,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他。
他的车依然不动,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我抬起手扶着身旁的柱子,流着泪,表情却慢慢冷漠。我知道,他是看清了我的。我想,他是否知道我有多希望跑过去,坐上那辆车,然后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和他一起回到一起生活的家……
但是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我,告诉我,错过了的爱,是无法再回头的……
但是车里坐着最深爱我的人,他在那里静静地等我,等我回头,即便我那样绝情的离开了他。
我们能重新开始吗?不能。真的不可能了。几年来日复一日思念累聚的痛苦煎熬不堪回首,支离破碎的我该怎样重拾这份沉重的情感?我能吗?我没有那份勇气……我们爱得太深,伤得也太深了,无法弥补。我们已彼此走过,两条平行线相交过后,距离只能更远。剩下的时间仍需我一个人去走,虽然这一生他已烙进我的生命。是啊,他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牵动着我的灵魂,永远……没有人再如他一样的打动我。他是永远让我心痛的那根弦,我不想也不能去忘记他,他是我永远的爱人……
时间慢慢地走动着……
参加婚宴的人已经走完了,不知什么时候大厅外只剩下我一个人。
看着武兆磊的车,我坚持的底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那辆车诱惑着我,车里坐着的那个人我至今深爱着不能自拔……
他此刻在想什么?他伤心吗?生气吗?我心疼得想着他悲伤的样子。
我用力地咬着嘴唇,乞求着,乞求上帝不要让他痛苦……
我太自私了,上帝让他爱上了我,却是为了让我去深深地伤害他……
可我既然不能忘记他为什么还要离开他?我要去找他,找回他……我终于迈动脚,而在那一刻,他的车突然迅速地开出停车线,极速向外冲去。
他的车高速冲向门外,致使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刹车太急,而整个人从车子上面弹出去,摔进了路旁的花池中。
我怔怔地望着眼前所发生的事。
我跑到骑车人的跟前。他正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色腊黄,停顿片刻口中突然骂:“他妈的,找死去吗?这么不要命!”
“你没事吧?”我担心的打量着他的举动,然后知道他并无大碍。
他看我一眼,奇怪的问:“你是谁?”
“我是从这儿路过的。”
他愣一下,继而感激地看我一眼,说:“没事,就是摔得身上有点儿疼。”
我心怀愧意的拿出钱包,掏出里边的钱塞给他,“拿着去买些药擦上吧!”说着也不去管他的反应扭头走开。
我把车开出酒店大门,驶向武兆磊的反方向。
我在车上大声的哭着,像孩子一样的哭喊,问这都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拿起手机,他的号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要告诉他我想他,这些年每时每刻思念的挣扎让我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没有他我过得有多么孤独和寂寞,我有多想能够一生守在他的身边。可是我的手在颤抖,一种力量支撑着让我按不动任何一个数字。
我把车停在路边,绝望地爬在方向盘上哭泣—哭喊—哭泣……然后像他一样在路上狠命地奔狂……
文:悠尔
草稿于2007.03.11 修改完成于2007.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