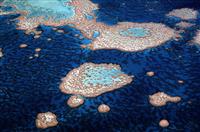舞蹈在暗夜或在光芒中。选择属于自己的表达。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阳光倾泻在脊背上。星空和云朵是天空中的花朵。从茧中逃出,在晨光中起飞。我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但却像雨水下落般知道要去的方向。
ABSA银行的巨大广告牌“what can I help you!”耸立在斜对面。每天早上十一点,站在研究所顶楼咖啡室的阳台上,手捧一杯滚烫的红茶,看银行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片街区曾是市中心最繁华和美丽的地段。
南非白人怀念1994年之前,种族隔离制度下理想国般的秩序和优雅。黑人却为了打破这假象而付出血和生命代价。94年黑人政府掌权后,首府附近原种族隔离区的黑人蜂拥而入。拥有国家其实一无所有,理直气壮却肆意横行。犯罪率和暴力冲突让白人选择放弃,N1高速路沿线的Centurion,Middleburg也因此成为中产白人阶级的新家园。留在首都的白人大多无力另觅新家,只有向郊区一迁再迁。
昔日的城区景象成为最美好的记忆。
站在这里望下去,炙热的阳光下几乎都是油亮的黑色发顶和肌肤。间或有年迈白人或乞丐孤独穿行而过。有几次和我的黑人同事努芳朵下去买新炸出来的薯条和芒果酱。紧拽着她的手,像只怕触礁的小船。骨瘦如柴的男性黑人或者身躯庞大的黑人女性,对比是如此鲜明。让我好奇。他们的声音和气味,动作和神态,让我怯生生保持着微笑。异乡人的表情。
宁愿这样远观。喧哗沉没在那里,无法将我淹没。
电话响。野兽的号码。
“几点下班?”“当然要到下午四点呀!”“我要去卡利诺恩看望一位朋友,一起去?”“现在?要请假,等下打给你。”第一次在上班时间接到野兽的电话。
十分钟之后,站在ABSA门前等他。十字路口。忘记了问他从那条街过来。正午的烈日如钢水浇淋一身,躲避在阴影下又怕他看不见。交通堵塞。喇叭声,叫嚷声和闪烁的红绿灯。
静立在流动的黝黑肤色之中,眼盲耳聋。
突然呼吸屏住。野兽的车堵在街口不远处,他的摁喇叭声我根本分辨不出。视线锁住他的面孔,站在那里。
他是此刻唯一与我相联的人。
他挥手示意我从另一边上车。坐在进车里,根本无法开动,被堵在那里。车里满是手册,黄页和名片。“我的办公室!”给他指了一下不远处的那栋大楼。他探了一下头,手却伸过来:“你的背上全是汗!”他的手在我的T恤下面。
他将我的手拽过去,放在他双腿间。窗外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你的脸红了!”他大笑,放过我。
半小时后,经过收费站,野兽放开车速。车窗开着,温热的风卷裹着蒸腾的大地的气息扑在身上。美丽的原野一派生机勃勃。旱季里一人多高的金黄色枯草踪迹全无,小小的丘陵点缀在浓淡不一绿色平原上。天空如蓝宝石般纯净。
除了风声。只有我们的车疾驶。仿佛在另一个的星球。野兽的眼睛里面,有另一个小王子。他给我隐隐讲过的英国求学记和非洲漫游记。在纳米比亚夕阳映成粉红的海边沙漠里,独自飞车,忘掉要去哪里。这个星球上没有他想要停留的地方。
他腾出一只手来,捉住我的头发。将我的唇带到他的味道里。
俯身在他的双臂之下,双腿之间。感觉到他在加速。
那种令人疯狂到想要脱身飞去的加速度。
听到他喉咙深处滚过的低吼。忽然被带进一个奔跑的世界。听到远处的雷声,嗅到唇边的血腥。小乃伸出利爪,月夜的十二点钟。
被猛地一把揪起来,“叫你停!小乃你也会不乖吗?想出人命!?”他低头看小左一眼。被我伸手握住。掉回到卡利诺恩的世界。
卡利诺恩是豪登省最大的钻石矿。被开辟成特色旅游景点,游人可以下到以前的旧矿坑里去。镇子不大,野兽直接将车开进中心区的一家高级餐馆。
他说,今天要会移民局的一个老朋友。坐在临窗的桌旁,他打了个电话。漂亮的英语无可挑剔。他要我假装不会英文,只跟他将中文就好。乖乖点头,先叫了东西吃。
他的朋友很快就到了。一位瘦高的阿非利卡女官员。两人极其熟捻地拥抱,问候。她的亲切看见我时立即变作阴沉和警惕。在知道我不会英语后,她稍稍放松,再没正眼看过我一眼。
上菜时,余光中见野兽将一个信封顺手压在她的餐盘下。若无其事地吃东西,窗边爬满紫色的牵牛花。
不是第一次被当作聋哑人。
约翰以前带我去见他的老朋友,我也是只管吃和微笑。只有一次,那个优雅的英国老绅士替我点了烟熏金枪鱼和美味的沙拉,令我顿生好感。稍稍留神,发现约翰和他除了有一搭没一搭投资钻石业之外,涉及人名尽数是政界要员。不禁抬头,看一眼约翰。
约翰和老绅士交换眼神,转头笑道:“帕瑞斯,你知道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吗?”我一愣:“当然啦,铁娘子,前英国首相!”“你对面坐的是她的前助手。”临告别,老绅士邀请我们周末去他在北方省的农庄玩。犹豫了足足一星期,还看了约翰特意拿给我的庄园的照片。美丽却荒凉的半荒漠牧场和仙人掌田。但约翰的目光让我最终却步。不喜欢被他捉到我的向往。
这次我是将耳朵和眼睛尽数封闭。但猜得出野兽和这个女官员之间大概有什么交易。就像约翰和那个老绅士,吃饭间老绅士将约翰提供给他的一些名字记在手边的本子上。
吃好正餐,我用中文对野兽说要点甜点。然后去洗手间。回来时他们正拥抱道别,两人的菜几乎没动。野兽叫打包,又要了好些饮料,说是请她办公室的黑人兄弟们打牙祭。
开出小镇,已是下午茶时间。野兽问我去没去过附近的中国佛寺。“听说过啊,台湾人出资修建的,号称非洲第一大佛教圣地!”“带你去看看!”他似乎心情很好。
远远就望见那一大片金碧辉煌的金顶,卧在小镇低矮的建筑旁,壮观却不协调。佛寺应是在深山流涧和云雾缭绕中吧。空荡荡的寺院中只有几个黑人和尚,香火并不旺盛。拾级而上,崭新的雕梁画柱和佛像壁龛,也像南非的天气一般色纯而明。但却没有气氛。
碰到几个澳大利亚人,他们站在大殿外并不进去,只是疑惑张望四周。一聊之下,他们原来是基督徒,所以只是随便看看中国建筑。野兽站在数十步开外,并不加入我们的讨论。待和澳大利亚人道别,我也顺石阶而下。夕阳西下,空旷而安静的庭院铺满一尺见方的青砖。
野兽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伸手要背我下台阶,孩子一般纠缠不休。吓一跳,毕竟是在寺院。
逃到门外的屋檐下,被他逼到长廊边。无处可逃。
他却安静地将我背对他,示意我看对面长蛇般游走在夕阳下的高墙。
风烈烈有声。静静停在他双臂的环绕之间。他的手从我的腰腹间滑过,落在胸口。
他知道我三个月后回中国。当被他握住,我听到的却是他心跳的声音。
他的气息。他的温度。一语不发间,被那重量击倒。
不堪的情欲之火,被捕的甜蜜。淹没在金碧辉煌中,飞来峰般的中国寺院如同幻觉。他的手将我唤醒。
突然间他松开手:“车停在那边,是吧?”
一路开向将落的夕阳,听野兽讲纳米比亚的童话沙漠和不见人迹的白骨森林。
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我平静的生活里。他应该永远是生活在别处的那个人。
“你若不是落魄,怎会被我捡到?”后来有一天,忍不住说。
而他在靠枕和被子的云朵里,安静地睡着。嗅到我手中的咖啡,轻轻皱皱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