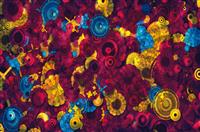已过而立之年,小时候的事情大多都被遗落于黄土。偶尔想回忆童年之时,就想起母亲。我们倚窗,她总是满脸的笑意。
母亲说起年轻时的劳苦岁月,甚至一路从她的儿时说起。我静静地听着,跟着母亲或哭或笑。母亲很坚强,很善良,我,爱她如一。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透玻璃温暖地照在母亲浅折的皱纹上,她面容红润。我将削好的苹果递给母亲,她的推辞抵不过我的坚持,最后,我们各自一半。
我说,我还记得门前的大枣树。母亲精神抖擞:还有咱家的老东屋。
对了,还有那口我们得跳起来才能够到的小轧井。关于它,记忆最深的就是它还曾把二姐的鼻子弹得流了好多血。不是因为调皮,而是要帮家里打水。
小小年纪你们没少帮我们干活,母亲满脸的心疼。我笑笑拉着母亲的手,我们并不介意,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这时候你怪懂事,记不记小时候你总是要跟我上地?你二奶拿的“割耳朵票”忘了没有?
我记得我从小一直很懂事。不过这“割耳朵票”我还真有印象,挺有画面感,我还一直以为那是梦境。记忆里我一直在哭,然后二奶就拿着一张崭新的一角钱在我耳朵上比划,是吓唬我。母亲笑着,那是我去地干活,天太热,你却非要跟着我。我也羞愧地跟着笑,仍然握着母亲的手。
母亲的手温暖而干涩。我掏出护手霜想给她搽上,母亲却执拗着说,农村人没那么娇贵,你看我脸上一辈子啥也不抹不是照样红润。我赶紧笑着附和,那是,说明妈皮肤好。
阳光依然斑驳,母亲起身,回屋里拿回一捧核桃。我用开核器剥开递给她,母亲不住地说,你多吃点,看瘦得成啥了。那一刻我笑中带泪,低下头,使劲睁着眼睛。略显苍老的核桃一个个地在我手中裸露。
我说,再给我说说以前的事吧。
那时候,你外公去世得早,你姥姥一手把我们兄弟三人拉扯大……你们姐弟四个都很乖,挨尖似的就在家门口等着我和你爸去地回来……母亲慢慢地说,我静静地听……
夕阳已褪去光华,却染红了母亲的白发。
遥远的天际,升起灿烂的红霞。
时光的焦距逐渐拉远,音乐响起,镜头中那一对母女倚窗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