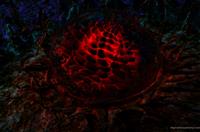全村的人都知道我爸死了。
第二天办葬礼,八个人憋足劲鼓着青筋把我爸从屋子里抬出去,我爸在棺材里,一动也不能动。他们踩在那些刚洗过雨,潮润贴着杂草的黑泥巴上,一个一个的脚印就像当年我爸背着我上学时踩在大雨下那树坎子里,我使劲的哭,我知道我爸这一出去就回不来了,我拼命的跟着棺材跑,可是他们八个人抬着棺材也要比我快上很多,渐渐的追不上了,我就扯着嗓子喊,喊我爸教我的诗儿,
小牛儿
要吃草
草儿嫩
草儿香
终于再也见不着人影,我哐当一屁股坐在了狗尾巴草的石头缝上。
我爸是个好人。全村人都夸我爸好,我爸长得斯文秀气,干农活却很能卖力,收谷子在咱那地方叫打禾抱把,我干农活时受不了那股煎泥巴的太阳,热的一身汗像在泥潭子里打了七八个滚,就偷偷的跑去抓蛤蟆,结果弄得后来满身是泥被我爸一手夹在腰上搂回了家。到家了青姨给我喝杯从井里压的凉冰冰的水,喝进嘴里甜到心坎子,就像我爸喝完常说的那句“真他娘的爽”。
我爸不仅务自家的农活,住在咱屋后那家就一个六十多岁的王爷爷,也有几亩田地,我爸每年都帮着他弄,王爷爷送我们些米,我爸收着,每天请他到我家来吃饭,就像待自己的亲爹。可是这个亲爹突然在某个刮着大风翻着乌云的下午把我爸给打了。
听说我爸被王爷爷打,全村的人都像蚂蚁一样挤了过来,我家那一米五宽的门被挤到了两米三六,可怜我瘦骨头弱身子,好挤歹挤终于跑了出来,奔着屋后那斜坡一路插上半山腰子,然后抱住三米高的大树使劲往上爬,明明是下午,铺天的乌云却把光亮全给挡住了,阴暗中天空几声巨响伴着闪电,吓得我犯了疟疾样一个劲哆嗦。我就这样虬着粗干看山下屋里那些密密麻麻的黑点,突然有个黑点冲了出来,径直向我这,速度很快。
黑点越来越近,我爸拉崩着脸,像一块刚擦了桌子的抹布又黑又青,他来到树下,抬头看向我,吼道:
“王八崽子还不给我下来!”
“我不下!”又害怕又委屈,我哭着跟他拗。
我爸做势欲爬上来,我拼命喊道:“你再爬我就跳下去了!”我一边看他一边转头向后瞄。
“你倒是给老子跳!”我爸没有停止继续往上爬,我慢慢往后挪,越挪后面越窄,终于再也不能挪了,我双腿夹住双手死死的抱着,生怕掉下去摔个脑瓜开花。
然后我爸爬到了我前面的树干底上,一只手像拎猫一样把我拎了过去。
到了家围观的村民都被王爷爷打发走了,屋子里王爷爷坐着,我爸站旁边,青姨低着头站我爸身后,我就瑟瑟的站在门槛上。外面刮了几阵大风后终于下起了雨,雨漂在我脸上,钻进我衣服胳膊里,我的衣服黏住皮肉,鞋子里的水用力踩就能挤出吱吱的声音,他们也不说话,我就像个木头桩子站那一动不动。
“进来吧栓子。”王爷爷叹了声气然后喊我进房间。
“还不滚进来?”我爸吼道。“洗个澡把衣服换了,病了又要花老子的钱!”
洗完澡睡在床上我像脑子进了蝗虫,左右翻滚睡不着觉,我是亲眼看见王爷爷压在青姨身上,我知道那是他们大人干的事情,王爷爷的嘴巴在青姨身上像狗嗅东西一样贴来贴去,手伸进青姨那橘黄色及膝裙子里面,他又咬青姨那黑黑挺立的乳头,像在品尝什么美味。
我告诉我爸,我爸听后勃然大怒,动手打我。我满屋子跑他满屋子追,王爷爷就坐在那里。然后我就对外面喊,我说王爷爷打我爸了!王爷爷打我爸了!然后一群人都跑了过来,挤进我家。
我才五岁,我爸就送我去十里路外的学堂念书。第一次进学堂,就看见那破旧的校门上左右挂着两扇铁门,左边那扇上面的螺丝已经掉了,向里面倾斜着,我们后来常常在那扇门上玩滑梯,张老师就训斥我们,说那门随时会倒,在那上面溜达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们扯着嗓子喊
“你们都是家里的命根子,摔坏了我可赔不起!”
张老师是个女的,听说是城里的大学生,她教我们语文,数学,音乐。她唱歌很好听,声音就像我家井底的水那样甜,她唱《十五的月亮》,还唱《妈妈的吻》,我特别喜欢听她唱《妈妈的吻》,六个小黑木桌凑在一起,往上面盖一张废布单,我们十几个人围在一起听她唱着,我边听边扭头看旁边的小伙伴,看他们听这首歌时的表情,像在炫耀一件自己心爱的宝贝。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伴我思念到如今
“张老师,妈妈的吻,和您的歌声一样甜么?”我听着张老师动情的唱着,突然很好奇。我的妈妈在生我时难产死了,我没有被妈妈吻过,所以很想知道。
张老师站起身来,她从旁边的塑料袋里翻出一样长方形的东西。
“呐!送给你。”我接住那东西,她摸了摸我的脑袋,“这是口琴,来,我示范给你看。”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它比山谷里流淌的泉水还要清澈,我听着那曲子,想起了我爸把我搂在怀里给我讲故事,讲关于妈妈的故事,他说我的妈妈长得很美,他们相遇在城市,一见钟情,然后我妈离开了那个富裕的家庭跟着他出去闯荡,但是他没能让我妈过上好日子,最后只能搬回了老家。
我不知道我爸爸讲的是不是真的,至少在我心里面,我的妈妈,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即使他们总是会嘲笑我爸,说他一辈子没走出过山村。
那首张老师吹的《梁祝》,就那样静静的陪着我走过难忘的岁月,之后我一遍又一遍的缠着她,叫她吹给我听,后来终于学会了,我就故意在有人的地方拿出口琴,得意的吹着这首曲子。我吹多了,小伙伴们也都会哼了,他们一群人在山里哼着,我就在那吹,偶尔打猎的村民经过,都会循着歌声看向我们,我们就哼的更起劲。这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承担了童年很多的无忧无虑。
我见到了我的妈妈。
我从未想过会再见到她。也想过重逢之后会跟她说的一万种开场白,但最后发觉千言万语言不由衷,不知从何说起。我看见了妈妈在远处向我招手,那是一片长满了大树的森林,密密麻麻的树叶遮挡住了天空,即便这样,妈妈的身影在远处也只能印出轮廓,又好似看花了眼,我使劲朝她的方向奔跑,感觉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颤抖激动的快要蹦出来,越来越近了,堆积多年的委屈忽然迸发了出来,停下脚步开始犹豫着是否要上前拥抱。这时她张开了手,也许是阳光太刺眼了,我感觉她的轮廓渐渐消消失,一点一点,她突然开始倒退。我憋不住了,疯了般向前追赶,此时才发现一万种对话一万次想念都不再重要,我只想她回到我的身边,我只想能够自豪的告诉别人我也有个妈妈,我只想过要这样再次拥抱再次重逢,原来我的内心也一直期盼着这样的重逢,那是谋划已久的自我宽慰,没有失去过妈妈的人又怎么会懂。我双手划动,然而越来越模糊,阳光却越来越刺眼,终于我睁不开眼睛,一切都消失了。“妈妈!”我大喊近乎绝望,再睁开眼,映入眼帘的却是自己房间黑白相间的天花板,墙角的蜘蛛网已经固执的搭建了很久,稀松的裂缝,熟悉的房间,还有一股莫名难闻烧焦的味道。
果然,这只是一场梦,唯一真实的,是眼角滚烫的眼泪和窗外照射进来的刺眼阳光。下意识的用手遮挡住眼睛。要迟到了!我一个激灵跳了起来,再也顾不上那些藏在内心深处的伤感,捡起掉在地上的白色背心胡乱套上,刚出房门,就看见已经被烧穿底部的水壶,刺鼻的焦味,我大喊青姨,却无人回应。已经顾不上那么多,我把火灭掉,拔腿就跑,比起水壶,我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屁股。
已是姗姗来迟,出现在教室门口张老师的表情让我内心仿若雷电交加,但转而发现,这表情又不是愤怒,而是惊讶多一点,甚至还有某种难以言喻的情感。她问我怎么来了,我回答说我家没人,我起晚了。看似简单的对白,却昭示着不一样的心理意境。但这都不再重要,她缓慢的走到我面前,全班的同学竟格外安静,就这样默默的注视着我,终于张老师要我坐下,我已然感受到气氛的不同寻常。
一直到后来才知道,那些在你岁月里烙下深深印记的,不一定是你最爱的人,只是她曾经用一种方式带你走进了岁月,走进了生活,让你发现美,就像大自然让你来到这个世界,给予你生命,让你去感受,你也会生生不息的去爱着这大自然。
张老师要走。我知道今天这种气氛的由来了。昨晚的梦又映入我的大脑,我觉得有点懵,带着淡淡的麻木。已经懒得去思考了。我吹了最后一遍梁祝给她听,她背对着我整理行李,等我吹完,她突然转过身抱住我:
“好孩子,”她哭着说,“喊我一声妈妈吧。”
“妈妈。”
我不只喊了一声,第二声,第三声,我越喊越想哭,设防多年的大坝终于决堤释洪,夹杂太久的情绪,像无法阻挡的汪洋大海吞噬了所有的一切。然后我就哭了,哇哇大哭,谁也劝不住。张老师已经泣不成声,她不再说一句话,只是紧紧的抱着我,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终于,她松开了手,用眼睛温柔的看着我。两行泪水刹那之间从眼里流了下来,她用手捧住我的脸,又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
“好孩子,你是男子汉,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坚强的活着!”说完她转过身,像是下定了决心,提起了行李就不再回头。
回到家里,他们说我爸死了,我跑进房间里,四只腿的短木床睡着一个被白布盖着的人,他们说那就是我爸爸。我慢慢的走过去,一群人在后面看着我,我听见有女人在后面小小的啜泣。
揭开白布,我爸像睡着一样静静的躺着,和平常睡觉时一样,假如把他弄醒了,他就会骂:
“臭王八羔子,还不快睡!”
声音是压着的,仿佛怕惊醒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