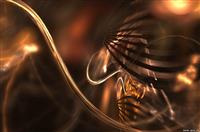假若你活过了八十岁,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儿,你会不会,把从前做一次回眸?
我没有到八十岁,我只是在深更半夜,读着过去的一篇小说,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人事,忽而有些想念罢了。至少,我还能把青春做想念,我还隐约记得些,当初的日子——
第一个事儿,是我总忘不了的人。
细细算算,也都整整三年了,再恍惚一想,是啊,再隔几日就真得是我们认识的三周年祭日了,似乎中间的时间,隔了十年般漫长。我对于中间的分分合合、痴痴迷迷都不怎么记起了,只是对于那天清晨,你拖着小皮箱、穿着灰灰的小短袖走进火车站时,可能听到了我的哭声,回头望我,就那一幕,定格在青春的最中间处,再隔几年都或许改变不了那幅精彩的画面。假若以后需要黑白色遗像,拿那画儿最合适。
放到平生去说,我似乎对人的眼睛情有独钟,我总以为人心所有的秘密都隐藏在眼眸中,在他眼神闪烁之时,必有声音在传递,他在说什么。回头去看,无数双眼睛在生命里凝望过我,可我渐渐都不怎么当真了,是梦耶,是幻耶,只当做是过往路上一个偶然的过客。
唯有那一双眼睛,好像是始终忘不了。
就在火车站,你憨憨的眼神,带着愁味蕴藉的阴霾,望我。
既然望尽了我的此生此世,我也当报还,原谅我永念永记。
这也使得,哪怕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在上海火车站,在杭州火车站,每每于喧闹繁华的人海深处回眸,总似乎是凝望见你的眼睛,就在看着我,一览无余的放不下、舍不得,而我也总能够如愿以偿地表现出惘然感,痴呆样,就那么傻傻地不知离去,不知呼喊,甚至也、忘记了哭泣,生命就好像在那一刹那是活过的。
等到后来人渐渐长大,也渐渐不把爱情当回事情,总爱告诉朋友:“这世间所谓痴情的人,往往是最无情。你想呀,他只对一个人痴情,那他是不是把所有的情都给了一个人呢?那他对其他人,岂非已经只剩下是冷漠无情?”
于是乎,我恍然大悟,原来世间真正的痴情应该是无情,我应当做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于是时间过去,我已经成功地变作了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当我再回头读到过去的那篇小说,读到了两个主角十年之后再相遇,已经是一个在病床上弥留之际,一个在病床旁哭的疯疯癫癫,我开口大笑,叫道:“总算是死了啊!”
叫这话时,我就好像是看见了你站在火车站之外,回眸望我,又是穷尽了我平生。
假若说此时此刻是那人躺在病床上,皮包骨头、身材也矮了一小截、完全陷入了昏迷状态,我是不是也能够站在旁边,不离不弃呢?亦或者,我就站在远远的城市某角落,在望云天,在望流光,在想念着岁月无情,匆匆而逝,我唯独不会想那人。只是说,死了也好,活着受罪,指不定死了还能变成白云映入我眼里,化成雨水淋湿我衣裳,融入大地黏住我的鞋子,盛开出花朵就在我身前,我只孤独地站在院子里,天高地迥地瞭望着,只以为这宇宙间的一切,无一不是你——
不必等我,我们终究再度相逢在人世,虽然,我已记不起你的名字,你已忘记我的笑容。
今时今夜,我把想念写成这篇文章,我只是想等将来我老年痴呆了,再偶然读到这里的文字,我记不起你的脸,我忘记了我们的故事,我只还知道你回眸时、待我神情,如此哀伤,如此甜蜜,如此不可一世地不可错过。
真应了当年我写给你的那句诗,“今生不必化蝶,来世也不用相约,我在我的江南,你在你的天边,从此也不必相恋,从此也只远远望着云天。”
你安心,我绝不会把我的话告诉你,我也定不能去打扰你而今的生活,我只是无聊极了,自作自受,写写这些无关痛痒而无声无息的文章,只是消磨我在人世间似乎该有的这一段无用的岁月,每一个深夜,总可能是有确定的那么些时间是用来消磨的,当做没事可干地虚度着,这也顶顶好的年月。
我在人世间辗转,早不是当年的我,也再不可能和谁在一起就没心没肺地疯疯癫癫地玩闹,再回不去了,但我还会在某些时候情不自禁地想起你的眼睛,在你看我时,假若有憨憨而厚道的笑,嘴角一抹弧线,我似乎才觉得我也曾经活着过,只是后来应了古老的诅咒“你本是尘土、仍将复归于尘土。”
夜深了,我又劳累了,稍稍动笔写几个字就觉得困乏,想睡了,你反正也不在,我也不必温暖了被子,也不必打扫地干干净净,只如此便好了,晚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