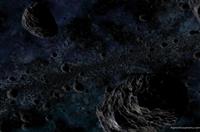
兵 殇
黑龙江省的冬季漫长而寒冷。今年的冬季更是格外寒冷,雪多雾大,气温比往年偏低了许多。进入正月初八就到了雨水节气了,可仍旧是满天飞雪,寒气袭人。坐在温暖如春的室内,看着那盆含苞欲放的杜鹃花,心中却是悲情涌动,泪花莹莹。十七年前的正月初八,天气也是这么冷,雪也是这么大,却上演了一幕不该发生的悲剧,一个青春的生命永远地将这天的台历染红。
步履匆匆,山高水长。18岁正是青春绽放的季节,高永胜却以18岁冲锋的姿态,像一朵迎春的蓓蕾悄然凋谢在正月的飞雪中。时至今日,我仍不相信那个鲜活的生命会消失。高永胜,这位士兵的名字,多年来已在我心里默念了千遍万遍,未曾冷却,未曾远去。
这是发生我身边的一个沉重而令人窒息的悲剧。我不知道从何地方讲起这个悲剧,那种无法用文字描述的痛在我心里搅动多年,灼痛着我的记忆。
高永胜是个憨厚的中原农家子弟,父母在河南省老家务农,上有一个哑巴哥哥和一个身略有残疾的姐姐,为人不善言谈,做事来却是风风火火,干净利落。1996年底入伍时,他当时在新兵二班,我在新兵一班当新兵班长。三个月的新兵生活,我慢慢地熟悉了高永胜,并喜欢上了他。新兵下连时,我找到连长、指导员,把高永胜要到我带的班里。我所带的班是全营的标兵班,要求个个顶呱呱,军事素质出类拔萃。尽管高永胜并不是新兵中表现最优秀的,但他勇于吃苦的顽强拼搏精神着实让我赞赏不已。这也是我挑选高永胜到班里最主要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如有神知,我当初悔不该挑选他到班里,如果不到班里也许就不会发生以后的悲剧了。
在班里,高永胜睡在我对面床上的上铺,是班里的四炮手。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起床,打扫班里的卫生分担区,脏活累活抢着干。凡是接触过高永胜的人,都说他身上那股农家孩子质朴的味道特别浓厚。
1997年9月初,我由士兵提干并被单位保送到军校上学。临别时,班里人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会,我让班里的每个人给我留下一段话。轮到高永胜讲了,他站起身,憋了半天,才红着脸说了一句:“班长,欢迎你早点回来,我们仍跟着你继续干。”说完,就抹开了眼泪。先前,班里那股儿喜庆氛围,这会儿被他一下子捅破,每个人脸上都挂满了泪花。压抑已久的情感,倾刻间喷涌,令我也热泪盈眶。
分开一个月后,部队到大连某靶场执行年度训练考核任务。我在学校听说后,特意请假到部队驻训地看望连队。在靶场营地,我穿着扛红牌的军装与班里人员照了张集体合影,准备冲洗出来给大家留个纪念。谁知,相片冲洗出来,惟独我闭着眼。拿着相片,或许是顾忌自己形象的原因,我没有把相片给班里邮回,而是将相片留存在手中。期
间,我与班里每个人经常书信往来,只字未提相片一事。
春节时,学校放假,原计划与班里人约定回老部队一起过,可因爷爷突然病危,我只得匆匆乘船返回烟台老家。正月初一,我往连队打了电话,与班里每个人聊了半天,在电话里能听出来,离开连队这么久了,班里人都特别想我,希望我能早点回连队工作。高永胜在电话里,没和我聊上几句,就被班里其他人把电话抢去了,我没有太在意这些细节。离开连队这么久了,我能理解班里的每个人对我那份的感情。正月十六日,返回学校后,我第一时间给连队打电话,打了半天没打通。一连好几天,电话就是打不通,让我好生纳闷。我只好给班里写了封信,叮嘱班里的人好好成长进步。信邮走了一周,却石沉大海,这和以往班里给我定期回信,形成了反差。
一个月过去了,班里也没有给我来电话,更没有来信。此时,我隐约地感到自己身边好像发生了什么,只不过是我还蒙在鼓里,大家都有意向我隐瞒真相,刻意回避着我而已。考虑了好久,我开始从外围“突破”,通过别的连队老乡打听自己连队的情况。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连队确实出了大事,连队正在整顿。
原来,这年10月底,有军校学员到基层实习,连队分来了一名地方大学生干部,到我所在的一班当兵锻炼,既补班长经历,又履行排长之责。正月初八,这天天气特别冷,一早上起来,天就飘着雪花。上午九点多钟,我所在的一班7名人员和其他班五、六名人员,在那名地方大学生干部的带领下,到团锅炉房担负运取暖煤保障任务。
锅炉房院内,煤堆得像小山一样,上面落了厚厚的积雪,煤层冻得有几十公分厚,用镐刨下去一刨一个点,虎口震得隐隐发疼,刨起来极为困难,大半天下来,也装不走一车。运送取暖煤,我以前曾干过数次,这活又累又不好干。一般来说,人站在煤堆最上面,用钎子打眼,一点点把冻层抠掉,再往下煤堆就好刨了。当然了,在没抠去冻层的煤堆截面中间处平行掏个儿洞,以这样方式刨煤既省时又省力,却有危险性。煤洞一旦能容进人的半个身子后,就立即需要从煤堆最上面将冻层抠去,一直将煤洞刨掉为止。否则,煤洞一旦掏深掏大,随时就会有塌陷危险。这是干此活最基本的安全常识。
这样简单的安全常识,我不知道是我所在排的人员熟视无睹,心存侥幸,还是连队干部责任心差的原因,没有人事先组织提提安全要求,就匆匆干起活儿来。那天,大家采取掏洞抠煤的方式,一车接着一车运,干得特别起劲。
几个月后,我毕业回到连队,走进锅炉房大院,那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丝毫看不出有悲剧发生的痕迹。班里人指着空荡荡的场地大概方位,向我讲述起那幕场景时,我的心被戳得极为疼痛,手脚发凉,浑身发颤,悲怆之情让我泪流不止。我能想象得出,当时运煤的火热场景,能理解大家在冰天雪地里想早点干完早点休息的心情,正月初八毕竟属于年的味道。五年的连队生活,我太了解班里排里每个人员的真实想法了,太熟悉大家的一举一动了。
半天时间,运了一百多小推车取暖煤。任何一个对数字概念有理性的人,都能想象得出,那煤洞掏得有多深多大。在冰冷的天气里,煤洞像狮子一样张开了血盆大口,等待着吞噬送上嘴的猎物。这一切的危险,大家却是浑然不知,安全的弦谁也没绷紧,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全被速成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被正月的氛围冲花了眼睛。那个现场,我虽然亲身没去过,我却能感受到触目惊心。
运煤现场,大家干了半天,都感到疲惫了,衣服被汗水湿透裹在身上令人有了凉意。两位老兵烟瘾上了,边发牢骚,边带头走出煤洞。排里其余人员见状也纷纷走出煤洞,透透空气,抽起烟来。
“再运上三、四车,就可以收工了。抓紧干完,回连组织打扑克。”那名地方大学生干部在一旁焦急地督促起来。一向以勤快出名的高永胜,在外面歇了一小会儿,便与班里的张道兵,拿起铁锹和镐返回煤洞,一个抠煤,一个装煤。就在其他人员拿起工具,准备返回数米之深的煤洞时,意外发生了,瞬间煤洞坍塌下来,将高永胜和张道兵埋了进去……
在场的人员,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全吓傻了。“快救人!”数秒钟后,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大家才清醒过来,跌跌撞撞地冲向坍塌的煤洞方位,边哭着喊着高永胜、张道兵的名字,边发疯似的用手拼命地扒着煤堆……闻讯而来的连长、指导员、营长、团里领导和连队剩余官兵,也加入了抢救大军。一拨冲上去了,另一拨接着又冲上去了,一拨接着一拨,每名官兵的手都鲜血淋淋,煤堆一点点在手中减少,任凭人们怎么呼唤,里面都没有任何一点儿柔弱的气息传出。
雪花越来越大,官兵越聚越多。每一寸煤层,染红了鲜血,落满了热泪。在官兵们接力般的抢救下,埋在煤层里的张道兵第一个被扒了出来,高永胜拿着镐倒在最里面,最后一个扒了出来。经过紧急救治,张道兵醒了过来,高永胜却永远地离开了。
事后,听班里人讲,高永胜父母来到部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接受任何捐款,背着高永胜的骨灰回老家去了。
人世间,最美的情怀莫过于军旅。一个朝气蓬勃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永远倒在了和平时期的军旅方格坐标系内,以生命为代价,为人们撞响安全警钟。
事情已经过去十七年了。 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既是一种缅怀,更是一种震耳发聩地告诫:“和平时期,每名基层带兵人只要心怀一团火,躬身实践,落实规章制度,就会避免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生命之花就不会凋零在不该凋零的季节里!惟有敬畏生命,才能虎虎生威,肩负打赢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