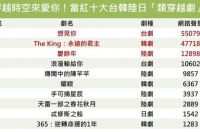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为此,他依照旧例,给皇帝写了《湖州谢上表》,意思大概是说作为人臣,我实在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但是皇恩浩荡,还是继续任用着我。也许是文人意气使然,总想调侃两句,在后面,苏轼夹了几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因为客观环境限制,古人写文章的时候,在遣词造句上总是十分小心谨慎,力求既能表辞达意,又要说清本意。加上文人每天的主业就是摆弄这些文字,本来对文字就比较敏感,何况苏东坡是大文人,写词、作文原本就十分讲究,每个字、每句话有的放矢;那时的读者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因此本能地想要在字里行间搜寻出表面文字背后掩盖着的深刻含义。当时还有一些深刻的社会背景,也使苏轼这两句话引起了某些御史(御史,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检委委员)们的高度关注。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保守派认为变法派无事“生事”;“新进”则是指王安石引荐的个别品质低下的变法派新人。于是,“新进”、“生事”这些原本很稀松平常的字眼,这时就被大家注入了一种深刻的内涵,几乎就成了保守派对变法派攻击的专有名词。这年六月,一个监察御史摘引“新进”、“生事”等词语,以“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提请整个御史台弹劾苏轼。
当然,如果单单凭借《湖州谢上表》里的一两句话,就认为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或许有点牵强附会。可恰在这时,苏东坡的一本《元丰续填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也适时出版了,这就给御史台那些新进急需表现的新人提供了一个绝佳良机。他们经过四个月的钻研,终于找出了苏轼很多首诗作里许多“犯忌讳”的词句,上奏朝廷,称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这个消息是苏轼的好友、驸马王诜悄悄告诉了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轼后又派人给湖州任上的哥哥苏轼传递过去的。
苏轼在湖州得到消息以后慌做一团,整个太守府上下人等乱成一片;家人听说此事后,直接把苏轼与朋友的来往书信、手稿全部烧毁了;据说,苏轼当时还打算自杀,被属下通判劝住。就在这时,皇上派来的钦差急急忙忙赶到了。皇上是以一份普通文书传唤苏轼进京的。文书是普通文书,内容也波澜不惊。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从古至今,许多惊涛骇浪就是以最高统治者的一纸普通文书,或者是以很平和的语言召唤开始的。而现实总是让你猝不及防,结尾也定然会让你刻骨铭心、心有余悸。苏轼尽管算不上一个杰出政治家,但毕竟出身官宦,又在官场浸淫多年,他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果然,苏轼一进京,就立刻被逮捕了。从当年八月到十月,御史台审了苏轼将近三个月,也在苏轼许多词作里找到了大量对他不利的证据,苏轼也写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也承认了他对新政不满。御史台由此认定他诽谤新政事实成立,证据确凿,罪名清楚。如果按照御史台的意见,那苏轼将必死无疑。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也可以想得到:抄家灭门,诗词书稿全部焚毁,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或许只在历史上有过些许痕迹,就像有些游人在某地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更像黑黢黢的夜空上的流星从天际划过坠落一样,但他们的锦绣文章绝对不可能流传下来------特别是苏轼所写的那些妙趣横生的文字,我们后世恐怕再也看不到了!
好在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就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也好在宋神宗皇帝也不是一个昏君,加之苏轼本来就是一个不知深浅、胡言乱语的文人。
不过,这里有一个相关背景必须交代一下。那就是当时北宋朝廷已经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摇摇欲坠,边境告急文书雪片似的摆在神宗皇帝书案上。但朝廷实在没有银子支撑军费,没有能力派兵扫除边患。如果不改革旧的体制,任由这种现状发展下去,北宋朝廷用不了多久,就得吹灯拔蜡。因此,只要多少有点脑子的人就应该知道,改革变法是必须进行的。不变法,就是在等死。这就是当时从上到下所有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公开反对变法,就如同谋逆。既然是谋逆,那就是死罪。因此,假如苏轼罪名成立,不仅苏轼性命难保,即使整个苏氏家族,也将面临灭族之灾。情况十分危急!就在宋神宗皇帝犹豫不决,想着该怎么处理这个不识趣、尽找麻烦的苏轼的时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轼文字中曾经讥讽过的那些人全都给他说好话,劝诫神宗皇帝念他只是一介书生,口不择言,意气用事,放过苏轼。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一直效法尧舜的大度,认为魏武帝曹操猜忌偏执,但是,就连曹操那么喜欢猜忌的人,最后还能容得下骂他的祢衡,陛下难道就不能容忍一介狂妄书生苏轼吗?”已经罢相退居金陵安置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哪有圣世妄杀高才之士的道理呢?”让人觉得更加好笑的是,苏轼口中所贬损的“新进”之人章惇,也为苏轼说尽了好话。章惇为了营救曾经是好友,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但由于政见不同这时已经不怎么来往的苏轼,在朝堂上不惜和非要致苏轼于死地的宰相王硅撕破脸皮,对着神宗皇帝,对着满朝文武大吵了一顿。
在“乌台诗案”里,苏轼贬损的本来就是王安石变法中所用的那些“新进”的“生事”者,既然这些人都认为苏轼罪不至死,神宗皇帝自然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顺水推舟,赦免了苏轼的死罪。但作为一个臣子,对朝廷推行的新法,所用新人,胡言乱语,活罪自然是逃不掉的。至此,吵吵闹闹、沸沸扬扬几个月的“乌台诗案”宣告结束。十二月,苏轼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武装部副部长,但对他有两个要求,一是限制人身自由,二是不能签署公文。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只是个闲职。其实,就和现在所说的“限制居住,不得离开住地,随时听后传唤”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没有开除公职,薪水还有,也承认你还是个政府官员。“乌台诗案”也有几个被牵连的。驸马王诜和苏轼关系极好,得到消息后,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本来是要给苏轼告密的,因无法离开京城,便先秘密通知了苏轼的弟弟苏澈。苏辙转而派人快马加鞭告诉了哥哥苏轼。因此,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且平常宠妾压妻,被消除了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苏辙,都得到了降职处理。
回过头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叫“乌台诗案”呢?其实很简单,乌台,就是指御史台。后世有很多人说,这纯粹就是一桩冤案,文人写一些东西,对时政评说一番,有什么错?其实,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从苏轼的立场上看,御史台的做法的确有点吹毛求疵。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御史台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工作职责,本来就是找“茬儿”的。如果不找“茬儿”,御史台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看看现在的所有职能部门,如果都能像古代御史台的御史们那样,每天勤勤恳恳找“茬儿”,不辞劳苦地挑毛病,何至于社会上有那么多的腐败和丑恶现象发生呢?何况,当时的北宋王朝积贫积弱,急需改革。不改革,那就是死路一条。因此,赞成惩罚苏轼的人也有,而且他们的理由似乎更充分,更有道理。改革是北宋当时的主流。苏轼诋毁、讥讽王安石变法改革,就是与主流唱反调,就是和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作对。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的确应该受到处罚。就好比我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改革是必要的,这是前提。具体到怎么改,如何改,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但如果你假如明知改革属于不得已,但又反对改革,那就是逆历史车轮而动,必然会走一次苏轼老先生曾经走过的老路。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