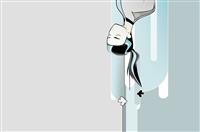
1968年7月21日,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人民喜迎党的“九大”胜利召开的新形势下,毛主席站在社会历史的制高点上,发出了高教改革的重要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指示,如春风,似雨露,滋养和吹开了植根于社会主义土壤中的教育革命的新芽,“七·一二”工人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及经过洗礼改进后的各类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批批来自农村、厂矿、部队的工农兵学员,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继续革命的新战场,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我生长在湖北农村一个“家大口阔”的贫困家庭,母亲早逝,父亲是生产队普通社员,幼时辍学三年;1968年7月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同年年底在社员大会上被选为生产队会计;1970年春进入鄂城县庙岭高中读书,被选为学校团委书记;1972年春高中毕业,被学校和区党委推荐到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深造。
那是一个光华灿烂的早晨,和着热烈奔放的《工农兵学员之歌》的旋律,在老师和七一届老生的欢迎下,我们跨入了华中师范学院大门。数学系党委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系主任和科任老师到寝室看望新学员,系团委举办新老学员篮球赛和文艺联欢晚会,院团委统一组织新学员参观毛主席故居和农讲所旧址,参观武钢、武重和武汉展览馆。而后考试分班。新学员间的考试成绩差别不大,按分数分在三、四两个连队,不久改为七二(一)级和七二(二)级。每连三个排,我編在四连五排,不久改为7205班,全班28名学员。新学员的中学届次构成是30%左右的应届高中毕业生,10%左右直接从华师-附中、汉阳铁中等重点高中选拔的定向培养生,余下为往届高中毕业生和部分六六届﹑六七届初中毕业生。从农业生产第一线入学的同学大都当过中小学民办教师。各届次的学员在一起恰似水乳交融,按当时的说法都是革命同志,从日常生活到听课、讨论、做作业、体育锻炼,从未感到有什么群际之间的差异和隔阂。1974年下半年我祖母去世,同班的方华荣同学还给我家寄去过15元钱;平日里同组女同学李景华、冯金莲帮我上过被子;我为班上编创文艺节目时,刘端林同学帮我抄过稿子;陈德洲和丁昌金同学还相约到我老家去玩。
当年大专院校均实行供给制度,工矿和部队学员带薪学习,其他同学按每人每月13.5元的伙食标准发一大张进餐券,另发5元钱零用。此外还可以凭学生证免费看病,到学院澡堂洗澡。
当年大学的校园生活既紧凑又活跃。每天凌晨六点广播起床号;六点半钟全班集合做广播体操,之后是晨读;八点上课,中午午休;下午两点上课或自学;五点半钟以后课外活动。课外活动是同学们发挥和锻炼各自特长的第二课堂。每当第一课堂的下课铃声一响,整个校园顿时沸腾了起来,大多数同学到操场跑步、踢足球、打篮球,在房前屋后的空地和马路上打排球、羽毛球;有的值班打扫寝室、卫生间、教室、楼道和校园;有的写字、画画、办墙报;有的唱歌跳舞;我和班上另两位同学参加数学系管弦乐队的排练。每星期四上午政治学习,到大礼堂听院长做政治报告,听政治系、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做儒法著作的学习辅导报告,或分组读报和讨论;每星期六下午到本院南湖农场搞农业劳动,顺便观看将军村的女兵操练和排练文艺节目;星期六晚上是同学们最欢乐的时刻,早早吃过晚饭,我们就背着寝室里的靠背椅,三三两两到学院电影场占位子,谈天说地,看电影。星期天休息一天,有的在寝室忙活,有的上图书馆看书、写文章,有的上街闲逛,有的会老乡。逢年过节请省歌舞剧团、省说唱团、武汉歌舞剧院、武汉杂技团、胜利文工团、省军区宣传队到学院大礼堂演出。重大纪念日出专刊,组织院、系文艺会演,组织代表队参加市、区纪念活动。我爱给专刊写稿件,参加过1972年6月武昌区纪念毛主席民兵“三落实”指示发表十周年的肩抢操演比赛和1974年7月武汉市纪念毛主席7•16畅游长江八周年的横渡长江活动。每年7月24日和8月24日放暑假,有的留校攻读,有的回家自习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春节放10天寒假,过完年就返校上课。
当年数学系的课程设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学教改的需要,以服务工农业生产为落脚点,注重培养学员正确的思想方法,注重专业理论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公共课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地理。其中哲学课除讲授马哲原理之外,还针对专业特点专门开设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的讲座;历史课侧重于中国数学史的讲授。专业理论课的主要教材有《中学数学研究》(两册)、《数学分析》(四册)、《高等代数》(两册);应用数学课的主要教材有《常用数理统计》、《画法几何学与机械制图》、《农村测量》、《算法语言初步》、《最优化数学方法》各一册;同时还针对数学与力学、机电及无线电的密切联系,开设了力学、机电、无线电等课程。学习方式除课前预习、课中听讲、课后讨论和练习外,还结合本院工厂、农场﹑实验室的生产和实验进行对照学习,到厂校、社校挂钩的厂矿和社队聆听专场讲座和参加“三结合”攻关试验。这样设置的好处是既能巩固学员所学的理论知识,也能增强其实际操作能力,使其除具备一般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之外,还能劳动、会测算、制图、测量、开拖拉机、装收音机等,更重要的是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临毕业的那一学期,先由系主任和几位与企业技术部门长期合作的老师开过几个应用数学讲座课,而后便奔赴全省各地实习。我们小分队共9人,我是联系人,教高等代数的周教授随队指导。我们先到汉口新华路红星制革厂推广优先法,并用正交式验帮助该厂解决了皮革涂料的配方问题,接着便深入到黄陂县蔡店公社农机厂、红苏大队、蔡店高中和农中实习,向工人、农民和一线教师学习生产经验和教学方法。白天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和教学,同工厂的技术小组和生产队的植保小组成员一起研究技术,与当地老师一起办墙报,晚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排练文艺节目、开联欢晚会。期间还应邀到黄坡县气象站帮助分析气象资料,完成了蔡店公社计划修建的红苏渠工程的测量和设计任务。
我在华师数学系学习成绩一般般,最多算个中等,但自认为教专科数学或工科院校的高等数学、工程数学的功底还是有的。毕业后分配到鄂城师范函授部,负责高师数理函授工作。报到仅一个月,县教育局就通知办一期正交试验培训班,各公社高中数学组长、骨干教师或函授站长40多人参加培训,由我主讲5天的理论课,鄂师另一位数学教师带学员到田间讲半天实践课,在鄂城数学界一炮打响。接着在本县汀祖、旭光两个公社各办了一个高师函授班,各有30多名初、高中数学教师参加学习。我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赶到这两个点上各上一天课,讲数理统计和最优化数学方法,很受学员欢迎。1977年初冬恢复高考时,我又被抽去给应考社会青年复习班讲高中教学,之后还教过1978、1979两届高中毕业班数学,被遴选为全县数学示范课教师。1980年5月参加中国社科院全国统考,除考外语、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之外,还考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高等数学、统计学原理等,被湖北省社科院录取为社会学实习研究员。
划时代的工农兵上管改,犹如“文革”星空上的一颗划过的流星,仅实行了七年就开始坠落……在中国的红色土地上,她的意义和作用如同巴黎公社一样,虽败犹荣、犹著。她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壮举,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她之所以空前绝后,是因为她的存活必须具备两条极为苛刻的社会条件。
一条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列主义理论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吸取包括我国革命根据地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经验在内的一切优秀成果的产物,是迄今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其精髓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基础上的人民当家做主和为人民服务,按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发展社会生产,举办各项社会公益事业。这是其本质性的一面;另一面是因其脱胎于旧中国剥削阶级的社会基础和政权体制,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旧的痕迹,如家族资本经营、单干耕作、乡政村治、家长制作风等。怎样使新的经济基础和政权组织形成更好地适应人民国家的本质性要求,革命的共产党人一直在进行探索,经过一波三折,直到1965年才基本定型。如“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组织体制;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以集体所有制为补充的工矿商贸企业生产经营体制;取消按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取消军衔制,实行官兵平等;反对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平权……但在人民当家作主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与实际行动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如干部决定一切还是人民群众决定一切?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高等教育、文学艺术是为少数精英服务还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还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和组织机制的完善。
三年文革的疾风暴雨对人们的灵魂是一次极大的洗礼,最明显的变化是人民群众提升了主人翁的意识,爱评议国家大事;人民群众不仅能进 “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管理国家事务,还能写大字报监督干部;干部从眼光向上的决策和向下的发号施令变成了“事事看群众脸色”。兹后七年的继续革命,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部进五七干校学习锻炼、城市医护人员下乡巡回医疗、文艺工作者争创歌颂工农兵的文艺节目等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和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直接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组织机构体系,形成了与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生产劳动岗位相适应的科技文化和业务管理的岗位体系。
就农村而言,直接为农民服务的除有县、区、社卫生院医生、中小学公办教师、文化馆(站)的文艺工作者及竹木家具厂、供销社、食品站的人员岗位外,还有公社、大队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代销员、文艺宣传队员岗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有县、区、社农场、林场、养殖场、知青点、建筑公司、运输队、搬运站、农科所、林科所、畜牧兽医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植保站、排灌站、农田水利建设规划设计的专业技术岗位,以及大队、生产队植保员、农机员、电工岗位;直接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有县、区、社农机厂、农机修配站、生资门市部的技术岗位;直接为提升农业生产管理水平服务的有县、区、社各类机构的业务干部岗位及大队生产队长、会计和小队财经队员、会计、仓库保管员、记工员岗位等。
就城市而言,直接为工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有各大中小企业内设的科研院所、设计院室、技术处室、生产处室、供销处室、财务处室及工宣教机构的专业技术岗位;有国家和地方设立的各类科研设计院所、交通流通部门、质检标准化机构的专业技术岗位。直接为市民和城乡人民群众服务的有防疫站、医院、疗养院、商店、粮店、银行、学校、文艺团体、文化场馆、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社、出版社、公益福利机构、公交水电燃料公司等专业技术岗位。直接为维护人民利益服务的有公、检、法、公安、警备部队的专业技术岗位。直接为提升工业生产和城乡管理水平服务的有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党政群团机构的专业领导岗位等。
完备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和工农业生产体系及分布其间的专来技术岗位体系,既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源头活水,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对口分配工作的广阔天地。若打掉这一体系,农村各级各类机构和单位的专业技术岗位便首先不复存在,城市专业技术岗位体系也会随之七零八落,剩下一点杂碎连七大姑八大姨都照顾不过来,加之国内高端企业都被外资垄断,诸多专业技术岗位还轮不到咱中国人。如此这般,大学生、研究生毕业不甘于失业,或不甘于与民工抢活干,就只好送钱去国外“留学”打洋工,或像旧时科举考试那样,再过考公务员的独木桥,甚至像八旗子弟那样到队伍上去吃粮当兵!
有人说造成现在这一“毕业等于失业”的问题是扩招后大学生过多造成的。旧中国的大学何其少,每个省一两所,边远省份还是空白,且普通大学只有几百名乃至百十名在校生,清华大学1947年在校生也不过2000人,除去留学一条路,也是毕业等于失业!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有健全的工农业生产体系结构和城乡社会结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再一条是端正的社会风气。推荐各条战线的优秀青年上大学,必须要风清气正。如果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很坏,选人标准就会被扭曲,选人程序就会被搞乱,有权、有钱、有势的人就会利用职权、金钱、美色拉关系、找门路、做交易,甚至动用警察和黑社会,将自己的子女、亲属、关系户塞进各类院校,工农子弟眼睁睁地被忽悠、被冒名、被警闭、被杀害。精英们会站出来证明弱势群体的子弟“底子差”和爱仇富,不能为突出他们而剥夺官二代、富二代的“人权”,对那些想吃天鹅肉的“无赖”,只能用刀子捅他八刀,这样才能加快发展;贱民不服就用天价维稳,警察﹑保安不够用武警,武警不够用军队,还怕翻天不成?结果是越维越糟,世道人心陷入一片混乱……这是任何政权、任何社会都不敢轻易尝试的。只有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年在工农兵中推荐优秀青年上大学,按现在人的眼光,根本没法搞。一者招生的数量少,二者历届初高中毕业的人数多,如果都为“自我”去挤这座独木桥,无疑会挤坏身子,打破脑売,踩死人命。可“文革”中从1970年开始推荐了七届工农兵学员,除张铁生交过一张白卷之外,没有发生过一起纠纷事件。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奇就奇在当时的风清气正上。
我当年就读的高中毕业班分到两名上大学的指标,华师数学系招1名男生,外语系招1名女生。学校推荐我和班上表现和学习均不错的另一位杨姓男生上数学系;外语系女生初选也照此办理。负责我县二区片招生的武汉钢院谷老师分别找我校的班主任、科任老师和曾校长谈话后,通知我和杨同学返校,谷老师分别找我和杨同学谈话面试,决定将我和一位姓罗的女生列为初选人员报到区委。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大队、公社都出示了被推荐者的家庭和本人的鉴定意见,区教育组考察同意后,让我们到葛店区医院接受体检。
当年体检这一关也把得很严,国家花费大量钱财培养一个病号是不合算的。我区经初选共去4人参加体检,除两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有一名被推荐上湖医的赤脚医生,一名被推荐上华工的下乡知识青年。体检结果前两名通过,后两名未通过。补上并不困难,因有一至两个备选人员,换符合条件的人再去体检。
体检合格报到县招办复审通过后,再报到地区招办与招生院校一道审批,招生院校还有最终的否决权。在当年的被推荐人员中,有被县招办和地区招办审查下来的。我的一位内弟是老八路的后代,有体育专长,还会点武功,高中毕业下乡后劳动表现不错,被推荐上武汉体院。报到县招办审查时,了解到他在下乡期间帮知青朋友打过群架,被退下换了别人。
推荐上大学后也不算完,若群众有反映,也可能落下。我的一位姓谢的高中同学,毕业后在乡教了三年书,因工作勤奋被推荐上了北京工学院。有人向区招办反映说该同学曾有过摸人的“流氓”行为,招办找当事人核实后,将己上学两个月的同学追了回来。
1974年8月底,中央某帅借南京大学一部队学员自曝“开后门”的传闻发火,要在全国各大专院校进行清查。华师3000多人、武大4000多人、华工5000多人被列为武汉地区的清查重点。查来查去,没有查出一个人是开后门上大学的。怎么向某帅交待呢?于是就退而求其次,说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是“回朝”,要全部退回原藉。我当时己在读三年级下学期,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做法极为反感,便挑头写了一张反对“清退”的大学报,在桂子山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和驳斥的大字报贴满了长长一排立在马路边冬青树丛中的墙报栏。我沉着应战,针对有代表性的观点先后写了7篇辩驳文章,争取了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后来虽然没有被清退回去,却把进校时系党委宣布的将理科由上两届三年改为四年的学制弄成三年半就让我们毕业,以后几届再也没招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这对当年正在逐渐走向完善的高教改革是一次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文革”中的高教改革既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器。相对于其他的社会形式而言,她具有不可逆性。即社会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采取推荐制度,也可以像其他社会形式那样采用高考制度;而其他的社会形式可以采用高考制度,如老佛爷的清政府那样腐败无能,还能一本正经地开科取土,但绝对不可以采取推荐制度。她的社会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确立了工农兵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主人翁地位。全国解放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他们在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是当之无愧的主人翁,但在教科文卫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还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工农兵上管改,是打破这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改变上层建筑主体结构的重要举措。只有通过这一改造旧大学的同时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而后通过其占领其他一切上层建筑领域,才能真正确立工农兵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主人翁地位。
当年大专院校各项工作的重心是“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学员既是受教育者,也是教育改革的生力军。上管改不像后来有人想象的那样乱搞一气改别人,而是首先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入手,在政治学习、尊师互爱、星期天义务劳动、整理内务、清扫校园、帮厨帮困中锤炼自己的思想品质,然后才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破除封建关系、提教改意见、改进学校管理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改造客观世界。
工农兵学员这一同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彻底决裂的新生事物,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一些形左实右思潮的非议和干扰。其中在七十年代末的四个标杆性人物的言行上反映最为集中。按照他们的相互画像:一个是从未进过大学校门的“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的人,说什么工农兵大学生在学校只学了一个斗走资派专业;
一个是从未圆过工程师梦的“总设计师”,说什么:“入学不考试,清华大学就叫清华中学好了” ﹔两个哼哈二将,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一个“要吃粮,早指洋”。社会上的一些人为颠覆工农兵在人民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借机生事,指东打西,拧着劲儿妖魔化工农兵学员,以庸俗的市侩常识和“文化不齐”为借口,把工农兵学员糟践得一钱不值,直到人们一提起“工农兵”的字样,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还是时光造化人啊!尽管他们通晓权术,会抓主要矛盾,通过妖魔化红卫兵达到了抹黑文革的目的,通过妖魔化“大锅饭”达到了否定社会主义的目的,通过妖魔化计划经济达到了搞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目的。现正在通过妖魔化毛泽东,以达到否定共产党的目的。试问这些人有没有想过,这是一柄双刃剑呀!老是这样否定来否定去,最终否定的利剑会挥舞到谁的头上?会不会像现在大学里所有的专业真的都弄成了一个专业-------捞钱专业,清华大学真的变成了留美预科中学一样成谶了啊?看看前苏联的舞台坍塌后,戈尔巴乔夫算个神马东西------骗子、小丑、丧家犬,还是靠帝国主义基金活命的乞丐?
2、建立了突出政治、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教学体系。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贯穿教育全过程的政治问题。教育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就必然会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剥削阶级服务。
当年大专院校抓马列主义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在革命大批判中明辨是非,是学员重要的修身课和成长课,是光明正大的做人课,与表面坚持、暗里洗脑的韬晦课恰成鲜明对照。
当年的专业课程设置紧扣为人民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主题,在各重点院校动用一切资源,组建“三结合”教材研究审查组和骨干教师编写组,深掘专业基础,拓展专业内涵,突出专业应用,经日积月累的探索,建成了一套严整的专业课程体系,并通过一线生产检验和教学实践的检验,进行不断完善。这是能真正使学员学有所长、学有所用的专业教育,与为评职称和赚银子你编一本书,我编一本书,东搬西套,拾洋人牙慧的所谓瞄准市场需要的稀松教育恰成鲜明对照。
当年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倡导产、学、研结合,以“产”引导教学,以“学”深化对生产规律的认识,以“研”服务生产和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变象牙塔为三大革命的前沿阵地。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袁隆平在湖南怀化农校教书期间提出杂交水稻的试验课题,便是由该校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帮其搞成的。这样的教学能有效激发学员的学习动力,有利于把学员培养成为有思想、有专业素养的新型劳动者,与尽在教室里东扯西拉、空对空地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方式恰成鲜明对照。
3、培养了一大批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文革”中大专院校共招收了七届工农兵学员,约有230万人;全国各地大中型厂矿创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和各县创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招收的学员也不下200万人。前者毕业后70%回其原来所在的厂矿、市县、部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30%由国家分配到中央和地方教科文卫事业单位和党政群团机关从事相应的专业技术工作。后者毕业后大都回原厂矿、公社、大队从事相应的专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他们历经30多年的风风雨雨,大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我就读的华师数学系7205班的28名同学毕业后,有20名同学一直在高中、师范和职业院校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其间大多数同学担任过数学组长、教务主任和校长;余下8名同学中,1名同学留美归国成为数学家,2名任大学数学系正副教授,1名任大学自然辩证法教授,1名任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1名任大学人事处长,1名任县长,1名任省直机关副厅级干部。
工农兵学员因其“出身不好”,长期处于异类和边缘化的位置。比较典型的是在北大和华师为百周年校庆所编写的校史中,均把“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的历史做空白处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却不妨碍他们仍将这空白的七年算作他们“办校”的年头。对此,我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愤慨地说:这些自诩为以社会良知为社会代言的名校,连自身的历史都不能善待,还能指望他们去善待人民共和国的国史和中共党史?但工农兵学员群体毕竟是从工农兵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加之其所受教育的底蕴,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多,自轻自贱的少;普通劳动者多,精神贵族少;任劳任怨的多,投机取巧的少;靠专业吃饭的多,靠巧取豪夺暴富的少。
1980年5月中国社会科院在全国院统一招考研究人员,应考者包括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几届大中专毕业生,有的是研究生和留学生,还有大学讲师,连西藏活佛也参加了考试。考试结果全国录取了360名。在湖北考区录取了25名,其间大专院校毕业的工农兵学员7名,中专毕业的工农兵学员1名。这8名工农兵学员除1名被中国社科院录取赴日留学,1名中专工农兵学员后来留美归国之外,其余6名均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直面惨淡的人生,以惊人毅力攀登理论文化高峰,俱取得了正高职和担任过处级以上的业务领导职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靠非毛反社反共和呵洋屁起家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春光年年驻人间。工农兵学员队伍历经30多年风雨的洗礼,也涌现出了一大批顶尖人才。如中科院院士、卫生部长陈竺、物理奇才徐依协、数学家陈明祥、自然辩证法专家卢翼翔,经贸教授陈人康、特色经济学家樊纲、播音员敬一丹、军事评论家张召忠、画家严家宽、作家梁晓声、贾平凹,宛如天上的星星,数不胜数;还有部分学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习近平、李源潮、王岐山、张德江、王沪宁等,地方各级领导就更多了。中专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出了广州市社科联主席李明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色经济学家钟朋荣等。之外也有极少数负面人物,如中科院院士张启发、旅美华人女作家张二鸿、气功大师严新。他们也是从工农兵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却解脱不了特色年代名缰利锁的羁绊,以致由南橘变成了北枳。
“文革”中的高教改革是继清末科举制度改革、新中国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改革之后的第三次伟大的改革运动。她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和世界的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如英美的“职业教育”、印度的“赤脚学院”,都有我国“文革”高教改革的影子;改开以后曾在一些重点高中实行过由学校推荐优秀毕业生上大学的做法,也有“文革”高教改革的影子。
“文革”中的高教改革的大方向即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她探索积累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她的操作失误和遭受干扰以后妥协放任的教训也必须深深记取。就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而言,总结教训比宣扬成绩更为重要。如多少年来只知对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起哄,不细致分析其来龙去脉就是一例。就张铁生自身的文化条件和工作能力而言,应该不差,否则不会在中学时学习成绩名列前芧和下乡时在生产队当队长;当时并没有让他上理工科类的普通高校,而是上相当于共大性质的社来社去的农学院。像张铁生这样的条件不经过考试上这类的大学并没有什么不妥。
当年的工人大学和共大因其是在工厂和公社的“熟人社会”中招生,相互之间了解较深,谁行谁不行人人心中有数;招生过程是先由车间、大队摸底提名,工厂和公社一一排队挑选;若放着好的不推荐却让劣的上,谁受得了大字报的一顿暴晒?个人也有自知之明,就是硬挤进去了学不了,不遭人笑话?往后怎么在单位混下去?况且去学的又都是大家熟悉的老本行,内行看门道,只要按标准对号推荐就行,用不着考试就能择优录取,还能避免“一考定终身”的缺憾。现在的各类职业院校将来非走这条路不可,要改进的只能是操作办法。但在“文革”中发展到后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取消各类普通高校的必要考试和测试,这是值得商榷的。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当年若能进行分类处理,在普通高校一些理论性较强的基础专业和前沿专业的招生中坚持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做法,除工人大学和共大可以将招生指标直接分解到工厂、公社和知青点之外,普通高校的这些专业则以该校的招生范围为界,先推荐和体检,将推荐面放宽到1:10左右,而后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坚持有特别需要的院系专业直招应届高中生入学的做法;坚持文科和农林、工技等专业三年学制及理科、外语和工、医的部分专业四年学制的做法……改开以后唯一一个“出彩”的恢复高考,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震撼力。
工农兵上管改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型就遭夭折,加之在其一波三折的探索过程中不便放手招生,难以做到野无遗贤。当年的贤者也应该对此有最大的体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