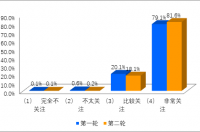内地大约一年前为“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根据宪法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下称《老年权益》),对老年人(六十周岁以上)的权利和赡养人(老年人的子女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应尽的义务,有巨细无遗可算非常全面的规定,举其荦荦大者有“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生活”;还强调“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而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真是具体而微,媲美《宪法》对人民享有种种可说应有尽有权利的规定。此外,当局定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此节似为我国独有)。由于《老年权益》第三条至第十条明文规定各级政府要把“老龄事业”(这还是第一次听到的“行业”)列入财政预算及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而“国家和社会”会采取措施,以“健全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多项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安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欢乐”。内地真是老年人的天堂,政府如此周到,且立法“强迫”子女等后辈行“孝道”,老年人真太幸福了。由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一项长期战略任务”,预料内地的“老年节”一定会搞得热热闹闹、耆英开颜。《老年权益》不算新闻,近日西方传媒所以“热炒”,皆因内地出现一项代子女“行孝”的行业(下详)而引起广泛注意。
可是,亲情的有无、子女是否孝顺,不仅很难通过立法去解决,其有无亦不易用传统智慧去衡量,人人诉求不同,因此不可能有“通论”。事实上,什么是“经常”,怎样做才算合格的“看望”和“问候”,并无定义亦乏具体的形容,以至诸如什么才算是有关人等以至法官大人认同的“关心”,并无(简直不可能)明确规定,因此执行起来肯定极度困难……一旦后辈“犯案”,便可能要凭法官大人主观定夺;而这类可“酌情”处理的事,在贪风弥漫的国情下,便很难有令多数人信服的判断。总之一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有几个“清官”?),放诸中外古今而皆准,如今政府要以法律行之,困阻重重纰漏百出是免不了的。
数十年来,一穷二白时期只知歌颂领袖和党,亲爹亲娘算老几!经济勃兴后则一切唯物质是尚;加上在一个基本上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独孩”自幼被宠坏,孝这种必须后天培植的行为,在内地似不易寻觅。根据“孔家店”儒家的说法,父母护育婴孩、稍长抚养供书,尽显双亲的“慈”(慈是先天形成与生俱来的),而待其成年仔肩已尽父母转入晚境,子女若不以“教道相敦勗,恐兴风木之叹……”(见钱穆《双溪独语》第三十三篇)。中国千百年来“育幼养老……发扬孝心慈心而达和美圆满之境”,这种自然和谐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社会,在极端政治化和绝对金钱至上的大环境下,早已成为陈迹。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世界少有要用法律规范道德行为,强迫子女应尽“孝”以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德政”。
然而,孝道属于道德层次的行为,是无法凭法律来规范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才算是“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恐怕很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经常”、“看望”、“问候”都不易有标准(7月中旬内地有一宗判例把“经常”定为两个月,即儿子两个月要“看望”、“问候”双亲一次),在这种情形下,《老年权益》必会引起没完没了的诉讼,虽然予经手断案的执法人员及法官上下其手的机会,却肯定会使更多的老人家伤心。
《老年权益》还衍生了不少“法律漏洞”,比方说,如果子女因远在外地工作或住于本地而太忙无法抽身做出符合《老年权益》的诸种规定,可否请人代劳?在笔者的想象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由“非家庭成员”这样做,只是表面虚应工夫(“做秀”),并无真正关怀老人的精神内涵,与《老年权益》中的“道德规范”背驰。不过,海峡两岸人民的看法肯定有异于笔者,若不如此,内地近月便不会出现一种收费代子女尽“孝道”的行业,据贴在淘宝的广告:“十分钟八元、一小时二十元”,亦有“一小时一百元”的“代看老人、给父母打电话、带看空巢老人”所谓“常回家看看”的新兴行业。这种在西方社会看来非常诡异的服务,在中土(内地和台湾)却有滋长的土壤,因为传统中国丧礼可以雇人“哭丧”,代孝子贤孙“哭丧”既被传统社会认同,代子女“关怀”老人家有何不可?内地有“代子女行孝道”的职业,便是答案。
我们看看没有“孝”的传统和“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
资本主义看穿人性贪婪自利的一面,因此颇能对症下药。资本主义世界俱以物质诱因导使子女及其他“负有赡养义务的人”遵行孝道。最常见的诱因——诱使子女及“有关人士”供养老人家——是税务宽免,即供养父母的金额可扣税。显而易见,这样的“税法”,先假定有财力的子女不愿供养父母,是对子女的侮辱,但此税例之立,是对老人家物质生活(免于饥寒交迫)的保障。和内地不同,“不孝”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道德过失,并不违法,因此故意或疏忽照顾父母,并不罕见。乏人供养的老年人,因而成为社会的负担,这对大多数(纳税)人不公平,为弥补此种漏洞,遂有“扣税”的发明。换句话说,“扣税”是“必要之恶”,因此少人诟病。
“扣税”对“供养”双亲的子女有一点鼓励作用,但如果父母有积蓄而子女有自己的世界因此对老人家不闻不问,令他们寂寞难耐甚至不快乐因而促寿,除了可能徒具虚名的《老年权益》,又有什么方法可解决?答案是没办法。在事实上大都穷透根(负有数代人无法还清的巨债)的所谓“富裕社会”,这种窘迫情境只能由政府来承担,这是为什么在大多数国家都有种种优惠老人的现金救济、房屋津贴及医疗补助(香港地区当然不例外,最近推出的是“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对老人家的照顾可说无微不至),那是构成“福利社会”的重要一环。政府插手“家务”,子女于有意无意间顺水推舟把照顾双亲的责任推给政府,家庭关系更疏离,《老年权益》试图拉拢子女与双亲的关系,却因漏洞太多而难竟全功!
笔者早在二十多年前的1992年,便写过题为《享受人生黄昏, 生收钱死交楼》的短评,评说老人家应把拥有(已断供)的住宅“卖”给按揭公司,由金融机构逐月支付定额生活费,直至两老都入土为安,这是在保障老人晚年物质生活无忧前提下,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传统智慧”彻底落实的良方。这种方法,便是经济学家称为“逆势按揭”(reverse mortgage)的“财技”。笔者当年撰此短论,是以为此法符合人类自利天性,希望后代自力更生,不要期待可以获得先辈“遗赠”而嬉于学、荒于业。然而,这种做法毕竟违背“水向下流”的天性,这些年来,“逆势按揭”似乎流行不起来。事实显示,留下“遗产”给社会(以至庵堂、教会)或把财富“遗赠”后代,仍是老人处理一生“积蓄”的主流做法!
把财富“遗赠”子孙,撇开遗产税的困扰(内地和香港人当然没此问题),老人家要考虑的自然是怎样做才能使受授双方均感满意?这正是经济学家下过不少工夫惟迄今仍在探索的命题。2004年10月20日,笔者翻到一篇写于此前整整二十年的论文,撰成《家财死后才分赠,慈孝永远在人间》一文,因谈论《老年权益》,找出一看,仍有“可观”处,因而引述改写如后。
经济学上有所谓“遗赠策略性动机或理论”(Strategic Bequest Motive or Theory),指出财富持有者在生前把财产捐出或分赠后代,不是最聪明的做法,因为有不少例子显示,有“遗产”此一诱因,可以换取后辈特别是已自立子女的关爱;生前便把财产分赠后代,在“百事金钱挂帅”令“百行孝为先”的传统已少人闻问的现代社会等于连此诱因亦断送掉!有积蓄(不论多寡)的老人在有生之年,“笑言”要把某儿孙从“遗赠”名单中剔除,虽然那可能只是开玩笑,但在一般情况下,已足使后辈对父母毕恭毕敬甚至照足父母的话处世;如果这种“策略”正确,意味着可用作“遗赠”的财富愈多所能获得后辈反馈之爱愈深愈浓。
上面这种说法看起来太市侩太不人性,亦把“孝道”视为可用金钱交换而得的东西,肯定不为“道德大多数”或假道学之辈接受。然而,经济学家以实证方法证实此法对老年人最有利。三位已成大名的经济学家(包括曾任哈佛校长、美国财长的萨默斯[继伯南克出掌美联储主席的“黑马”]、被政府控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当苏联经改顾问时中饱的哈佛大学名教授Andrei Shleifer等)于1984年3月所写的《作为支付手段的遗赠》(Bequests as means of Payment),得出如欲子孙经常来访或来电,生前把财富送尽是最愚蠢做法的结论。
这篇论文以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King Lear)第一幕第一场的一段话为“开场白”,笔者无处觅迷失于书堆中公认权威的梁实秋或朱生豪的中译,请内子将之迻译如下:“告诉我,女儿们 / 在我放弃全部权力、领土和责任前 / 你们当中谁可说是最爱朕的人?/ 送出我的最大恩惠 / 给天性充满厚道的人。”莎翁此剧写于距今四百多年前的1608年,当时当然只有民间智慧而未有社会科学遑论经济学理论,且莎翁写的只是人性,与“经济行为”很难扯上关系。可是,在经济学家的推理中,如果李尔王生前不把所有分给对他阿谀奉承肉麻话说尽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他便不致贫困哀伤至疯致死!李尔王的小女儿对他真挚的爱始终如一,展示了人性善良的一面,惟此与本文无关,不赘。
《作为支付手段的遗赠》还以实证数据展示,教育程度愈高收入愈丰的子女,“探访”双亲的次数愈少。英国学者循着这种“指导思想”,凭“英国家庭分类调查”的数据,得出有大学学位的子女打电话问候父母起居健康情况的次数,比没有学位者少百分之二十,“探访”双亲的次数更少达百分之五十。为什么会这样反常(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资大但“回报”小),经济学家的解释有二。其一是教育与收入成正比,大学毕业的子女收入较高、社会活动较频仍,等于时间较值钱(或可说在父母身上所花时间的机会成本较高),对父母的嘘寒问暖遂较疏。其二为独立的子女探望或以不同形式关怀父母的程度,与父母是否有“余资”留给后代有关,如果父母在生之年把财产分光花完,父母所获待遇较差甚至极差(亦可说是“李尔王征候”);反之,即使他们又老又病,仍然是受尊重、关爱的老人家。有经济学家打趣说,父母即使没什么钱,亦应经常参加慈善活动,因为这类“有开支无收入”的“社会工作”,发出了“我们尚有一些积蓄”的讯息,结果换来较多关怀,不难预卜。
多年前笔者据已故薛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i)的《无趣的经济》(Joyless Economy,牛津,1976)写过系列评论,这里所写,同样“无趣”;然而,这是不想晚境孤独凄凉的老人家不得不细思的问题。
撇开儒学宣扬的孝道,从现实角度考虑,老年人拥有一点虚虚实实后人“有兴趣”的财富,是“安享晚景”的保障,是过安乐欢愉退休生活的最有效办法。不过,中国人认为最幸福的家庭生活为N代同堂、子孙绕膝,这显然是不少同胞梦寐以求的事。然而,经济学家有异议,他们认为:“祖父与十八岁以下的子孙同住促寿!”众所周知,经济学家不作讹语,所说都是实证求真的结果(是否为“真理”是另一回事),上面这种结论,见于两名经济学教授(分别在普林斯顿及Stony Brook大学任教)根据盖普洛在全球一百六十一国对一百一十多万人调查所得统计写成的《爷爷与“反斗星”——和儿童共同生活对老人康乐的影响》(A. Deaton / A. Stone :“Grandpa and the Snapper :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Who Live with Children”,NBER Working Paper No. 19100,2013年6月)。在一般人想象中,“稚子迎门……携幼入室”,是人间之至乐;受儒学熏陶,古人大都谨守“长幼有序”、“有上有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的教诲;父母慈而子孙孝,这样的家庭组合,多代同堂亦能和睦相处。但现代尤其是向来崇尚、追求独立人格、生活自主的西方社会,本来便很薄弱的伦常关系,在工业社会特别是政府有完善的“老有所养”政策的国度,早已荡然。在这种情形下,“祖孙同堂”,前者便会因为看不惯而又教不听“十八岁以下”的少年而“比较不快乐”,令神经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这是因为“隔一代”的代沟不易融合,无论价值判断和生活习尚的“鸿沟”太阔,同住同食,龃龉不绝,经常吵闹,自免不了,而吃亏的当然是年老体弱感情容易受伤的老人家!值得注意的是,父母与子女同住,由于只是“隔代”,较易沟通,父母有苦有甜(also enhanced positive emotions),有失有得,不若祖父与孙辈同住对前者的健康和精神弊多利少!应该一提的是,这篇论文仅以祖父入题,不及祖母,料古今中外的祖母都比祖父非理性、更仁慈,盲目迁就溺爱孙辈之故。
用经济学家的提议处理“老年人乏人照顾”问题,虽无人情味却肯定比立法规范后辈行“孝道”更有效,令“重晚晴”的老人家因此有较多的“眼前利益”。当然,此事的关键在老人是否有“家产”,除了那些一穷二白必须靠政府救济才能活下去者,不然,退休前的父母要设法多储点钱,储蓄不多的老人家则应耍点小计谋——比如经常做些慈善性工作——借以引起早失传统孝道的后辈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