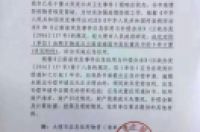在实力上升阶段,美国在全球推行其价值观所负担的成本往往被更为可观的现实收益所掩盖,其国内在对外战略和政策选择上往往能达成较为高度的价值共识。但是,在其实力步入下降通道的过程中,美国推行所谓“仁慈的霸权主义”①以及在全球维护和扩张其价值观念的成本变得越来越沉重,需要不断消耗其国力作为代价。当美国对外实现价值诉求所需要承担的成本高于其现实收益时,两者之间的冲突开始凸显,国内对于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的认识分歧形成相互掣肘之势。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相对实力下降阶段,价值扩张和巩固国际“领导者”合法性的诉求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负担?这种重负在美国国内价值认同和社会层面导致了什么结果?价值认同危机和社会分化的状态与趋势对于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产生何种影响?对此,美国精英阶层的应对之策是什么,以及这种应对原则对于美国对华战略前景的判断具有怎样的启示?
一、美国国家实力难以承载的价值诉求负担
(一)巩固国际“领导者”合法性和进行全球价值扩张的重负
美国在全球扩张其“普世”价值需要在国际社会谋求合法性。在某种意义上,这越来越成为其对外行为的枷锁。与崇尚国家实力和利益至上原则的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的对外行为往往还需在道德至高点的基础上推行。这一道德合法性曾经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得以确立。二战后,在由美苏引导的、以意识形态斗争为核心的“非敌即友”的世界中,美国曾凭借“自由世界领袖”这面旗帜,在道义上获得了领导并塑造所谓民主国家及国际社会的特权。为确保“自由世界”的安全,美国被赋予了在全球建立规模宏大的军事网络,以全面控制或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力。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解体,由于无法找到一个能够支撑其庞大军事机器的明确敌人或潜在的重大威胁,美国以民主为由在全球的干预行为失去了道德合法性基础。这种道义基础的丧失,不但使美国内部界定其一致的“国家利益”变得异常困难,而且加剧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内部的分歧,在降低效率的同时,提高了美国的“领导”成本。
尽管作为西方世界价值领袖身份一呼百应的荣光岁月,对美国而言已经不无遗憾地伴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坍塌成为历史,但其精英阶层不仅满足于就此扮演世界“主宰者”的角色。他们仍坚持认为,美国作为具有统治实力的超级大国,有担当世界“领导者”的职责。在他们看来,一方面,美国需要继续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与此同时,这种对外干涉行为又必须坚持在国际社会道德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按照他们的逻辑,民主制度的吸引力正是美国获得全球号召力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力的极其重要的来源。因此,在领导民主国家共同体之前,美国必须在共同体中获得被拥戴者的资格,占据提倡实现“美好的”世界秩序及普遍人权社会的道德优势。②因此,美国在加强对外霸权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护自身行为在全球的合法性。③在美国,即便最青睐于现实主义理念的政治家同样不敢公然藐视这种道德合法性的权威。对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外交传统颇有微词的基辛格也强调,处于传统世界格局变化、过渡时期的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继续把自己的权力转变成具有道德共识的合法性基础,让别国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④赞同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前国务卿赖斯也声称,“美国为促进民主价值观和人道主义目标在全球付出高额成本,从长期看是值得而且必要的”,甚至是应当享有“最高优先权”的。⑤
尽管政治家们不时为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实现描画出一幅又一幅美好的远景,但就现实层面而言,为维护其世界“精神领袖”地位,美国在财政上消耗了过多的国力资源。这种负担对美国来说,在“敌友分明”的冷战背景下或许是必要的,在其经济实力强大到足以支配世界以及漠视竞争对手时或许是有效的,但在其相对实力无可挽回的下降阶段却是难当重负。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成功传播其文化观念、运用其软实力,其背后的实现途径有赖于支配世界的巨额军事开支。与旧式“殖民帝国”相比,美国通过构造“基地帝国”网络实现其军事统治和文化传播。这一“基地帝国”由建立在全球各大陆上的永久性海军基地、军用机场、陆军驻地、情报侦听站和战略飞地等军事要件,以及巡弋于世界各大洋上共10余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组成。美国通过在其他国家领土内占有或租借专属军事区的方式,创建了近千个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50万以上的士兵、间谍、技师、教师及其民用承包商。由这些基地和人员组成的庞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利益网络,以上千种不同的方式与美国的公司、大学和社区互动,并在五角大楼这一中心链的指挥和监控下彼此相连,最后共同纳入美国的军工综合体中。在查默斯·约翰逊看来,这一“基地帝国”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通过显示美国“消费主义的斯巴达”模式,以影响当地文化,通过炫耀其军团的电影院、超市、高尔夫球场、游泳池、空调宿舍等,来宣扬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就和优越性,从而改变这些地区的传统观念。他同时指出,维持这一由军事带动的传播价值的网络需要耗费巨额的财政开支,这极大地增加了帝国的经济负担。⑥
为了促使美国式自由民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美国政府还必须对那些有扶植潜力的外国政府及机构“慷慨解囊”。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将对外援助作为促进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有效工具。在“马歇尔计划”推行期间,为了尽快在欧洲、日本实现民主国家的重建,美国曾将其预算的15%用于对外援助。尽管今时今日美国政府的该项支出比例与当年相比早已捉襟见肘,但就政府发展援助的赠款规模而言,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援捐赠国。⑦美国对外援助款项中的相当份额被用来支持世界各地被美国所认可的民主政权和民主机构。这些规模及声势宏大的援助行动遍布于中亚、非洲、中东、拉美和东南亚地区。自2001年以来,美国官方发展援助(ODA)的预算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扩大了三倍左右。⑧巨额援助中的大部分被用来促进由美国所定义的全球“民主化”的发展。
(二)全球问题引发的道德危机和治理成本上升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是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谋求道德合法性成本提升的另一重要因素。全球化固然蕴藏丰富的经济和文化收益,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各国政府无法掌控的力量,由此引发的层出不穷的全球问题放大并激化了各种矛盾。如何解决那些影响人类发展甚至生存的重大矛盾,成为世界考验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对美国的需求定位已经从昔日的“自由世界领袖”转变为当今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如今全球问题的主要及热点议题主要包括:恐怖主义对人类安全的威胁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材料的失控问题、与地区冲突相关的安全问题、由金融体系不稳定造成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全球贸易失衡问题、气候变化及环境恶化问题、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蔓延问题、有组织的国际犯罪问题、难民泛滥问题、人权问题、信息技术问题,等等。
全球问题首先并紧迫地体现在安全领域。如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彼此对立的国家之间开始具备相互摧毁的核实力,世界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核扩散威胁。全球安全的另一焦点问题是恐怖主义威胁问题。一方面,以传统军事安全防护手段对付并打击恐怖主义,其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武装训练有素且财力雄厚的恐怖主义组织横行于市,使得采用能造成大规模破坏效果的手段对一国实施打击,已不再是有组织的国家之专利。这些新变化趋势使得传统军事投入已经不足以有效防范风险。全球气候异常及减排问题也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它可能演变成为国家间潜在的冲突源。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和控制直接影响到一国的能源消费数量、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变动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并通过负担温室气体削减成本而影响到该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因此,各国在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的分歧很大。
不断涌现的全球问题,使各国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在人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期望变得更为积极和迫切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如果力求在价值层面维持其领袖的合法性地位,就必须证明自己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领导这个由交互式通讯所造就的不同宗教、文化、政治经验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存的世界。而证明这一点,美国需要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承担更高昂的成本。如今的美国深陷于如下全球性“道义”责任的泥淖中:人道主义干预、通过全球化扩展美国式的“市场民主”、公开对拉美贩毒集团和本地政治改革运动开战、隔离并打击“无赖国家”、领导永无休止且愈演愈烈的“反恐战争”,以及对任何地区威胁以及拥有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任何潜在不友好力量进行干涉,等等。以上领域均如同无底洞一般吸纳着美帝国的财力和精力,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难现成效。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在自身相对实力下滑的过程中,美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随之下降。在这些亟待解决的全球性困境面前,美国显得疲于奔命、力不从心。这种状况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精神上领导全球事务的合法性。
二、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认同危机和社会裂痕
(一)精英阶层与公众之间的认同分歧和矛盾
当现实利益难以平衡担当世界精神领导者所必须支付的成本,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定位在国内会引发激烈的争论。这种分化的压力干扰着美国对外行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从而进一步增加其实施的成本。尽管美国对外行为体现的多是精英阶层的利益和诉求,但是一旦触及切身敏感的利益,社会公众及其舆论对于决策的干扰力也不容小觑。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指出,社会凝聚力是美国有效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必要前提。因为民主政体的形式决定美国外交政策出台前,不仅需要从上到下进行动员,而且要就“选民对国家利益共同的、基本的甚至几乎是本能的理念形成一致意见”。⑨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民众往往不能正确领会国际事务的错综与复杂,并通常带有较强的情绪色彩。美国公众对于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价值取向和与切身相关的利益具有双重敏感性。当价值诉求与其现实利益相互匹配时,他们对于政府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并不介意。当两大目标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即为达到价值目标所需要支付的现实成本越来越大时,社会舆论的反应会变得十分强烈:一方面,就手段合法性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分歧越来越明显和尖锐;另一方面,在统治精英看来,普通民众看待国际事务时只顾及眼前利益的“眼界狭小病”在社会中蔓延。在这种时刻,决策者制定对外政策稍有不慎,公众和社会舆论就会表现得义愤填膺。而作为“第四权力中心”的新闻媒介也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推波助澜,把民众情绪推向高涨,以求制造社会兴奋点。尼克松在谈到越南战争引发的社会舆论骚动时,曾按捺不住抱怨道:“都是该死的新闻界干的好事。他们死咬着越战不放,每年都有新花样。……这样一来,你再看看民意测验,你还能指望它会符合事实?”⑩在声势强大的舆论和形式上的民主决策程序双重压力下,美国政治决策者通常不得不关注甚至迁就国内情绪的变化,选择依据国内社会因素来制定那些将影响外部世界的对外政策。11政治决策者对选民和社会压力的积极迎合,反过来继续助长了国内狭隘民族主义的发展。12
当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相互掣肘以致引发深度社会反响时,美国决策者往往会陷入一个“既无法驾驭,又不能忽视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裂缝中”。13这一裂痕的渊源由来已久,在美国取得世界领导者地位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冷战期间,杜鲁门的顾问在谈到国会和美国民众“不仅厌恶把自己与世界事务搅缠在一起”,而且“渴望遣散军队和增加消费”的倾向时,称其为“一场国际关系精英分子的认知和大众压力之间的冲突”,并视之为“美国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主要障碍”。14当年,尼克松担心社会公共舆论干扰其建立中美新关系的战略目标,事前“把盖子捂得死死的”,几乎完全避开国会和新闻界。因为他深知,美国是“一个爱嚷嚷的国家,两个人就会有三种政见”,不希望因此功败垂成。15如今,对自身实力下降的普遍感知,使美国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仰和认同危机。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16由于国家实力不足以弥补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目标之间的裂痕,美国社会分歧不断扩大,不满的舆论呼声越来越高。
(二)精英阶层内部的分化
除了社会舆论与精英决策层之间的认同危机,美国精英集团内部在价值与现实目标相互冲突的情景下亦出现分化。在社会和自身信仰的双重压力下,对外如何处理价值目标越来越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精神负担,对外政策的摇摆性也随之增强。
基辛格曾对美国外交决策的特点作出如下结论:“任何一种真正体现美国精神的国家利益概念都必须源自美国的民主传统,都必须对世界范围内民主兴衰表示关切。”17美国学者在谈到对外决策的合法性问题时也指出,美国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18而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流露出漠视这些价值观念的端倪时,便会受到来自政府部门、国会、反对党、新闻界的批评。19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其新作《我们濒危的价值观》中所表达的立场和情绪,或许能够从侧面让我们体会到美国决策精英们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无法逃避的价值负担。卡特不但坚定地认为,他的国家不能成为“让别国观察、效仿”的“道德的国际表率”,是“没有道理可言的”。而且,他对于美国背离自己“曾矢志不移的承诺”之局面,表达了不满和忧虑。他强烈谴责政府“背叛人权承诺,背弃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权卫士领导角色”的行为,并表示“高层官员极力为这种背道而驰的行为做法律辩护”,是一出“令人尴尬的悲剧”。特别是提到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那些可怕的虐囚照片”时,卡特更明确地称其“玷污了国家的声誉”。20这些有悖于价值目标的对外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国文化精英阶层思想的裂变。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不久,新保守主义著名人物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新作中承认自己是新保守主义的“叛徒”,并公然表示与新保守主义阵营决裂。21福山此举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诉求与其现实外交行为之间的裂痕和矛盾、对美国思想和知识精英的冲击。
(三)利益集团政治与党派纷争
精英及社会阶层分化对美国对外战略的掣肘,通常以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集团政治形式体现。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民主的危机》中指出,政府不敢漠视甚至在必要时极力迎合利益集团要求的动力深深植根于美国民主社会的“故作姿态和结构特征中”。民主政治在形式上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集中社会形形色色的利益以形成政策的交汇点。在美国社会,这一功能的实现要经过“讨价还价,政府和政党内部的妥协,政党间的妥协以及竞选竞争等一系列复杂过程”。斯蒂芬·克拉斯(Stephen D. Krasner)也同样看到,美国政治制度中包含有“外部强大而内部虚弱的悖论”,即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其决策者经常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和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之制约。22美国对外行为的决策同样受到党派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和约束。在相对国力衰落的过程中,美国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的平衡被打破。不同利益集团就美国对外行为中两种存在相互冲突潜质的目标的理解及排序不同,其间产生的分化和冲突对国家决策的干扰性越来越强。
近年来美国集团政治的分化首先体现在其党派分歧的日趋尖锐、激烈化上。尽管美国党派斗争的历史由来已久,但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实力能够支撑价值与现实目标的共融,因此各党派在原则性问题上相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如今,这种共识的达成越来越困难。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感觉到,目前政党在政治上的分化,比他们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克林顿和小布什在其反对党中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明显地反映出政党分歧的加深:小布什在民主党中的个人声望,比克林顿面临弹劾时在共和党中的个人声望还要低。23其中,各党派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分歧尤为明显。
除了政党的分化之外,各种利益集团也是牵制美国对外行为的关键政治力量。商业界、行业协会、劳工集团、种族集团、宗教团体等等,都期望并努力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以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失衡,导致了各集团利益的进一步分散和共同目标的缺失。如今,美国的对外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受制于社会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抵触、难以协调的需求。国会变成了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相互争夺资源的竞技场。在那些重要的利益集团逐步升级的诉求,以及为保证目的而使用的花样繁多的政治手腕面前,美国决策者缺乏能力和意愿拒绝之。由于这些集团的需求与国家利益的方向未必趋同,因此美国对外政策的倾向和资源分配难以避免在它们的强力干扰下偏离国家利益本身。布热津斯基曾不无忧虑地指出,“在美国霸权和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集团对美国整体国家利益能够理解得既独特又深刻”,而国会作为一个成分复杂的集体机构,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很难对美国与全球范围相关的政策给予必要的战略性指导”。24具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分散了美国的对外战略目标,阻碍了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迫使国家在对外决策方面承担着“过重的负荷”。25这种趋势在相对国力下降的过程中,越来越困扰着美国的外交决策层。
美国外交史学家塞西尔·卡拉布(Cecil V. Crabb)如此评价美国人对国家对外决策的期望:他们期待着“任何新方针都将符合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她的精神气质及其传统”,符合美国“对自由、公正、正义、放任主义、民主及其它所珍视的理念的信仰”。26然而,自上个世纪以来,同时支撑威尔逊式理想主义与对外功利目标的强大的国家实力在一个多边化的世界中难以维系。于是,在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的两难抉择中,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在《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中描绘的“焦躁不安、个人至上、族群分裂、党派松散”的社会图景在美国得以重现。27一个惯于扮演“世界事务中的弥赛亚”角色的商人国度,其精英阶层如何在确保实现国家及内部集团之现实利益的同时,竭尽所能使其对外战略的解释与价值观相吻合,将是美国面临的巨大难题。
三、相对实力下降与分化状态下美国的对外战略困境和应对之策
在相对实力所处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预期面前,美国对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目标之间的权衡存在不同的心态。在其国家实力上升阶段,二者之间即便出现矛盾,这种矛盾通常也易于协调。一方面,强大的国家实力可以有效支撑追求价值目标所需要的投入,弥补两大目标之间的裂痕。另一方面,对国力蒸蒸日上的预期使美国人对维护价值目标所支付的成本具有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他们认为牺牲部分现实利益以换取价值诉求,从长期看是值得的。从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看,美国可谓一帆风顺、鲜有挫折。形成美国对外交事务态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美国“没有悲剧的经验”,在历史进程中“幸免于灾难”,其“国内经验无与伦比地成功”。28自建国以来至本世纪初,美国国力总体上也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美国人自信,历史经验为其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法则中取得胜利的信仰之有效性提供了充分的佐证。国内集团在价值和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时,带有更多理想主义的共识。
如今,美国相对国家实力步入前所未有的下降阶段。无论外部世界或其国内,均感受到相对国力和全球控制力的下行趋势。然而,衰落中的全球霸主已经不可能退回其实力弱小的年代所采用的那种“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来维护已然四处扩张的价值观诉求。一个深信其优越的信仰令国家无往不利的商业民族能否承受未来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之间越来越大的失衡?美国是一个在对外行为中不断寻求合法性基础的国家,当这种道德合法性地位的谋求必须付出过度消耗其国力的投入时,美国对外战略决策将陷入困境。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帝国越过其能力所及的军事扩张边界将导致国力式微那样,帝国价值扩张的边界同样受制于国家实力,并会在超出负荷的情形下加速国力的衰落进程。尽管美国人仍相信其价值目标本身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然而未来的美国不再具备以“帝国”的方式在全球推行自身价值观的条件。强行为之不仅负担沉重,而且将令其手段和过程较之目标适得其反。
当相对实力的衰落令美国的价值观与其现实利益目标之间渐行渐远,其对外决策开始更为频繁地处于如下两难境地:一边是就其国力而言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价值负担,另一边则是国内集团对现实收益的热切期待。当不能以较小的代价令“美国精神”或“美国梦想”在道德层面上得以保全,或者仅仅牺牲较低层次的价值原则来最大限度地确保现实利益时,美国对外战略的困境便得以显现。面对价值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相互排斥,以及各种具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其国内集团政治开始出现明显分化,并严重干扰国家对外决策的一致性。这种困境进一步蚕食着美国国内越来越难以达成的价值认同,对其对外战略形成明显的掣肘。亨廷顿对此有深刻的洞见。他指出,美国与一般民族国家不同,不是由天然的血缘、民族和地域所构建,美国人内心所谓“我们”的概念是基于不同的族群在“新大陆”逐渐形成的价值认同。美国国家利益来自其独特的国家特性,其界定首先在于“我们是什么人”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如今,美国在对外战略和政策上的争论,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是什么人”这一方面存在越来越严重的分歧。随着族群政治的分裂,美国价值观的认同越来越难以达成,这不仅令美国社会陷入分裂,而且导致其对外战略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29
基辛格在谈到美国外交政策的两难抉择时,不无感叹地评论道:“命运把一个相信只要一套基本原则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推到一个具有多样性历史演变并需要做出选择性战略的世界”;如果不能区分自己“必须做什么,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它将“耗尽自己的心力和物质资源”;因此,美国必须取得这样一种平衡,即“把它的价值观转化为解决一些棘手难题的答案,例如什么是必须竭力防止的,无论采取的手段有多痛苦?什么是必须努力实现的,无论支持的国家多么少,必要时甚至单干?哪些不公正现象必须得以制止和消除?以及哪些目标超出了国家的能力所及?”30
这些基辛格所谓的“棘手难题”,实际上是如何界定美国对外战略中谋求价值目标的可能性边界。约瑟夫·奈(Joseph S. Jr. Nye)为美国在全球的人道主义价值干预提出了四项重要原则:被普遍视为一项正义的事业;手段与目的相称;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尽可能以现有且具有很强说服力的国家利益来加强该项人道主义事业。31其中前两个原则涉及价值诉求的合法性,而后两个原则是实现价值诉求的成本—收益边际值计算,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收益。对于这一点,奥巴马总统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强调美国的安全“源于事业的正义性、典范的感召力以及谦卑和克制的平衡作用”,并提醒美国人“审慎使用实力会使美国更强大”。作为一个需要依靠道德解释达成内部共识的宗教国家,美国对外战略在逐利的过程中必须继续承担获取价值合法性的成本,即便二者无法达成一致。美国精英阶层明白,如何将包括价值诉求在内的所有问题,纳入到一个综合的定价体系中进行考量,从而实现在国家实力衰落的约束条件下获得最优的投入—产出比,是美国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核心问题。
如今的美国,国家实力的下降令其对外战略中的价值负担与现实利益之间摩擦不断。如此背景下,“巧实力”(smart power)战略成为美国的“外交新理念”。32事实上,所谓“巧实力”概念的提出,体现的正是在相对实力衰落过程中,被价值与现实利益目标冲突所拖累的美国所采取的战术调整。“巧实力”并非一套目标明确的对外政策或理念,它是基于对外二元目标最大化的美国式逻辑而确定的一种外交策略,其核心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平衡美国在全球的价值诉求及现实利益需要。按照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和奈的解释,所谓“巧实力”战略,意指灵巧地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利用各种影响力的组合获得想要的东西,以实现美国对外目标的“工具箱”,33其目的是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提高对外行动的合法性,重振全球领导地位。34“巧实力”的实施作为一种功利、圆滑的战略或战术,它蕴含了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商人秉性。这一战略的本质是为衰落中的美国维持软实力与硬实力、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意识形态同现实利益、国内事务及全球议程之间的平衡。
在相对实力走向衰落的时代,美国国内集团在实现对外价值目标所需承担的代价面前无法取得共识,这迫使商业理念深入骨血的美国精英阶层不得不努力在两大目标之间寻求投入—产出最大化的战略。鉴于维系单边霸权所支付的价值和财政成本越来越超出国内集团的心理承受能力,美国会主动接受并塑造一个以其为领导、分享其力量、共担其风险和责任的多边世界,以求在重新巩固道德合法性基础的同时,分散帝国统治成本。美国在多边体制下实现价值和利益目标的融合,其追求的理想结果是最大程度享受超级大国收益的同时,尽可能让其他国家分担治理成本。因此,在未来存在多边权力中心的世界实施对外政策时,美国不仅需要支持其“精神领袖”地位并与之共同塑造符合所谓自由和民主文化体系的价值伙伴,而且必须找到与其共同分摊世界日益增加且需求迫切的全球治理成本、维护国际和地区秩序有效运转的利益伙伴。换言之,美国最有效平衡两大目标的实现条件是:一方面令与自身持有相近价值观的大西洋盟国继续为保卫人权、支持新的民主政体增加投入,另一方面联合与其拥有相互依赖关系或共同利益的新兴大国一起应对全球治理的挑战。
四、美国对华战略前景展望
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美国的价值认同和现实利益目标难以相互适从,这导致美国国内对华态度的摇摆。对美国人,特别是其精英阶层而言,中美之间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分歧与难以割裂的商业利益共存。在以何种姿态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国内不同社会层面和集团之间争论不断。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之间的排序,以及各集团利益本身的差异,使美国对华政策具有较大的伸缩空间。价值和利益之间的钟摆随着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954年日内瓦国际和平会议上的“握手事件”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当时周恩来总理和国务卿杜勒斯在无法回避的场合相遇,面对周恩来主动伸出的右手,反共立场坚定的杜勒斯沉吟片刻后,最终选择摇首弃之而去。为坚持某种价值原则而弃外交礼仪于不顾,不仅要求政治家具有过人的勇气,其背后更有赖于压倒性的国家实力的支持。当年,具有“自由世界领袖”之道德合法性地位的美国,同时也是拥有其他大国难以望其项背之实力的美国,它有充分的能力将自身信仰的所谓价值原则一以贯之。
如今,双方力量对比形势早已不复当年。疲惫不堪的超级大国美国,如何面对一个被其视为“异教文明”,然则每年以高于10%的增长率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精英阶层深刻认识到,衰落中的西方世界已经不能阻止中国活力四射的发展势头,和与之俱增的各个层面的消费需求。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异己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在经济领域30年连续不断的成功,给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正按照自己的模式摸索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其目前所取得的成就不但对美国倡导的“西方民主模式”惟一性展示了经验上的反证,同时还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另一条实现长期发展的选择道路。如今,中国正以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令美国精英阶层感到深度忧虑的是,一旦中国发展模式不仅在经济上,同时也在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等领域继续取得成功,其行为及示范作用会破坏他们二战之后有意营造及背后支持的全球“民主化”进程。他们进而猜测,崛起中的中国可能会逐渐将美国的势力排挤出亚洲,然后着手建立新的亚洲文化秩序体系。他们认为,在传统中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中国有可能产生大国沙文主义的权力意向。如果美国的势力被迫撤走,中国在本世纪便有可能将亚洲恢复到过去曾有过的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秩序体系。35中国在亚洲的文化重建在他们看来,具有历史和现实条件。一方面,传统中国文化在亚洲,特别是东亚拥有深刻的历史影响;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增长模式和理念,即所谓“北京共识”,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号召力正在不断增强。
虽然美国统治阶层在某种程度上,视崛起中的中国为价值观念“异己”的挑战者,但他们同样认识到,与美国历史上其他对手,特别与前苏联相比,中国在价值和利益两个层面与美国的关系又具有其特殊性。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做的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中,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对美中和美苏关系进行了比较:两者相比,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进行最后的搏斗,不认为自己在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的斗争,也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程序。36特别是步入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的中国,其发展更是为积累财富和改善生活的强烈欲望所驱使。1976年至1985年,曾先后四次访华的尼克松对此颇有感触。在最后一次访华过程中,他曾作出如下对比:1972年他访问中国的五天时间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只关心战略大事和苏联的军事实力”,“从来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在时过境迁的20年后,彼此交谈的“几乎都是经济问题,并且是中国的特色”。他还表示:“尽管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共同的利益把我们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37
和美国历史上与其他诸大国的竞争关系相比,中美之间有着更为现实和密切的利益纠葛。这尤其有别于冷战期间几乎被切断了经贸往来的美苏关系。美国精英阶层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在经济领域提供的配合,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为保持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优势,需要中国这一庞大的市场支援。它既有赖于获得中国生产的各种制造产品,同时渴望中国动用其储备对美国国债、其他债券等金融产品进行投资。美国的精英集团在华更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他们同时看到,美国在许多重大国际事务及地区事务上也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38在和中国缺乏有效关系的情况下,美国对许多国际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会变得难以施展。
美国决策界人士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其心态通常是矛盾的。在他们看来,中美之间很难寻求到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但是两国关系已经深深扎根于共同利益之中。39他们认为,虽然“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意味着新的挑战”,尽管“两国在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方面有重大分歧”,“美国对中国在人权、宗教自由、劳工制度和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持深度警惕态度”,但是“美中双方应当并且能够共同完成的事宜众多”,不希望“让双方的分歧阻碍两国共同追求的目标”。40美国不愿意,也不大可能为了遥远的“理想”而放弃眼前在华的巨大收益。
中美之间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商业和全球治理方面亲密的利益伙伴。面对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既尝试各种途径阻止、延缓它的上升势头,又不甘心放弃分享其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之机会,而且必须与之合作推行全球战略。如今及未来的中国对美国精英阶层而言,在价值观上仍然难以相容,现实利益则随着中国的快速上升过程而一分为二。美国精英阶层一直试图寻找这样一条两全之策:它既能够行之有效地约束中国,以致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其打破国际既得利益格局和挑战西方价值观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它又可以在一定程度和时间范围内容纳中国发展,以确保美国精英阶层珍视的商业利益。41
鉴于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不断加深的国际相互依赖,美国难以行之有效地通过传统“遏制”手段限制中国发展。美国精英阶层最倾向的方式是积极地通过国际规则来规范中国,令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42一方面使其为美国的全球统治分担部分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美国制定的国际制度钳制中国发展,这将成为美国长期针对中国的战略。
为了避免中国利用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在周边建立主导性优势,美国大战略的制定目标开始更多转到中国和东亚地区。43不过在实施其重返亚洲战略时,为了降低投入成本,美国会尽量减少直接军事干预,而是充分利用亚太地区由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发挥作用。美国一方面夸大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令中国周边国家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另一方面借助这些盟国或准盟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联合其对中国形成反制。在全球范围,美国精英阶层则越来越倾向于联合西方盟友,将“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包括价值观念在内的一系列“西方规则”对中国进行规范化。在他们看来,如果让中国成为西方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令其观念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取得一致,那么美国就仍可以有效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尽力引导或施加压力,令中国融入以西方主流价值观为中心的秩序体系,并努力提高该体系在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后仍可继续生存和壮大的可能性。44
注释:
①Robert Kagan,“The Benevolent Empire,”Foreign Policy,No.111(Summer 1998),pp.24-35.
②[美]乔治·索罗斯:《美国的霸权泡沫——纠正对美国权力的滥用》,燕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0~141页。
③[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④Coral Bell,“American Ascendancy and the Pretense of Concert,”The National Interest,Vol.57(Fall 1999),pp.55-63.
⑤Condoleezza Rice,“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8,pp.2-26.
⑥[美]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4~25页。关于美国扩张背后所承担的巨大财政代价,另可参见[美]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警钟——美国共和制的衰亡》,周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反弹——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与后果》,罗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⑦Carol Lancaster,“The Chinese Aid System,”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2007,http://www.cgdev.org.
⑧同注⑤。
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第209页。
⑩[美]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杨仁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11Zbigniew Brzezinski,Second Chance: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New York:Basic Books,2007.
12[意]米歇尔·克罗齐、[日]绵贯让治、[美]塞缪尔·亨廷顿:《民主的危机》,马殿军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1页。
13[美]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第350页。
14[美]孔华润:《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载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4卷,王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
15[美]莫尼卡·克罗利:《不在案的记录:尼克松晚年私人谈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16[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美]吉米·卡特:《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汤玉明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18Earl H.Fry,Stan A.Taylor and Robert S.Wood,America the Vincible:U.S.Foreign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94,p.113;Ali A.Mazrui,Cultural Forces in World Politics,New Hampshire: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c.,1990,p.7.
19[美]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岩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45页。
20[美]吉米·卡特:《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第1、101、106、107、114、168页。
21Francis Fukuyama,After the Neocons: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London:Profile Books,2007.
22Stephen D.Krasner,“U.S. Commercial and Monetary Policy:Unraveling the Paradox of External Strength and Internal Weaknes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1, No. 4(1997),pp.635-671.
23[美]吉米·卡特:《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第6、8页。
24[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第210~219页。
25[意]米歇尔·克罗齐、[日]绵贯让治、[美]塞缪尔·亨廷顿:《民主的危机》,第142~144页。
26Cecil V.Crabb,The Doctrin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ir Meaning,Role,and Future,Baton Rouge,LA: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p.67,转自董秀丽(主编):《美国外交的文化阐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27[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朱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8Henry Kissinger,“Reflection on American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56,pp.19-56.
29[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9~10页。
30[美]亨利·基辛格:《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胡利平、凌建平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357~358页。
31Joseph S.Jr.Nye,“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9,pp.22-35.
32 “巧实力”一词最早由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于2004年提出。她在《外交》杂志的同名文章中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的重要性,认为“巧实力”战略是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延伸。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小约瑟夫·奈共同发表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应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以恢复其国际影响力。Suzanne Nossel,“Smart Pow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4,pp.131-142;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Jr.Nye,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A Smarter,More Secure America,Washington,D.C:Report fo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7,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71106_csissmartpowerreport.pdf。
33具体说,美国的软硬实力工具箱包括四大工具。按各种工具使用强度(由硬到软)排序,军事最强,外交次之,经济再次,最后为文化。其中军事工具包括动用战斗力量,以及在进攻、防御和报复性军事行动中使用战斗力量的威慑等;外交工具包括运用政治力量、本国的治理体制、同盟关系及其他国际关系等;经济工具包括施展其经济实力、经济援助、贸易、对外投资、财政状况及优惠的贸易协定等;文化工具则包括利用媒体、信息、公共外交、交流、传统,以及一些美国行动所导致的无形物,例如信誉、信用、普遍的友善等。详见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China’s and U.S.Diplomacy,Foreign Aid,Trade,and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CRS Report for US.Congress,RL34620,2008,http://www.usembassy.it/pdf/other/RL34620.pdf。
34参见唐彦林:《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
35阎学通:《西方人看中国的崛起》,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9期。
36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Deputy Secretary State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21,New York City,2005,http://www.ncuscr.org/articlesandspeeches/Zoellick.htm.
37[美]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第233~234页。
38[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770页。
39同注⑤。
40Hillary R.Clinton,“Security and Opportunit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07,pp.2-18.
41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双重目标和策略博弈,参见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
42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梁亚滨:《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再保证:霸权衰落下的中美关系》,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
43参见吴征宇:《地理政治变迁与21世纪前期的美国大战略》,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2期;潘亚玲:《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
44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Jannuary/February 2008,pp.23-27;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Penguin Group Inc,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