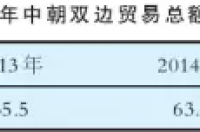这是一个被信仰传统相悖的各方之间的宗教斗争蹂躏的地区。但冲突也存在于军方和温和派之间,并受到试图捍卫自身利益、扩大影响力的邻国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冲突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存在;内战和代理战争已难以区分。政府往往无力控制游曳在国内和国家间的军事或其他小集团。生命的损失触目尽心,更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这可以是当今中东的写照。事实上,它描述的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欧洲。
在2011年的中东,一位受尽屈辱的突尼斯小水果贩自焚以示抗议,拉开了剧变的序幕。在几周时间里,中东地区已成燎原之势。在十七世纪的欧洲,一场波西米亚新教徒与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帝费迪南二世的地方宗教冲突引起了一场时代冲突。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转向日后成为德国的领地内宗教盟友寻求支持。许多当时的列强,包括西班牙、法国、瑞典和奥地利,纷纷卷入其中。结果是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欧洲历史上最暴力、破坏力最强的事件,直到20世纪才被两次世界大战超越。
1618—1648年的欧洲与2011—2014年的中东存在显著不同。但相似点也很多——并且令人警觉。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三年半后,我们正在目睹的极有可能只是一场长期的、代价沉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初级阶段;事件极有可能朝着更加糟糕的方向发展。
该地区是动乱的温床。其大部分人民在政治上孱弱不堪,并且一贫如洗,前途渺茫。伊斯兰教从未经历过类似于欧洲的宗教革命;宗教和世俗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并且互相冲突。
此外,国家身份通常与宗教、宗派和部落身份冲突,并且被后三者压制。公民社会十分孱弱。在一些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的存在阻止了多样化经济的产生,中产阶级也无从兴起。教育强调机械学习而不是批判性思维。在许多国家,极权统治者不具有合法性。
外部性东方的作为和不作为起到了火上加油的效果。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重要事件,它加剧了该地区最重要国家之一的逊尼派-什叶派冲突,结果是该地区其他许多分裂社会的这一冲突也纷纷抬头。利比亚的政权更迭产生了一个失败之国;对叙利亚政权更迭的支持漫不经心,为持久内战提供了条件。
中东地区的动向令人担忧:弱国无力治理领土;极少数相对较强的国家为主宰权而互相争夺;军事和恐怖组织影响力日盛;而国家边界日益模糊。地方政治文化分不清民主和多数人统治,选举沦为巩固而不是分享权力的工具。
除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和生命损失,中东动荡最直接的副产品是严重而频繁的恐怖主义——不但在于中东内部,而且正在从此走向世界。能源生产和运输受到了干扰。
外部人所作所为是有限的。有时决策者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防止事态恶化而不是雄心勃勃的改进计划;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
首先,这要求阻止核扩散(从伊朗开始),不管通过外交还是制裁实现,甚至在必要时采取破坏和军事打击。否则的话局面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中东不少国家以及通过它们的军事和恐怖组织将获得核武器和原料。
降低全球对中东地区能源供给依赖的措施(包括改进燃料效率、开发替代资源)也很有意义。应该马上对约旦和黎巴嫩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它们应对涌入的难民。土耳其和埃及的民主进程应该专注于强化公民社会、创造分散权力的强大宪法。
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现已自称为“伊斯兰国”)等组织的反恐行动必须成为常规动作,不管通过无人机、小型突袭还是训练和武装本地合作伙伴实现。应该认识到,伊拉克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如今,与其说伊拉克是对抗伊朗的堡垒,不如说已经沦为伊朗的势力范围)。应该支持沿伊拉克原有内部边界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Kurdistan)。
我们不容幻想。政权更迭不是万灵丹;它可能难以实现,并且几乎不可能巩固。谈判不能解决所有冲突,甚至不能解决大部分冲突。
眼下,从以色列-巴勒斯坦争端看,这显然是正确的。即使发生变化,全面和解也只是有助于本地,而无法影响邻国或冲突动态。尽管如此,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狭隘停火仍是值得追求的。
类似地,只有在接受叙利亚的现实(包括巴沙尔政权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存在)而非试图改变它的情况下,外交才有可能在叙利亚起作用。答案不在于勾勒新地图,尽管一旦人口发生改变并且政治稳定得到重塑,承认新边界将是可望且可及的。
决策者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对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在新地方秩序出现或冲突各方都筋疲力尽之前——中东与其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需要管理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