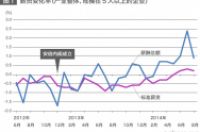出版:中信出版社
乔·史塔威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便活跃在亚洲新闻业,是《中国经济季刊》的创办人、《经济学人》知名撰稿人。与他之前颇有影响的《亚洲教父》和《中国热》等著述不同,在《亚洲大趋势》中,他试图以更高视角剖析亚洲的发展路径。他先从地缘角度将东亚划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阵营,东北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在此基础上,他通过深入分析两大阵营的土地、制造业和金融业,探寻曾一度紧随“亚洲四小龙”欣欣向荣的东南亚诸国为什么会陷入发展反转?东北亚的韩国却能突破金融危机获得新生?日本为什么在接近巅峰时陡然陷入长年徘徊等问题。当然,笔者最关心的是史塔威尔对当下亚洲趋势下中国发展路径的探索分析。
农业发展当厘清虚实
2002年,史塔威尔在接受《经济观察报》的访问时说,“亚洲有三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基本上按照它们的模式发展”,他们都“进行了土地改革,把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提供给制造业”。在《亚洲大趋势》中,史塔威尔进一步延伸了前述观点,认为东亚的土地问题具有较强的地域特性,即人多地少。土地政策变革前,东北亚农民群体庞大,农村土地政策变革贯穿了新中国的发展史。从土改到集体大锅饭,再到凤阳农民“闯”出的联产承包制,农村土地发展经历了破、立、破的曲折轨迹,总体来看还是土地再分配的尝试。史塔威尔认为,如果没有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几无可能。不过,他同时又认为,这种改革虽然让失地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因为缺乏所有权的支撑,失地风险如影随形,这在一些地方近年推进的“农民上楼”运动中表现极为突出。
中国农业发展将向何处去?史塔威尔只是给出了产权问题,这显然不够。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通过多年观察研究后完成了中国“农业经济史三部曲”,认为受地力、人力以及膳食结构等诸多因素制约,欧美的农业发展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固化,虽为土地流转铺平道路,但同时也孕育了“新失地”风险。虽然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用工荒”,但以当前非农行业创造的岗位,难以消化因失地而“制造”的大量劳动力。所以黄宗智认为,农业发展的出路在于培育“家庭小农场”,即以血亲和姻亲“控股”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不过,虽然土地至今仍然可以为农民提供“兜底”生存保障,但纯粹务农,致富难度极大。而大量从课堂直接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二代”甚至根本就没想过,有朝一日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实际上,在许多地方,农业经济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地体现出“非农化”,与此对应的是土地抛荒现象在许多地方极其普遍。
或者说,土地平均分配只是解决了生存而非富裕问题,这不是真正的农业经济。没有发展,城乡差距必将进一步扩大,而差距同样会成为孕育社会危机的“沃土”。顺便提及的是,由于受到政策有力呵护,2013年日本农民收入超过了普通公务员。而韩国农民收入一直在相当于城镇居民八成左右的水平上徘徊。
工业制造需摒弃虚胖
从1990至1996年,泰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约达8%。然而,一场金融危机,使泰国经济一落千丈,社会危机不断,冲突延续至今。而同样遭受金融危机的韩国,经过短暂波折后,重整精神,1999年便实现了复苏(增长率达到9%),此后数年保持了5%至6%的较高增速。
之所以会有如此迥异的结果,史塔威尔认为除了金融管控因素外,两国工业结构起了关键作用。金融危机前的泰国虽然经济增速较高,但大多是低端外包加工,缺乏知识产权含量,没什么附加值,说直白点,赚的是点加工费。一开始韩国与泰国没太大差别,但韩国很注重培育规模性的民族企业。当然,仅有规模不够,还必须让这些企业勇于直面国际竞争。为此,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既在培育大企业方面给予种种优惠,同时要求这些企业必须满足出口条件。在严格的出口纪律下,现代、三星等韩国企业在摔打中迅速成长。相比之下,我们很难记起泰国有什么响亮的国际品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来一补”外资企业在中国沿海遍地开花,满足了开放初期的外汇需求,同时有效吸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2013年,进出口总值达4.1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更是高达8.3万亿美元,坐稳全球第二把交椅。2014年中国上榜世界500强的公司数量创纪录地达到100家,数量上似乎能给人以美好的想象,但靠政策拼凑和垄断“壮大”的国企依然占比极大。
总之,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就必须坚决摒弃虚胖,即不能仅凭其数量与规模,比如那些靠政策垄断上游资源的大型国企,而要看其是否具有创新力,是否有能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金融政策当不慕虚名
1997年的金融危机后,泰国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加快了金融开放步伐。不过,此后十多年的发展充分表明,这些“良策”并没能真正救挽泰国经济。史塔威尔认为,其原因在于泰国经济实力有限,羽翼未丰之时便急急地洞开金融大门,这种接轨,实际等同将金融话语权拱手出让,丧失了政府通过金融政策发展农业和培植优势企业的能力。
基于每个国家所面临现实的巨大差异性,发展并不是简单地打开一扇国门那么简单。史塔威尔感到,越是发展初期,金融自主控制权越是重要。这种控制权虽然会遭到外界不开放的指责,但可以为国内还显虚弱的经济提供有效庇护。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常常会遭到来自外部的“威逼利诱”。史塔威尔认为泰国是反面典型,而韩国则是正面典型。1957年,韩国一度臣服于美国的“改革”要求,但三年后朴正熙将银行又重新收归国有,并认为,“一个得到妥善管理的银行体系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个是必须接受政府的管制,另一个是必须满足发展重工业的融资需求”。事实上,正是朴正熙开启了韩国经济腾飞时代。
金融作为资源分配的重要调控手段,“可以引导一个国家有限的金融资源去扶持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但是,政府金融控制权与政府控制金融不应混同为同一概念。金融控制权意味着政府只是占控制主导力量,而政府控制意味着金融的一切活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政府决策。虽然后面的管控能更有效抵御金融危机,但过于行政化的金融体系并不能满足市场规律的需要。比如,金融控制权下的银行可以参考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而后者则可能出于平衡地方发展差距或政绩发展需要,分摊一些并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行政性融资任务,增加坏账风险。
由此观之,金融发展既要不慕开放的虚名,至而沦为国际金融大鳄的鱼肉对象,也要力避过于行政化至而偏离市场轨道。毕竟,金融业发展最终要顺应市场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