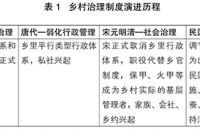——以反支配的权力为视角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呈现上升趋势,移民上访、土地维权、环境抗争、业主维权和工人抗争等问题不断增多。批判性地考察现有的社会抗争问题研究,可以发现,既有的分析基本上未曾以权力为核心来解释社会抗争现象。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在于,现有的权力分析往往将权力等同于支配,将权力主体等同于支配者,因而不太可能从权力的角度深入阐释社会抗争现象。事实上,现实社会中不仅存在支配性的权力,也存在反支配的权力(power as anti-domination)。从反支配的权力角度分析,社会抗争是由于某些行动者受到支配性权力的压迫导致的,其本质是抗争者通过生产或激活反支配的权力以实现自身诉求,其动力来源于抗争者所生产或激活的反支配的权力,其过程则体现为反支配权力的生产与运用过程。本文依据相关研究者的田野调查案例,在简要阐释反支配权力的意蕴基础上,重新探讨社会抗争何以可能的根本原因与动力机制,分析反支配权力的生产机制和运用策略,以期为社会抗争问题研究提出一种具有概括性、解释力与综合性的阐释。
社会抗争的动力机制再审视
在学术界,现有的研究基本上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抗争是由于某些行动者在物质或伦理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损导致的,是他们在外部力量压迫下采取的自我救济行为。于建嵘就曾指出,集体维权抗争的原动力在于某些人受到“集团”外部的“压迫”,使他们采取各种“压迫性反应”的方式实施抗争:“这种基于共同压力完成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及共同的利益诉求的形成,正是集体行动得以发生的决定性条件。”①然而,需要追问的是,那种“压迫”某些行动者的外部力量究竟是什么呢?某些行动者实施抗争的根本原因与动力机制究竟何在呢?
在社会抗争事件中,抗争者所针对的对象既可能是那些实施征地、拆迁、排污等行为的企业及其员工,也可能是地方政府机构及其公职人员。具体而言,社会抗争对象往往通过决策制定、议程控制或偏好塑造等方式损害某些行动者在物质或伦理方面的合法权益,因而引起社会抗争。
第一,在决策制定的情形中,社会抗争者和抗争对象往往会在某项或某些关键议题的决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存在冲突行为,并且由此导致权益受损。在这种情形下,尽管抗争者能够参与决策制定,然而,他们却往往会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压制。其原因在于,社会抗争对象通常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能够通过决策制定实现自身利益,而社会抗争者则往往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处于被支配或从属地位,其权益会被抗争对象的决策制定所损害。在吴毅考察的某石场纠纷案例中,抗争者就曾对镇政府在决策制定中的支配行为表示不满:“听说一个场子只补偿三五万,政府这样干,我们就亏大了。我们准备上访,要么提高赔偿标准,要么让我们再生产一段时间,把本钱弄回来。”②
第二,在议程控制的情形下,社会抗争对象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限制决策制定参与者的范围,将其他行动者可能提出的替代性方案或议题排斥在议程之外,使各种不符合其需要的方案或议题根本不可能进入决策过程;社会抗争者则被排斥在决策制定过程之外,他们根本无法使那些符合自身诉求的方案或议题被纳入决策议程。闫丽娟和王瑞芳在调查农村征地抗争时指出:“S村的征地事情始于2008年,即移民安置之时。作为县政府安排的任务,镇政府与村干部合力为之,他们想以一种私相授受的行为强行征地,而不顾及普通村民的利益。当村民得知事情的时候,尤其知道征地价格之后,自然就会抵触。这根源于农民最痛恨最担心的暗箱操作。”③在这里,所谓的“暗箱操作”事实上就是通过议程控制将某些利益相关者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
第三,社会抗争对象也可能试图通过塑造偏好的方式构建某些行动者的态度、情感与价值判断,甚至使他们形成自我贬损、自我蔑视的心理认知与行为倾向。应星描述道:“下午,县政府一个副县长带着县政府工作组赶到现场。这个副县长一来就训斥群众:‘把你们江边人喂肥了,不听话了?’结果他这话激怒了众人,众人要去追打他。副县长情急之下,居然被逼得跳到江里,后被当地的派出所所长救上来。”④从本质上讲,上述副县长认为群众应当“听话”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将群众比作被“喂肥”的家禽家畜,将他们看作处于依附地位的被支配者。也就是说,副县长实际上是想影响群众的意愿和判断,塑造和强化他们的依附观念,提醒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份,使他们接受自身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境况,其结果必然会使群众感到蔑视、侮辱和屈辱,因而采取抗争行动。
在社会抗争过程中,无论是运用决策制定与议程控制的方式约束他人,还是通过塑造偏好的方式影响他人,上述社会抗争对象都运用了各种“限制他人选择的能力”⑤,都“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要“贯彻自己意志”⑥。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压迫”抗争者的外部力量实际上就是某些行动者所运用的支配性权力。因此,那种具有支配性的权力是抗争者受到“压迫”的根本原因,而社会抗争则是抗争者针对那些实施支配行为的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支配是抗争的开始”⑦。然而,无论是行动者遭受支配性权力的外部“压迫”还是他们的合法权益受损,都仅仅是社会抗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针对支配性权力的“压迫”,社会行动者可能具有抗争的意愿,也可能不具有抗争的意愿;可能具备实施抗争的能力,也可能不具备实施抗争的能力;可能会采取各种方式积极抗争,也可能选择妥协、退让、忍受或顺从。由此可见,即使某些行动者受到支配性权力的压迫而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他们也不一定会采取抗争行为,而是可能通过妥协、退让、忍受或顺从等方式接受现实。
从根本上讲,由于行动者是针对各种支配性权力的压迫而实施抗争的,所以,社会抗争在本质上就是抵制或反抗支配性的权力。“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⑧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塑造出相应的权力,社会抗争者才可能抵制、反抗甚至颠覆抗争对象所运用的支配性权力。在社会生活中,权力不可能被某些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完全垄断,而是不均衡地、弥散性地分布于所有行动者中间。实际上,尽管不同行动者掌握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存在差异,但是,无论是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还是工人、农民或小商贩,任何行动者都会掌握某些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都可以通过动员某些资源获得权力。也就是说,那些由于支配性权力的作用而导致合法权益受损的抗争者并非完全被动的服从者,他们也是拥有资源动员能力的行动者,可以在既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动员各种资源塑造出权力。社会抗争者的目标不是支配他人,而是影响、干预、抵制或反抗特定支配性权力的运作,使其受到约束,挫败支配者的预期目标,改变既定的事态或事件进程,削弱或颠覆自身在物质或伦理领域中受到的剥削、压迫或蔑视,甚至变革既定的具有支配性的社会资源配置规则。社会抗争者所塑造的权力就是反支配的权力。反支配的权力既表明某些行动者具有反支配的意愿,也意味着他们具有反支配的能力,能够动员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实施反支配的行动⑨。
反支配权力的生产机制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抗争之所以存在,其原因在于某些行动者不仅具有抗争的意愿,而且具有抗争的能力,可以生产出反支配的权力。那么,反支配的权力是如何生产的呢?它的生产机制是怎么样的呢?在既定社会中,任何权力都是由某些行动者的共同行动生产出来的。权力“所对应的人类能力不仅仅是行动的能力,而且是共同行动的能力。权力绝对不是属于某个个人的所有物;它属于某个群体并且只有在这个群体聚集在一起的情形下才能维持其存在。”⑩反支配的权力亦不例外。下面,本文将结合相关学者的田野调查经验分析反支配权力的生产机制。
在社会抗争过程中,反支配的权力是那些受支配性权力压迫的行动者通过凝聚共同力量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其能否成功生产则取决于抗争者彼此间的团结。潘毅等在调查建筑工地农民工为拿到应得的工资而抗争时指出,“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已成为建筑工人的基本共识。“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成长,他们知道只有依靠自己,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11)在抗争过程中,工人们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办,人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着你,有钱也不给你。”(12)在这里,建筑工人所具有的“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的共识,既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社会抗争成功的基础在于“力量”,又表明他们对凝聚“力量”的方式具有深刻的认识,即“力量”来源于工人们的集体行动与团结。由此可见,在社会抗争过程中,那些受到压迫的建筑工人是通过共同行动凝聚“力量”来抵制、对抗甚至颠覆各种支配性权力,他们的“团结”是生产反支配权力的基础。
上述建筑工人的经验表明,社会抗争者所生产的反支配权力的强弱是决定抗争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他们生产的反支配权力越强,其抗争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他们生产的反支配权力越弱,其抗争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反支配权力的强弱依赖于抗争者的数量和意愿,也就是依赖于抗争者动员资源的能力:抗争者数量越多,抗争意愿越强烈,他们抗争的能力就越大,所能生产的反支配权力就越强。黄振辉在分析“表演式抗争”时指出,“表演者的数量越多越可能被定义为‘人民群众’,越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政治问题,越有可能被纳入政策议程。……无论是道德势能还是身份势能都不足以左右表演式抗争的实际效果,对表演式抗争的实际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表演本身的政治势能。……抗争者的数量越大越有可能被定义为‘人民群众’,问题被解决的概率越高。”(13)从权力的角度分析,“表演者的数量”之所以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其直接原因是有关“人民群众”界定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那些实施抗争的“表演者”数量越多,他们生产的反支配权力就越大,也就越可能影响政府部门以实现其诉求。这也就是有学者所分析的社会抗争者“闹大”现象的生产逻辑(14)。
在反支配权力的生产过程中,反支配的权力与支配性的权力存在着冲突,所以,社会抗争者需要处理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他们需要凝聚内部共识,化解各种内部分歧,尽可能塑造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抵御各种外部压力,抵制或反抗那些运用支配性权力的行动者。在这种情形下,抗争者面临的困境在于,他们既要“安内”,又要“御外”:“安内”是基础,抗争者只有实现内部团结才可能生产更加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御外”是目的,抗争者生产出反支配权力的目标就在于抵制与反抗外来压迫。如果抗争者内部分歧太大,缺乏凝聚力,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生产出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如果他们面临的外部支配性力量过于强大,那么,他们也可能在外部力量的操纵、诱导、威慑或直接压制下分化瓦解,甚至成为一盘散沙。所以,在反支配权力的生产过程中,各种行动者彼此间会不断地拉扯、妥协与平衡:那些实施支配的行动者试图拉拢抗争群体以及中间群体中的某些成员,削弱反支配群体的力量;那些反支配群体的核心成员则试图拉住处于摇摆状态的犹豫者,壮大自身的力量。
由于反支配权力的生产面临上述困境,所以,社会抗争者的组织化程度就尤为重要,他们的组织与动员能力是影响反支配权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将决定着支配—反支配的斗争发展态势。俞志元在比较分析乙肝携带者的反歧视行动、血友病感染艾滋病患者的维权行动与输血感染艾滋病患者维权抗争行动的案例基础上指出,“集体行动组织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对其行动结果有重要的影响。组织能力强的集体行动组织,通过资源动员和对行动话语的塑造对行动结果起到了积极作用。”(15)在通过自身的组织与动员能力生产反支配权力的过程中,社会抗争者往往依赖于既有的组织渠道,期望通过既有的组织渠道凝聚自身的力量。折晓叶认为,在发达的乡村地区,农民往往运用“弱者的‘韧武器’”,借助于既有的村民合作组织和民主参与机制,通过非对抗性抵制与合作的方式反对不公正的剥夺、守护共同的资源并且实现具有可持续性的保障。他们通常采取“审视而具有合法性的方式”,“借助于村民的合力,‘闹出不太大的动静’来,还要借助于合作组织的合法框架,将非正式规则进行正式运作,以集体坚守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政治参与态度”(16)。从权力的角度分析,那些居于弱势地位的村民借助于既有的村民合作组织与民主参与机制,通过非对抗性抵制与合作所凝聚的“合作力”,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现有制度和集体组织渠道基础上生产的反支配的权力,也是他们实施抗争的动力。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抗争者的组织化程度是影响反支配的权力强弱的重要因素,但是,即使在组织化程度不高的具有自发性、传统性的抗争行动中,社会行动者也可以通过生产反支配的权力推动抗争。在李晨璐和赵旭东调查的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中,海村村民依照自然习得的传统经验,通过自发的打砸、拦路、跪拜等方式进行抗争。“在海村,村民抗争初期采取的打闹、拉扯、谩骂、拦路、跪市长,是在无引导、无意识中自然表达的行为方式,看似简单、‘落后’,实则暗含相当的影响力。”(17)然而,即使像这样采用原始抵抗的抗争行为,“也可能演化为激烈的群体性抗争,某些抵抗也可能成为一定的政治力量”(18)。这就是说,虽然那些采取原始抵抗的村民组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们通过具有自发性、传统性的共同行动也生产出相对强大的反支配权力。
事实上,即使那些实施个体化行动的抗争者,也可能动员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生产出相对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在“表演式抗争”中,“表演者”可能人数较少,甚至是实施个体化的表演,然而,他们以社会为舞台,通过公开的、戏剧性的、景观化的抗争表演,使自身诉求被观众、媒体和网络传播开来,也可能塑造出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在王洪伟考察的艾滋病村民“以身抗争”的维权案例中,携带艾滋病毒的村民Z威胁颠覆既有的秩序,使其“身体”参与到权力关系的生产中,最终实现了其诉求。“身体成为一种带有支配性的权力……‘身体’的毁灭、伤害和缺陷,成为一种具有政治支配性概念,具有‘权力’意味。”(19)在这种意义上,那种携带高传染性艾滋病毒的、危险的、抗争的“身体”不再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身体,而是通过“身体”的行动卷入权力运作领域;但是,像这样的个体化的“身体”行动所塑造的并非“一种带有支配性的权力”,而是为实现反支配的诉求而生产的反支配的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反支配的权力不仅存在于政府体系之外,而且可能存在于政府体系内部。通常情况下,政府体系内部蕴含的反支配的权力机制处于有待激活的状态,而抗争者的反支配行动则可能激活这样的机制。社会抗争不同于叛乱、社会运动或革命,社会抗争者也不同于叛乱者、社会运动者或革命者。社会抗争者在实现其诉求的过程中并不寻求颠覆现有的政府体制,而是需要诉诸相关政府部门。在社会抗争状态下,抗争者所生产的反支配权力成为激活政府体系内蕴含的反支配的权力机制的基础。只有在生产出反支配权力的前提下,抗争者才更有可能激活政府体系内部的反支配机制,也才更容易实现反支配的诉求。如果抗争者的诉求得到相关政府机构的有效回应,那么,他们就成功地激活了政府体系内蕴含的反支配的机制;反之,如果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有效回应,那么,他们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就会恶化,部分抗争者甚至会采取更加激烈的抗争,以期得到更高层的政府机构的回应,从而激活政府体系内部更加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机制。这就如应星指出的,抗争者认为,只有发生足够重大的“问题”,其要求才可能为上级重视并得以满足(20)。
综上所述,反支配的权力是抗争者在既定社会结构、场域和情境中动员自身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而生产或激活的。在反支配权力的生产过程中,其强弱依赖于抗争者动员各种资源的能力,依赖于抗争者的数量和意愿:抗争者数量越多,抗争意愿越强烈,他们生产或激活的反支配的权力就可能越大。在反支配权力的生产过程中,抗争者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是影响其强弱的重要因素,也将决定着支配—反支配的斗争发展态势。然而,即使在具有自发性、传统性、组织化程度不高甚至去组织化的、个体化的抗争行动中,抗争者也可能生产出相对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
反支配权力的运用策略分析
从权力的角度分析,社会抗争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社会行动者所生产或激活的反支配权力的强弱,而且取决于反支配权力的运用方式和策略。福柯指出,“权力不是给定的……而是在行动中,也仅仅在行动中才能得以实施。……权力……是针对所有的力量关系的”(21),“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称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动作”(22)。因此,有必要从反支配权力的运用方式、策略和技术的角度重新审视抗争行动。
在权力运用过程中,任何形式的权力运用往往都不会是僵硬不变的,而是精巧的、灵活的、多样的和变化的。也就是说,权力运用者应当具有“环境智慧”,使自身策略与目标相匹配,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制定出聪明的战略和策略(23)。反支配权力的运用也是如此。在反支配权力的运用过程中,社会抗争者会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场域和情境中不断地触探权力关系网络,运用各种反支配的策略以实现自身诉求。对于抗争者而言,所有有助于实现反支配诉求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都可以被纳入策略工具箱中,所有处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资源都可以成为其动员对象。从反支配权力的角度上讲,现有的“依法抗争”“弱者的‘韧武器’”“以身抗争”等抗争模式都可以纳入其运用范畴予以描述和解释,都可以归纳为抗争者动员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实施反支配行动的方式。
通常而言,当社会行动者受到某些政府机构、公职人员、企业或社会团体等支配和压迫时,他们不会立即采取体制外的对抗性行动,而是在国家法律规则框架内诉诸相应的政府机构依法抗争。在“依法抗争”模式中,社会抗争者“运用当权者的承诺与言辞来限制权力的运用……能够创造性地运用官方法律、政策和其倡导的价值来反对不遵守法律的政治经济精英……对那些未遵从某种公开奉行的价值理念或实施某些有益措施的当权者施加压力”(24)。从反支配权力的运用策略分析,抗争者之所以诉诸相关政府机构与法律“依法抗争”,根本原因在于,抗争者试图尽可能地激活政府体系内部的反支配机制,通过行政或法律渠道使其实现反支配诉求的成本最小化。在成功实现“依法抗争”的情形下,抗争者所生产与运用的反支配权力与体制内的反支配的权力机制存在着契合之处,他们因而不会游走于体制的边缘或在体制外采取剧烈的直接对抗方式,而是依托于既有体制采取正当的、合法的抗争。有学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认为,当前中国农民上访主要体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非抗争政治的研究范畴(25)。
在反支配权力的运用过程中,抗争者也可能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通过合作、参与、妥协、博弈等策略和技术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身利益。对于那些尚能在既有的集体组织框架内凝聚起反支配权力的村民而言,他们往往既不会运用公开对峙的方式抗争,也不会采取退却的方式忍受压迫,而是运用“韧武器”,“以合作求参与、以合作求保障”,“绕开正面冲突、见缝插针、钻空子、死磨硬缠、事后追索、明给暗藏、出尔反尔、执行不到位等,还有抑‘散’聚‘合’、严守默契、一致对外、聚众掺合、集体决定、共担风险、分享收益,共同沾光,等等”。(26)在这种状况下,虽然抗争者相对于外来力量处在弱势地位,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依赖既有的制度与组织渠道塑造出反支配的权力,所以,他们试图在现有的组织、政策、法律与规则范围中寻找支持,使强势群体能够容纳其某些利益诉求,因而不用采取更激烈的公开对峙方式运用反支配的权力。
但是,在反支配的权力运用过程中,如果某些政府部门对抗争者的诉求完全不作为甚至与支配者沆瀣一气,那么,抗争者就未能激活政府体系内部的反支配机制,因而不得不游走于既定体制的边缘,或者在既定体制之外运用反支配的策略。潘毅等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维权者在遇到政府不作为后会调整行为方式,更加依赖于自身的力量进行抗争。潘毅等指出,“国家给了工人美好的承诺,然而,当工人们一次次满怀信心求助政府部门的时候,却又一次次失望而归。……行政执法部门在劳资冲突中的表现,削弱了工人们对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信心,转而更加依赖自身的力量。我们在工地上看到,很多有过求助政府部门经历的建筑工人,再次碰到权益侵害事件的时候,往往在法律、行政渠道之外选择‘闹’的方式,采取更加激进的集体行动。”(27)刘能也认为,如果政府部门或其成员在处理和消减某些群体的怨恨中表现出失当、不力或无能,不能有效回应公众和受害者的诉求,那么,最终将导致其失去公信力和合法性,引起公众和受害者对政府部门的次级怨恨。(28)所以,在抗争者未能激活政府体系内反支配机制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将相关政府机构视为支配自身的力量,并且重新选择反支配的策略进行抗争。当前学术界所谓的“表演式抗争”“依弱者身份抗争”“依势抗争”“以身抗争”甚至“以死抗争”等实际上都是抗争者在体制的边缘或体制外采取的更加激烈、更具对抗性的反支配权力的运用方式。
在“依弱者身份抗争”的模式中,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诉诸公正、生存道德等观念,运用自身属于弱者的身份生产或激活反支配的权力予以抗争。“他们以自身的弱者符号来缓和直接的抗争,减少自己参与的风险;因此,它虽然体现为一种‘公开的文本’式抗争,唯恐外人不知,但抗争的凭借及手段却又带有‘隐藏的文本’的性质,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赖皮’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降低公开反抗的风险”(29)。通过这种方式,抗争者试图增加自身的符号资本,促进彼此间的身份认同,使其行为与诉求正当化;同时,他们也试图削减抗争对象占有的符号资本,为局外人提供相关的认知与评价准则并且动员他们支持自身行动,尽可能将自身的符号资源转化为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优势。“他们希望以自身的弱者抗争符号直接与抗争对象形成对照,展示自身的弱势,反衬对方的强横,以不惜付出自身的身体、尊严甚至是生命损失的这样一种带有‘破釜沉舟式’(被一般人视为‘无赖式’)的缠闹式抗争,从而引起社会关注或政府重视。”(30)由此可见,在这种方式中,抗争者实际上也是动员有利于自身的社会、文化与符号等资源生产与运用反支配的权力;他们游走于体制的边缘,期待自身的行为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或政府重视”,因而可以激活体制内部的反支配机制以实现其诉求。
相对于“依弱者身份抗争”的方式而言,“以身抗争”和“以死抗争”体现出更加具有对抗性的反支配权力的运用策略。例如,那些携带高传染性艾滋病的抗争者在无法通过政府和法律渠道解决问题后,不得不展示“身体”内蕴含的破坏性力量,运用令人恐惧的“身体”实施抗争,威慑与诱导那些曾经支配他们的行动者。“Z在为子女遭欠薪和人身侵害而讨还公道的过程中,不断按照政策、法律和正常行政程序寻求问题的解决,但最后都付之阙如,出于无奈他才拿出艾滋患者的诊断证明‘以身抗争’,最终以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对艾滋病的恐惧讨还了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31)在各种“以死抗争”的案例中,抗争者采取自残、自杀的行为,以生命本身作为赌注给其他行动者施压,威慑那些实施支配的行动者给予其应得的权益,其实质依然是运用激烈的反支配策略实现其利益诉求。
需要强调的是,在抗争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抗争方式、技术与策略具有内在连贯性,而不会局限于某种单一的行动方式或理论模型。正如潘毅在叙述打工妹的抗争策略时指出,她们“绝不是任资本摆布的驯服的身体,而是机灵和反叛的主体。她们懂得在权力和纪律的夹缝中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展开反叛行动,有时甚至将现有的规则和纪律体系打破。”(32)社会行动者究竟采用何种抗争方式、技术与策略,既会受其所能动员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资源的约束,也是他们在具体社会伦理情境中考量各种现实要素的结果。他们通常试图在政府渠道和法律框架内实现反支配的诉求,只有在这种方式不能解决问题后才游走于体制的边缘或者在体制外采取更激烈、更具有对抗性的方式。然而,即使在那些更加具有对抗性的抗争方式中,社会抗争者依然持有通过政府机构实现反支配诉求的愿望。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即使‘以身’抗争的最后一瞬间,抗争者依然抱有‘依法’求解的心态和姿态。”(33)这也就为有关政府部门化解社会抗争的危机提供了契机。
总之,社会抗争是那些受到支配性权力压迫的行动者动员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等方面的资源生产、激活与运用反支配权力的行动。从反支配权力的角度分析社会抗争现象,有助于展现社会抗争者反支配的意愿和能力,揭示抗争对象与抗争者彼此间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与多样性的支配—反支配的关系与行为过程,阐释抗争者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场域和情境中运用反支配权力的策略、技术与方法。社会抗争既不意味着颠覆既有的政府体制与社会结构,也不能被等同于一种破坏性的行为,它有可能促进社会朝着文明、和谐与有序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于建嵘:《集体行动的原动力和机制研究》,《学海》2006年第2期。
②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③闫丽娟、王瑞芳:《农民的道义经济和发展抗争——一个西北少数民族村落的征地谈判个案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期。
④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⑤Steven Lukes,Power:A Radical View,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86.
⑥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⑦潘毅:《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
⑧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⑨关于“支配性权力”与“反支配的权力”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拙文《作为支配的权力:一种观念的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与《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一种观念的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⑩Hanna Arendt,On Violenc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ook,2014,p.40.
(11)(12)(27)潘毅、卢晖临、张慧鹏:《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13)黄振辉:《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基于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
(14)韩志明:《闹大现象的生产逻辑、社会效应和制度情境》,《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1期。
(15)俞志元:《集体性抗争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一项基于三个集体性抗争行动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6)(26)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7)(18)李晨璐、赵旭东:《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社会》2012年第5期。
(19)(31)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社会》2010年第2期。
(20)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7~320页。
(21)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2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8页。
(23)参见约瑟夫·奈《灵巧领导力》,李达飞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24)O’Brien,Kevin J.& Li Lian Jiang,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
(25)申端锋:《非抗争政治:理解农民上访的一个替代性框架——兼与于建嵘、应星等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28)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
(29)(30)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
(32)潘毅:《打工者:阶级的归来或重生》,《南风窗》2007年第9期。
(33)王洪伟:《底层抗争的潜在危机》,《人民论坛》2010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