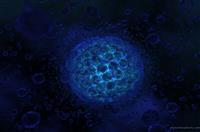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视野,培育具有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现代公民并使之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公民教育实践中,如何做到既遵循公民教育的一般规律又突显我国独特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构成了深化公民教育研究的学理焦点。从公民诞生的生命历程出发,可以找到破解这一理论难题的新视角。
在“公民”这个偏正语词结构中,“民”是中心词,它同时又被“公”所规定和诠释。“‘民’首先应当是被‘公’承认之‘民’,其次必须是承认‘公’之‘民’。”[1]现代社会中,“公”对“民”的承认方式是国家在制度层面赋予个体以平等的公民资格,为个体的权利、义务提供法律保障。这意味着个体在政治制度和生活世界中彻底摆脱封建专制的禁锢,脱掉“臣民”的身份,真正成为能够自觉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的个人生命的主宰。在“公”对“民”的承认中,伴生一场发现“我”的政治觉悟。它是在个体获得公民资格后,逐渐形成公民意识、确认社会政治身份的理性自觉过程;是把制度赋予的权利、地位等外在资格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规范、理想、意愿和期待的过程。以中国伦理文化的社会变迁为历史依托,“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域下,我国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公民政治身份的建构必须以认同国家政权合法性为前提”[2]。换言之,国家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勘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权利的边界,决定着公民身份建构的基本架构。
公民身份、公共生活本身并不具有伦理道德的天性,履行政治制度所要求的权利、义务,不妨害他人的利益,也远非理想公民教育的最终目标。当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教育正在遭遇“好人”与“好公民”的困境。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如何把公民对于国家认同的理性认知内化为情感体验和信仰感悟的现代性难题。此时,“民”对“公”的承认就显得愈发重要。在公民诞生过程中,“民”对“公”的承认本质上就是认同“我们”的伦理觉悟。这是一场促使公民由政治主体提升为伦理政治主体的生命觉悟,是一场公民伦理身份认同的精神洗礼。“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3],由于“‘公民’之‘公’兼具政治和伦理双重意义”,因此,“‘公民’之‘民’便应当是在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上达至‘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的社会主体”。[4]
现代社会中,发现“我”与认同“我们”的公民诞生历程与黑格尔(FriedrichHegel)提出的“个人获得现实性”的规律之间具有极其相似的同质性逻辑。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天才地发现:“既认识个体并希求个体的单一性,又认识实体并希求实体的普遍性。由此,个人就获得两种权利:无论作为个别的人或作为实体性的人都是现实的。”[5]需要指出的是,发现“我”的公民政治觉悟以理性为基础,而认同“我们”的公民伦理觉悟则突显精神关怀,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为了给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现实保障,为了规避伦理实体建设中的道德风险,认同“我们”必须建立在发现“我”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并有效提升公共生活及其质量,发现“我”需要依托于自然伦理实体,走向更高层次的认同“我们”。
二、发现“我”与认同“我们”的公民教育
由于“培养公民是一切教育目标表述的基础,也是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6],所以我们有必要基于培养现代社会合格公民的总体目标,从社会生活与学校教育两个层面入手,解析当下我国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
(一)发现“我”的公民教育——确立人的主体存在的公民政治教育我国现代社会生活中,发现“我”的公民教育应突显两个基本要义:一是彻底消解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依附型人格,确立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二是帮助个体充分体认法律、规则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并且尊重和敬畏法律的绝对权威,学会在法律和规则空间中获得方向感和权利定位。
没有私人领域的经历与体验,个体便不足以获得独立、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核心素养,不足以形成共同体生活中对话、协商、妥协、和解的内心体验和情感基础。在确认公民身份的过程中,培育个体的独立人格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清晰划定公民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边界,因为这是实现每个公民的自由并使人类公共生活成为可能的关键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这里的自由是消极自由)”[7]。“美国当代哲学家黑尔(JohnHeil)研究发现:人类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诉求,一是意志自由,二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注定了人类的公共生活。事实上,人类也只能在公共生活中获得自由。”[8]由于人类的公共生活具有明显的涉他性和外向性,公共生活的主体“不仅包括私域中现存的所有私人,而且关涉曾在的、将在的私人和与人类生活相关的自然生态等”[9]。所以,清晰划定个人权利的边界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们陷入不能自拔的自我泥沼,避免主体性原则的扭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法律和规则扮演着勘定个人自由边界的核心角色,为公民个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提供了参照基准,使公民个体在公共生活中有了方向感和权利定位,因而它们是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当前,我国部分民众在公共生活中忽视和否认个人自由的边界,表现为肆意在公共领域“张扬个性”,充分展现“唯我主义”;惯以个人标准和主观情绪遮蔽、僭越法律规则,这充分彰显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公民法制教育的紧迫性。
与社会生活相呼应,当前我国学校生活中发现“我”的公民政治教育应突显三个方面的本质特征:一是把培育个体的独立人格作为儿童、青少年公民意识启蒙的核心基础;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儿童、青少年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三是从个人权益的保障和民主社会的建设两个层面入手,帮助儿童、青少年充分认识法律、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引导他们自觉尊重并捍卫法律的权威,把遵规守法内化为自身的行动意愿。
(二)认同“我们”的公民教育——回归伦理精神家园的公民道德教育我国现代社会生活中,认同“我们”的公民教育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中,帮助公民个体确立起国家权力和财富与自己同一的“高贵意识”,进而使公民个体之心与国家作为伦理实体之公在精神层面上建立起同一性关系;二是在公共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上,引领公民个体充分体认人之为人的类属性,“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在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建立起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一体性。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建立在二者相互承认基础上的共生互动与价值同构,它不仅意味着公民个体之“心”对国家作为伦理实体之“公”的接纳、认同和回归,还意味着国家之“公”对于个别性存在的公民的“可靠居留地”的家园意义。就此而言,加强国家的伦理实体建设,是帮助公民个体在精神层面上实现国家认同的必要条件。伦理实体必须能够彰显人的公共本性,国家权力和财富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实质是判别国家伦理实体的核心尺度。认同个人与国家的一体性关系,自觉生发“爱国心”,把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个人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公民个体形成具有精神气质的国家认同的关键性标识。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和社会是不具有自然性和直接性的伦理实体,所以国家精神不同于家庭精神,它不能自发生成,需要加以必要的德性教化。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曾向西方社会警示:“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10]现时代,公共生活的领域已经从国内拓展到全球,从人类社会延伸到自然生态。此时,每一位公民对于人的公共本质的认同和信念愈发重要,因为这将对人类种族的绵亘具有决定性意义。认同人的公共本质,意味着公民个体主动扬弃人的孤立存在,致力于追求“更高质量的‘我’与‘他’、‘我们’与‘他们’的关系”[11]。在黑格尔看来,这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的“法的命令”;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情怀。认同“我们”的公民伦理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公民个体在公共生活中自觉服务公共利益,自觉承担公共责任,自觉捍卫公共福祉的种种善行之中。因此,培育公民“推己及人”的人类精神既有赖于进一步完善支持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制度安排,也要关注对个体公益精神和公共生活行动力的有效培育。
与社会生活相呼应,当前我国学校生活中认同“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应聚焦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在儿童、青少年中进行国家伦理意识启蒙,引领他们把国家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地,坚定他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二是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风尚,引导儿童、青少年学会伦理的思考,主动摒弃对于因不同原因而陷入处境不利状态的同伴的冷漠、歧视和排斥,自觉充当学校共同体生活的支持者、维护者和促进者。
公民诞生的生命历程无疑为我们改造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逻辑支撑。
(一)依托于公民诞生的两次觉悟,调整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内容体系
在公民诞生的过程中,发现“我”的政治觉悟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在政治、法律生活中,公民以原子式个体为出发点,力图借助制度安排和利益博弈来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精细置换。认同“我们”的伦理觉悟以“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的精神形态为基础。在伦理生活中,公民以对家庭、民族、国家等伦理实体的认同和信念为始点,把伦理实体作为个人行动的家园和目的。在公民诞生的两次觉悟中,尽管基于理性的发现“我”与基于精神的认同“我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但不容回避和否认的是,两者遵循着迥然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方式。如果无视公民基于理性的政治觉悟和基于精神的伦理觉悟之间深刻的殊异,把政治、法律、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诸多内容混杂在一起,堆砌在相关公民教育课程中,必然会令学生感到困惑,以致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法律生活与伦理道德生活的角色切换中频频错位。如果人们运用伦理道德原则去对待和处理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律等问题,那么必然会陷入“亲亲相隐”的悖论;如果在伦理关系中惯用理性原则,无视伦理实体的存在,通过精细算计谋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那么家庭亲情、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将荡然无存。
公民诞生的两次觉悟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基本架构做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在规定:帮助个体发现“我”的公民政治教育和引领个体认同“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我国的学校教育必须勇于直面并承担推进个体政治和伦理觉悟的双重文化使命。依托于发现“我”和认同“我们”的两次觉悟,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可以划分为两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旨在帮助个体完成发现“我”的政治觉悟。它包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政治学知识(如社会政治结构,民主、正义等关键政治概念,民主运作程序等);相关法律知识(如法定权利与义务、正义程序等);维权智慧以及表达个人合理诉求的能力等。第二个模块旨在帮助个体认同“我们”,即从政治主体提升为伦理政治主体。它主要涵盖伦理道德教育,注重个体的道德品格和德性养成。
(二)把学校生活改造成“公民生活”[12],以形塑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
在公民诞生的过程中,“公民生活”的作用远胜于“公民知识”。正如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所言:“有了公民生活,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13]不仅如此,学校的公民生活还要以成人社会的公民教育和成年人在公民生活中的自我教育为前提。毋庸置疑,教育者在为学生构建民主、平等、自由的“公民生活”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以推进儿童、青少年的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为目标。现时代,我国学校公民生活的建构至少应当展开为两个方面。
其一,清晰划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线,在私域中为培育个体的独立人格预留空间,在公域中坚守法律和规则的底线。
“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主张精英统治,偏爱礼制,强调日常人际交往中的仁爱、诚信、怜悯、责任等道德要求,尽管它有助于人们在交往、协商中和谐共处,但是它却既遮蔽自由、人权、私人领域的存在,又明显缺乏社会契约、公共领域、正当法律程序等概念”[14],致使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58长期处于经纬交织、含混不清的状态。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校生活亦是如此,部分教育者一方面按其个人偏好和价值判断对学生的私人领域强加干涉,另一方面忽视在学校生活的公共领域强化学生的法律和规则意识。这必将阻碍个体创造力、独立人格、公共精神的健康发展,不仅不利于当前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也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著名教育家杜威(JohnDewey)早在20世纪就曾断言,如果人们对社会现状不满意的话,首先应求助于教育。在学校公民生活中,教育者率先建立起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价值取向与理性自觉,“在私人领域为学生留下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在公共领域坚持群体利益和规则优先原则”[15]将会对社会生活起到倡导、引领和定向功能,助力我国公民提升政治觉悟。尊重、承认、不轻易干涉学生的私人领域,决不意味着教育者可以无视甚至纵容心智不成熟儿童偏离向善发展方向的不当选择。在我国当下的学校公民生活中,教育者应特别注重培育儿童、青少年自主发展和独处的能力,帮助他们形成独立意识,学会进行独立学习、独立规划、独立判断、独立选择,善于独立解决问题。我国社会法制教育薄弱的现状,迫切要求教育者在学校公民生活中引领学生学会清晰划定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边界,坚持把“合法合规”而非“合情合理”作为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准则。
其二,为儿童、青少年提供亲历共同体生活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帮助他们不断改组和改造以交流互惠、互利共赢、互赖互爱为基础的公共生活经验。
现代中国社会已经悄然步入公共生活时代,其标志是公共交往活动空间不断扩大,公共物质共享空间不断拓展,公共信息互动空间不断延伸。事实上,法律规则、制度安排对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和引导存在盲区。法律和规则没有涉及的那部分空白需要伦理道德来填补。当前,我国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践行能力的危机,既有部分民众藐视法律和规则的成分,也牵涉部分民众道德践行力偏低的问题。这就折射出我国学校公民生活中,儿童、青少年需要改组、改造的公共生活经验不仅包含遵规守纪的行动自觉,而且还要在相关法律规则明显缺场的条件下,坚持互赖互爱、互利共赢,提升公民的道德行动力。我国儿童、青少年公共生活经验极其匮乏的现状,迫切要求学校在建构公民生活中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参与公共活动、承担公共责任、服务共同体利益的机会。儿童、青少年改组、改造公共生活经验的成果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在认知层面上,能够理解国家与个人之间、公民个体之间、不同社群之间、不同国家之间普遍存有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进而形成融自身权利和尊严与他者权利和尊严于“整体社会福祉”的公共理性。在国家与个人情感关系上,能够主动接受民族历史文化的濡染,自觉生发对国家共同体生活的记忆、认同、享受、热爱、信念和追求。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上,能够自发生成同情心、同理心、归属感、责任感等积极道德情感。在行动智慧和能力上,能够有意识地尝试为在公共生活中处于纷争状态的当事双方探寻可能展开协商、对话的接触点和互惠点。
参考文献:
[1][4]樊浩.伦理,“存在”吗?[J].哲学动态,2014,(6).
[2]李兰芬.国家认同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2014,(12).
[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65.
[6]万明钢.论公民教育[J].教育研究,2003,(9).
[7]俞吾金.论尊严、公正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2).
[8]樊浩.道德之“民”的诞生[J].道德与文明,2014,(2).
[9]李晓辉.公域与私域的划分及其内涵[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10]伯特兰·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59.
[11]石中英.“狼来了”道德故事原型的价值逻辑及其重构[J].教育研究,2009,(9).
[12][13]檀传宝.当前公民教育应当关切的三个重要命题[J].人民教育,2007,(15—16).
[14]杜维明.家庭、国家与世界:全球伦理的现代儒学探索[J].国外社会科学,1999,(5).
[15]傅维利.论教育中的惩罚[J].教育研究,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