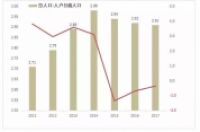
自去年以来,不少大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大学本科、大专甚至中专学历的都可以落户。尤其是最近天津推出的“海河英才”人才行动计划,把“抢人大战”推向了高潮。观察发现,加入抢人行列的多为省会城市甚至直辖市,集中了各种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为何还要抢人呢?本文试作解读。
大部分城市出现流动人口“净流出”
看到这个标题,想必大家都会心生疑虑,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都是以1%以上的速度在提高,简单测算,即城镇每年增加的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所谓常住人口,按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就是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超过6个月。
说实话,本人对于每年城镇的常住人口增加2000万也感到困惑:第一,2017年中国自然增长人口只有737万人,就算其中的70%增长落在城镇,那么,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也就是500多万。第二,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增加125万人;第三,据估计,2017年新增本科、大专等人数700万左右,按其中50%来自农村(高估)计算,从农村进城的学生数量约为350万人。
把上述城镇人口增加的三类主要方式加总,也不过975万人,还有1000万人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的呢?或许是由于市辖的农村行政区划改变,撤县设市或撤县设区,于是所在地有1000万人“农转非”。
但有一个事实毋容置疑,即从2015年开始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所谓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也就是说,人的居住地不在户籍所在的市辖区内,就叫流动人口。如户籍在上海崇明的农民,如果居住在上海的虹口区,就不算流动人口,但若居住在浙江,就算流动人口了。
2015年流动人口减少400多万,2016-17年两年减少了300多万。流动人口人口的减少有两个路径,一个是流动人口回到老家了,另一个是流动人口在居住地落户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居多,从客流量的统计数据看,2017年全年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客流量的加总出现了首次下降,2018年的春运客流量也出现了下降。
也就是说,尽管人口总量还在增加,城市化率水平还在提高,但流动人口数量已经绝对减少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城市的流动人口出现“净流出”的原因了。若对部分省市的常住人口中扣除自然增长人口后,观察到很多省份的大部分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
即便是人口流入量最大的广东省,在可获得的19个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中,居然有1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扣除自然增长人口后出现了负值,也就是人口净流出。而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辖市不仅出现人口净流出,而且常住人口数量也出现下降。
连经济最发达的直辖市和GDP规模第一的省份下辖的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问题,这就给不少省会城市带来了对未来人口流出的担忧,尽管迄今为止,大部分省会城市的人口还是净流入的。
相信各省级政府不会对此熟视无睹,尤其是过去几年一度出现过常住人口数量减少的城市,如天津、西安等,一定会充分评估劳动人口,尤其是人才对于一个城市的劳动要素供给和消费拉动的意义。
农民工不再“跨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披露,新增外出农民工主要在省内流动,省内流动农民工增量占外出农民工增量的96.4%。而2016年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79万人;2015年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22万人。
从细分数据看,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这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相对偏年轻有关。但是,农民工老龄化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如“201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比上年提高0.7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4%,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
外出农民工增速的下降,恐怕与人口老龄化相关,因为年纪越大,外出打工的动力就越不足。2017年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相差5.4岁。
此外,不同区域农民工薪酬差异的下降,也是导致跨省农民工数量下降的原因。如2017年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长7.5%,但在东部(3677元)和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只增长6.4%,西部和东部农民工的收入差异不足10%。
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与农村可流出劳动力总量的减少有关,也与这些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实现额占当年名义GDP比重超过85%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中西部省份。例如,富士康原先都只在国内的东部沿海地区设厂,如今,富士康已经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城市都设了厂。
附带说明一下,这些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地区,未来经济下行可能性和债务风险都将非常大。历史数据表明,高投资不能带来经济转型。
在过去三年中,中西部地区有六个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当地的GDP,同时,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发展最好的三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下。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几乎不再增加,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幅相对较大的原因。
但是,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要远超城镇,目前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大约为36岁,但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接近40岁了,原先流入农民工最多的珠江三角洲,已经出现农民工数量的净减少,说明老一代农民工中已经有一部分开始告老还乡了。
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与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的时间几乎一致,分别为2011年和2012年,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逐步步入到存量主导时代。既然到了存量时代,那么经济结构调整就成为必然,调整的过程就是此消彼长——哪个地方人口的流入,就意味着其他地方人口的流出。这就构成了某些大城市需要抢人的逻辑。
放开生育?远水不解近渴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鼓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供给成为必然选择。从中央层面看,今后不仅会放开生育限制,而且还会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是,对地方政府而言,若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不仅会当期增加财政支出,而且还要增加卫生、教育等投入。对企业而言,放开生育的政策又会导致女性员工工作时间的减少,对劳动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
以山东和广东两省为例,2017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均为101万,但山东出生人口达到175万,广东出生人口为151万。可见山东成为当下全国人口出生最多的省份,占全国新出生人口的10%。但是,由于山东人口净流出42万,而广东人口则净流入68万。假设流动人口大均为劳动年龄人口,死亡人口均为老年抚养人口,那么,2017年山东省和广东省的抚养人口均增加101万,但劳动年龄人口呢?山东减少42万,而广东增加68万。
上述数据表明,2017年这两个经济大省的人口抚养比例都在上升,是全国抚养比的一个缩影。只是山东的上升幅度明显超过广东。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当然希望人口抚养比例不要上升,吃饭的人口多,工作的人口少,自然不是好事。
我国在1970年之前,基本都是采取鼓励生育政策,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但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195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为60.5%,在鼓励生育的政策影响下,到1965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例到达历史峰值80%,这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间有没有必然关系呢?1976年,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5年之后,抚养比开始明显下降。
1977年之后,随着1962-1971年这十年的生育高峰人口逐步成为劳动力,中国人口抚养比加速下行。1980年降至67.8%,2000年降至46.1%,2010年则达到35.6%的历史低点。2011年之后抚养比开始缓慢回升,中国经济增速也随之下行。
因此,追溯历史,会发现鼓励生育政策对经济发展而言,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效果。如1950-1970年,显然属于“前人种树”阶段;而计划生育政策则具有“当下快活,未来遭殃”后果。“抢人政策”呢?相当于“树木移植”,即“甲地种树,乙地乘凉”。
如天津最近颁布的落户条件中,把“技能”与年龄进行组合,技能越高,年龄越宽,本科一般不超过40周岁,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也就是说,让一个本科生留在天津工作,一般可为天津工作20年;但要让一个新生婴儿成为一名劳动力,一般需要等20年。
那么,为何“抢人事件”首先出现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呢?这与这些城市的财政实力、产业支撑和经济转型需求有关,毕竟这些大城市需要资源集聚的优势。其实很多三四线城市更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也需要人口流入和人才引进以支持当地的房地产和产业发展。但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即便高成本引进了人才,恐怕也难留住。
总之,国内抢人现象的屡屡出现,是中国经济步入存量时代的一种反映。记得本人在五年前的一次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发言中,就提出今后中国大城市会出现“抢人现象”,上海应该及早制定应对之策。




